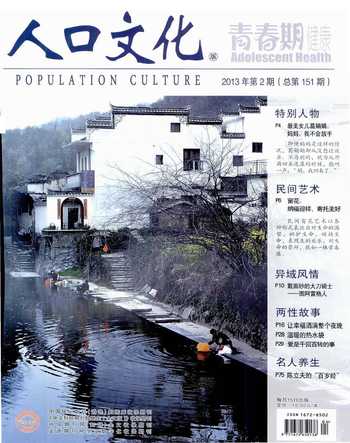最美女兒葛娟娟:媽媽,我不會放手
孔雨童
葛娟娟平順的生活在10個多月前的一天下午突然發生改變。母親呂豐蓮在家門口突發腦溢血,在醫院經歷15次病危后被勸出院“準備后事”。可葛娟娟和爸爸葛松波并不放棄,他們把母親接回家,靠著“鼻飼”和“插管呼吸”維持著她的生命。
10個月 24小時“醒著”的家
去到葛娟娟家里之后,才能真切地感到這一家的困境。
記者進門之前,葛娟娟特意又在屋里拖了一遍地。這是一個燈光有些昏暗、到處堆滿了藥、米粉、被褥的空間。客廳里,葛娟娟的母親躺在床上,渾身蒼白,身下是防褥瘡的氣墊。她雙眼緊閉,喉嚨間插著一根塑料管子,呼吸的時候能聽見呼嚕呼嚕的聲音。
娟娟的父親葛松波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一直睜大著眼睛盯著妻子。每隔兩個小時,定好的鬧鐘就會歡快地響起——提醒這對父女該給病人喂飯喂水了。這時,娟娟會用一個針管,一管一管地把米粉糊或水打進母親的鼻腔里。經常地,一管米糊下去,昏迷的母親會一激靈。
2小時喂一次飯水,3小時吸一次氧,隨時測量體溫、吸痰,只要覺得屋里干燥或有灰塵就立馬拖地……這樣的日子,葛娟娟和父親一起堅持了10個多月了。白天,父親就坐在客廳看著母親,到晚上換成葛娟娟。有時父親讓娟娟去睡一會,她就開著房門,屋外一點動靜她就爬起來。
這天傍晚,我們再來的時候,葛娟娟正在用溫水給母親擦拭按摩身體。一點一點,修長的手搓捏著母親蒼白浮腫的臉、僵硬的手、時常冰涼的腿……她邊搓邊跟母親說話,有時會微微笑著。
決不放棄 “要讓媽媽活著”
“那天,外面刮著很大的風……”
那是2012年2月11日,母親買菜回來走到家門口,忽然摔倒在地上。鄰居發現以后,重重地敲著葛娟娟家的門。獨自一人在家的妹妹給她打電話,她瘋一樣跑回家。
走廊里,急救醫生跟她說,是腦出血,趕快叫家長,快不行了。做完CT,醫生拒絕手術,因為“已經沒有生命體征”。
“要做。”娟娟堅持,父親葛松波正在外地出差。在電話里他沖醫生吼叫:“你不給我老婆做,我回去跟你拼命!”
手術進行到凌晨,母親奇跡般地被推進了重癥監護室。但在那之后,這種需要簽協議、被稱為死后的“死亡手術”在父女倆的堅持下又進行了3次。在醫院的幾個月時間里,母親一共被下了15次病危通知。
住在重癥監護室里,一天的花銷近1萬,這讓一個人在外打工的葛松波難以支撐。娟娟打算把自己攢的2萬塊錢拿出來,但父親不讓她動,說“讓她以后找對象花。”父親去老家借錢,一次次回來眼圈都是紅的。娟娟還是偷偷的,把錢交上了。
再后來,父親找出了房產證。
有親戚開始勸他們了。“你都知道往里扔錢了,還扔?”
“她是我媳婦,我把房子賣了,我也得救她。”葛松波說。
“你孩子怎么辦?”
“我養著我妹妹。”娟娟沖出一句。
“你傻啊,你爸以后怎么辦?”
“我養!”
“你妹妹呢?”
“我也養。還有我姥爺,我都能養著他們!”
葛松波帶著妻子的CT片走遍了省內的所有大醫院。在煙臺一位著名醫生看了片子第一句話是“去世多久了?”看了后來的片子第二句是“手術很成功”,可最后卻告訴他“你老婆永遠醒不過來了”。
在重癥監護室40多天,藥物已經沒有什么用了,而這時應住6個人的重癥監護室已經住進了13個人。怕母親感染,娟娟和父親跟護士一步步學會了所有的護理技術以后,他們把母親接回了家。
在沒有自主呼吸切開氣管插管的情況下,一般病人會很快感染。但是回家后半年多的時間里,母親一次也沒有感染過。
娟娟回醫院找醫生問情況。很多醫生聽說她母親還活著,都張大了嘴。
娟娟的家里,掛著父母親20周年補拍的婚紗照。照片中,有些豐腴的母親在父親旁邊甚至有些顯老。但是兩個人眼里都閃著笑意。
去當義工 “做公益好像能支撐我”
今年8月,在日復一日照顧母親的過程里,葛娟娟加入了萊州義工群。跟父親交班后休息的那幾個小時,她會跟大家一起去做些公益活動。有時候去拾撿垃圾,有時是去孤兒院看望孩子,這樣的時間并不多,但每一次葛娟娟都很珍惜。
“可能家里越是這樣,越是更能明白那些跟我一樣的人。”葛娟娟說,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一定要去做這個,從某種方面來說,做些公益好像能支撐她,給她一些快樂和安慰。
盡管家里欠著幾十萬的外債,盡管現在母親一天的花銷就要過百元、家里還有上學的妹妹,葛娟娟從來都是安安靜靜的做公益,沒有向誰傾訴過。
“跟別人說了,只能是多一個人為你難受,我想靠自己。”在這一點上,娟娟有著特別的執拗。母親出事這些天,她都是一個人跑到小區的樹叢里偷偷哭,哭完了笑著回家。當有人提出為她向社會尋求捐助時,她也拒絕了。27歲了,我們問她是否想找一個人幫她分擔,這個漂亮的女孩子還是倔強地搖搖頭。
“我們家的情況太特殊了,我只想一個人努力,讓家人都能活下去。”
義工“選擇”和“老魚”給她找了一份工作,在汽車4S店里做汽車用品的銷售。葛娟娟休息的時間更少了,白天上班,下班之后還要幫父親照顧母親,睡不了幾個小時又要去上班。
牽掛姥爺 “他們是我最親的人”
葛娟娟還有一個牽掛,那就是她的姥爺。
6歲以前,因為父母在大連打工,她一直住在姥爺家。“我上幼兒園,姥爺就搬個小板凳在外面守著。他們是我最親的人。”母親出事前,已經患腦血栓行動不便的姥爺跟著他們一家住。出事以后,姥爺不得不搬到舅舅家。
開著車,我們帶著娟娟來到舅舅家,但是在車上她始終沒敢下車,只是望著姥爺住的小屋默默紅了眼睛。母親出事以后,已經幾乎無法行走的姥爺拄著拐杖踉踉蹌蹌地挪到他們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從那以后,老人的精神就垮了一半。
中午,推開這個院子南邊的一間小屋,我們看到了葛娟娟的姥爺。一進屋,就能聞到一股濃重的尿騷味。這間屋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放衣服的紙箱,再沒有其他的陳設。老人穿著幾層衣服坐在床上,蓋著的那床被子顯得很單薄,在這個有些陰冷沒有任何取暖設備的小屋里,也許是因為腦血栓后遺癥,也許是因為真的冷,老人一直在抖著。
“冷不冷?”我們問他。“白天不冷,晚上冷。”老人的眼睛仿佛干涸了一般,籠著一層迷茫的神色。我們說明了來意,他遲疑的目光慢慢轉向我們,像是抱著很大的希望問:“我閨女怎樣了?”
“還在家,一直沒有醒來。”
老人仿佛憋了很久的委屈,眼淚涌了出來,一粒粒滾落在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我閨女是個好孩子啊,我這個人命不好。”
臨走的時候,外面還下著雨。老人拄著拐杖站在門口送我們,定定地出神。
幾天以后,萊州義工們帶著羽絨服和新的棉被到了老人的小屋。屋里依舊沒有生爐子,也沒有電熱毯。一位義工告訴記者,他們曾經跟娟娟的舅舅交流過,他說因為老人腦血栓怕尿床引發電線短路,所有沒敢用電熱毯。爐子因為之前發生過火災,暫時也沒有安。“
這里曾是老人的房子,但是現在他再也無法住到自己向陽的那間屋里。他還在等著,他的女兒醒來。
(編輯 李天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