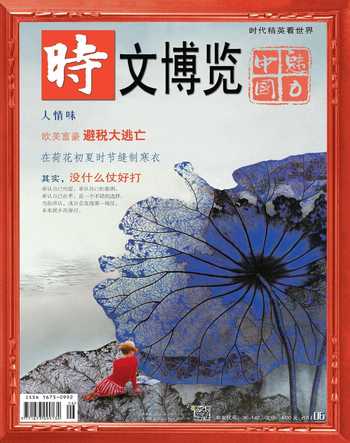黃怒波:登山者有敬畏
田小滿
早先登山時他總會習慣性地不斷追問向導:“還有多遠才能到達?距離頂峰還有多高?”后來他不問了,他知道一點點地前進,早晚會走到目的地。
一
用了20個月的時間,黃怒波將自己的足跡留在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地球的兩極點。從珠峰下來時,他給圣山磕了三個頭,感謝珠峰的佑護,“我登了三次珠峰并且活下來,是珠峰對我的寬容。”黃怒波這樣說。
在一次金融業的晚宴上,黃怒波朗誦了自己的一首詩作《塔肯納的鯨骨》—寫于麥金利峰3號營地。
后來,黃怒波告訴我,每一次朗讀這首詩,他仿佛都回到了登頂的時刻。那種渺小的感覺總是一次次沖擊著他:登頂并不意味著征服,登頂并且活著下來,也僅僅算是打了個平手。
2009年,黃怒波從北坡登珠峰失敗了。在這之前,一切順利,他一直對自己充滿自信。那一次,在7900米的營地上,他看到一個已逝的韓國隊隊員躺在旁邊,已經三四年了,就那么靜靜地躺著,像一個熟睡的旅者。他已經可以看到位于8000米的大本營了。然而此時天氣突變,雪霧彌漫,5米之外看不到任何東西。
他走在一個大斜坡上,一腳踩空。他拽著繩子,趴在雪坡上往下滑,一邊用腳使勁兒蹬石頭,但蹬著的都是浮雪,一點用都沒有。這時他先將右手插入雪里,固定身體,降低速度,當降速減緩,又將左手插進雪里。就這樣雙手插在雪里,慢滑了六七米,終于停了下來。
在還有幾十米就到頂峰的時候,黃怒波不得不選擇了放棄。
后來他說,這個決定似乎是珠峰對他的最大考驗:在看似唾手可得的成功面前,你真的明白自己的內心所愿嗎?
這像是一場賭局,有人不甘心放棄而成功登頂,也有人因此喪命。黃怒波說,如果他繼續登頂,很可能落下難以根治的身體創傷。對于放棄,他痛苦而不悔恨,他接受了挫敗,因為能活下來才是最幸福的。
珠峰歸來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黃怒波的頭腦里總是有山的影像出現,分不清是現實還是幻影。特別是晚上睡覺時,他感覺自己還在不停地攀登,山路總也走不到盡頭。每一次攀登都會目睹死亡,經歷風險,好幾個山友現在還躺在七八千米的山上,就永遠留在那兒了。在黃怒波這些年的登山歷程中,很多是二次登頂成功的。承認失敗和獲得成功有同樣的尊嚴,不同之處是前者需要更堅韌的心態。
二
回到大本營時,黃怒波回望珠峰,曾發誓再也不回來。但是,2011年他抵達北極點之后并無疲勞之感,他決定重新挑戰珠峰,而且要從北坡登頂—2009年他正是在這里黯然退卻的。
從珠峰北坡登到距頂峰48米處,他開始頻繁摔倒。他覺得兩個耳朵那么暖和,眼前沒有太陽,但卻感覺太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他聽到一個聲音說,如果能坐下來,閉上眼睛睡一會兒,就太美妙了。他幾乎要照著去做了,可突然意識到,那就是死神的聲音。
當他終于站到珠峰頂端,摘下氧氣面罩,在峰頂看到了平時無法看到的日出。在8800米的高度看日出是俯瞰,與平視、仰視的感覺很不一樣。紅彤彤的太陽躍出云海,剎那間變成金色,他真切地感知到天地萬物的萌動與蘇醒。
黃怒波看過一本美國人寫的書《登頂》,書中說美國許多企業家都熱衷登山,因為登山是一種行為哲學,是一種非常適合冒險家自我修煉的手段。企業家面對的不確定性和登山很像,所以企業家必須保持優異的風險應激能力。
和登山一樣,除了預見風險,還要維護好團隊的合作。早年經商時期黃怒波曾被下屬背叛,為此寒透了心,經過多年登山的磨煉,他漸漸釋懷了。
在山上時,大家拴在了同一根安全繩子上,等于命運捆綁在了一起,與向導、山友共患難,同生死,誰也離不開誰,不能小看任何一個人,那時候才真切地體會到團隊的凝聚力。下山后,面對戰戰兢兢的部下,黃怒波開始體諒他們的難處。他的員工都說登山回來的老板笑容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急躁易怒。
在山下的時候,黃怒波時常心事郁結,社會上恩怨不斷、爾虞我詐,弄得他只想脫離苦海。來到山上,他卻懷念起山下的每一天,比起山上那種地獄般的苦難和危險,現代人活的每一天其實都像天堂。
但他還要一次次進入地獄。每次從那兒回來,都是一次精神的凈化,更是心靈的拓寬。相比登山來說,山下的世界太安全、太輕松了。危機發生了,無非是公司的日子艱難一點,但是這也會變成另外一個充滿樂趣的歷險。早先登山時他總會習慣性地不斷追問向導:“還有多遠才能到達?距離頂峰還有多高?”后來他不問了,他知道一點點地前進,早晚會走到目的地。
三
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上,排列著這些年的登山行頭,鞋子、鍋灶、氧氣瓶、磨得發亮的手杖,整齊如方陣,見證了他每一次登山之后的自我發現。黃怒波開玩笑說,如果不曾登山,也許自己現在是個奸商。
2010年5月,在珠峰南坡營地里,王石和黃怒波在一起吃炸醬面,喝啤酒,朗誦自己寫的詩,天馬行空地閑聊天。在北京他們不可能這樣放松,大家彼此都戴著面具,被一群對他們有所求的人圍著,在各種五花八門的標準和利弊中權衡、伸縮,沒有人相信他們還會孤獨。
其實這種孤獨,流淌在所有的領袖人物的血液中,越在人群中,孤獨感越重。也許這就是社會擔當者的代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