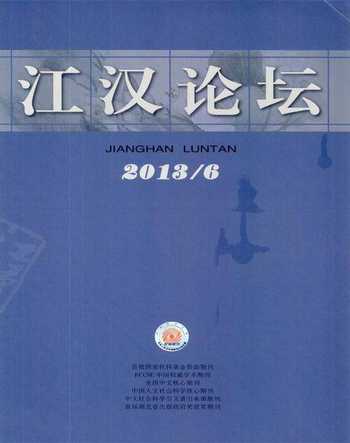革命文藝:創作主體與經典生成
吳艷
摘要:原生態的延安文藝本身很復雜,從前期的“多元共生”到后期倡導“工農兵方向”,存在一脈相承的聯系。革命戰爭年代對文藝服從性和服務性的要求,助推或限制了文藝經典的生成,但不同藝術門類仍然存在差別,就是同一藝術門類的不同主體和藝術作品之間,也存在明顯的不同。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關鍵詞:革命文藝;延安文藝;創作主體;經典生成;原生態
對延安文藝時間、空間的劃分,學界有不同意見,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狹義時空界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的1935年10月作為“延安文藝”的上限,下限則是1947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主動撤離延安。①我們將發生在這13年里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文藝運動和文藝作品稱為“延安文藝”。一般認為,狹義的延安文藝發展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開創和發展時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藝方向確立與完型期(1942.5-1947.3)。
延安文藝與蘇區文藝和中國共產黨存在著天然密切的關系,我們很容易把握延安文藝前后期的不同特點及其一脈相承的聯系。簡單說來,延安文藝前期是“多元共生”的境況,后期則是主張“工農兵方向”的時代或者用今天的話說是提倡“主旋律”的時代。由此形成文藝創作主體即藝術家包括作家生存的客觀環境,其具體細節又直接作用于作家的主觀精神,并制約了作家的創作和文學經典的生成。
通過對延安文藝前期藝術家及其文藝創作實績的原生態考察,我們發現延安文藝隊伍由三方面人員組成:一是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所屬革命文藝隊伍中的成員;二是從其他地區(蘇區和白區)來延安的黨的文藝領導和文藝工作者;三是從其他地區(蘇區和白區)來延安的普通文藝工作者,包括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延安文藝隊伍的開放性質,為文藝社團建設、文藝創作實績打下良好基礎。
作家丁玲到延安時所受到的禮遇、茅盾在延安的4個半月的經歷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文學史佳話。冼星海曾在日記里記載他到延安的原因和經過:“延安這個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國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當時并不留意。到武漢后常見到‘抗大、‘快公招生的廣告,又見到延安來的青年。但那時,與其說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說是注意他們的刻苦、朝氣、熱情。正當我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一封信,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我。我問了些相識,問了是否給我安心自由的創作環境,他們回答是有的。我問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他們回答說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慮去與不去的時候,‘魯迅藝術學院又來了兩次電報,我就抱著試探的心,啟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再出來。那時正是1938年冬天。”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錢韻鈴乘著一輛華僑捐贈的運送藥品的救護車到達延安。11日,八路軍前方將領宴請冼星海。12月,冼星海完成《軍民進行曲》歌劇。1938年3月,他花了6天時間完成《黃河大合唱》的創作。4月13日,由冼星海指揮的《黃河大合唱》首次公演。受到黨的領導人、文藝評論家和所有觀眾的熱忱歡迎和高度贊揚。
冼星海不僅受到政治、業務上的悉心關照,也在經濟上享有優厚待遇。冼星海當時每月津貼是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當時延安生活艱難,1938年的津貼標準為:士兵和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毛澤東、朱德也是5元,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學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10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發的是延安的“邊幣”,一元邊幣可買兩塊肥皂或一盒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
當時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其“刻苦、朝氣、熱情”曾吸引了許多作家藝術家,具備“自由的創作環境”,不合意可以“再出來”等寬松氛圍,許多藝術家就是抱著像冼星海這樣的心態投奔延安的。事實上,像冼星海這樣的藝術家,到了延安,確實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不僅在當時的延安及其他根據地產生了廣泛影響,至今仍然是中國的名曲之一。2009年9月14日,冼星海還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文藝隊伍的開放性,還可以通過以下史實說明:1936年11月初,丁玲到達延安;1937年8月,周揚、艾思奇、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達延安;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來到延安:1939年5月,蕭三從蘇聯抵達延安……由三方面人員組成的延安文藝隊伍,是開放的,是“刻苦、朝氣、熱情”的文藝隊伍。三方面人員依據自己的專長和對藝術的理解成立了相關的藝術社團。這個階段成立的文藝社團有60余個,基本涵蓋當時所有文藝門類,同時又帶有延安文藝的時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戲劇方面的社團就有人民抗日劇社、民眾劇社、魯藝實驗劇團、烽火劇團、戰斗劇社、戰士劇社、先鋒劇團等。按藝術門類、按戰爭需要組成的這些藝術社團,對激活藝術創作、鼓勵藝術創新、開展藝術批評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們在組織民眾、動員民眾和服務戰爭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隊伍成分多元、藝術社團門類風格多元必然帶來文藝成果的多樣化。這個時期的文藝批評也具有廣泛性、多樣性、民主性和經常性。如1938年1月“關于詩歌朗誦問題的研討”;1940年5月“關于文學才能問題的討論”;1941年4月“陳企霞與何其芳關于詩的爭論”;1941年7月“關于周揚《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的爭論”;1941年8月“力群與胡蠻關于美術創作的爭論”;1941年11月“楊思仲與魏東明關于果戈理評價的爭論”……我們知道,適時和正常的文藝批評對藝術家、對讀者觀眾、對社會甚至對文學理論本身的發展都具有積極作用。文藝批評對文藝創作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體現社會對文藝創作的影響力;文藝批評可以影響讀者觀眾對作品的理解:文藝批評對作品的文學價值觀念產生影響與塑造作用。文藝批評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分析與評價表達出特定價值觀念與理想,由此對社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時文藝批評的新發現可能被總結提煉成新的文藝理論,向既有的理論發出挑戰。
延安文藝的品質樂觀向上、生機蓬勃,帶有革命英雄主義的浪漫色彩。而形成這樣局面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黨對文藝的領導。延安文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隨行產物”④。黨對文藝的領導通過多種方式體現出來,主導方式是以“指示”、“決定”發出的,要求各級組織貫徹執行。這在戰爭年代是必須的,也是有效的。延安文藝同時是對蘇區文藝領導經驗的發揚光大。蘇區文藝領導經驗表現在黨直接領導文藝;組織文藝團隊和活動的方法;文藝對革命斗爭的配合方式;培養革命文藝人才;對群眾性文藝創作活動的指導和作品的收集整理等等。除此之外還有黨的領導人個人文藝素養、人格魅力對文藝帶來的直接影響。
以“指示”、“決定”的主導方式領導文藝生產,帶有強烈的戰爭年代的色彩,同時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風和領導特色。這在延安文藝開創和發展的前期為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繁榮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動員民眾,服務戰爭,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沒有接觸到延安文藝原生態材料的時候,許多人可能會存有一個簡單的想法,以為延安文藝是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這種看法顯然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了。延安文藝前、后期的發展有一個合理的軌跡,如果說前期“多元共生”是原生態的必然體現,那么后期的確立新方向、強調為工農兵服務也是原生態的必然體現,其中的變化存在一個漸變、復雜化的過程。
我們從文藝隊伍建設、文藝社團建設、文藝創作實績和文藝領導四個方面來分析。后期的文藝隊伍、文藝社團的開放性與前期沒有大的變化。以文藝對外開放大事為例:據《延安文藝大事記》記載,前期有1936年7月,毛澤東在保安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1939年,老舍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代表。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抵達延安;1940年2月14日。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三廳領導的中國電影制片廠西北攝影隊,為拍攝《塞上風云》外景路過延安,15日毛澤東、朱德接見電影隊,16日邊區文化界與電影隊座談;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劇隊抵達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壯丁》等劇目。延安文藝后期,1945年1月1日,魯藝舉行畢加索畫展;同年同月10日,邊區文協電唁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逝世;3月6日毛澤東電唁阿·托爾斯泰逝世;1946年7月,中央黨校俱樂部舉行珂勒惠支逝世紀念展……
從黨領導文藝的政策與方法上分析,我們曾經說過,黨的領導人的個人文藝素養、人格魅力對文藝產生過直接影響。但黨領導文藝的主導方式仍然是“指示”與“決定”。它是行政的,也是戰爭年代切實有效的方法,更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風和領導特色。這在延安文藝開創和發展前期,為“多元共生”的延安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有力可靠的保證,也為延安文藝后期確立新方向、倡揚主旋律提供了組織領導的有力保障。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寫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埃德加·斯諾首次訪問延安是在1936年6月,為時4個月之久。斯諾對紅軍的宣傳有切身體會,他曾經多次觀看延安劇團演出。“任何文藝都是宣傳”,但不能反過來說,任何宣傳都是文藝。文藝在戰爭年代成為中國共產黨有力的“宣傳武器”,這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共產黨地位和任務的變化,對這個宣傳武器的要求也有所變化,這也是自然、合理的,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而一廂情愿地給予假設和判斷。
以延安時期的“演大戲”為例。所謂“大戲”,“最初是包含了:多幕、寫得好、難演、難鑒賞等內涵的。既指形式上的精,也指內容上的好和精。后來,延安劇團演出的一些戲劇,不限于形式上的大,而是側重于選那些外國的、大后方的名劇上演,既有多幕的大戲,也有獨幕的小戲,但以前者為多”⑤。延安戲劇舞臺上演“大戲”的時間主要在1940年至1942年5月,其劇目分國外和國內兩種。外國劇目有果戈理的《婚事》、《欽差大臣》,羅穆的《鐘表匠與女醫生》,沃爾夫的《馬門教授》、《新木馬計》,拉夫列尼耶夫的《破壞》,莫里哀的《偽君子》,契訶夫的《求婚》、《蠢貨》、《紀念日》,伊凡諾夫的《鐵甲列車》,莫里哀的《慳吝人》,卡塔耶夫的《婚禮進行曲》等;中國劇目有陽翰笙的《塞上風云》、《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一年間》、《法西斯細菌》、《上海屋檐下》,曹禺的《雷雨》、《蛻變》、《北京人》,宋之的的《霧重慶》,陳白塵的《太平天國》等。從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起,延安戲劇舞臺基本上就不演“大戲”了。
演“大戲”最初是為了學習技術。開擴視野,后來把“大戲”的演出與政治活動聯系起來,以表示為政治服務的熱情,結果顯得文不對題。如歡迎周恩來等回延安,演出羅穆的《鐘表匠與女醫生》等。關鍵還在于,當時的延安處在戰事頻繁、物質匱乏、民眾文化水平低下的環境里。要演好大戲十分困難;大戲演多了也不合時宜。
在戰爭年代,純藝術的追求總是被大打折扣,更何況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不以某個藝術家、文藝理論家的意志為轉移。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劃時代的,卻不是一個突發事件。前面我們說過,黨對延安文藝的領導,其主導方式是以“指示”、“決定”發出,要求各級組織貫徹執行。這些“指示”和“決定”,完全服務于當時黨的中心工作。即便是前期,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服務戰爭、宣傳政治的特點。
以相關文本為例: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先以黨內文件形式下達執行,后來又刊于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第3期。1940年9月延安時期的黨中央發布了第一個關于文化問題的指示即《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1940年10月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出《關于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人團體的指示》;1941年1月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央文委發出《關于部隊文藝工作的指示》;1941年6月7日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獎勵自由研究》的社論;緊接著在6月10日又發表《歡迎科學藝術人才》的社論;8月3日發表《努力開展文藝運動》的社論;1942年3月25日發表了《把文化工作推進一步》的社論。
理順了這么一個發展線索,我們就可以說,延安文藝前期與后期存在著一脈相承的聯系。沒有前期的“多元共生”的繁榮就不會有后來的新立場新文藝的要求。傅樂成對唐宋文化作出的分析也許對我們有一些幫助。傅樂成比較研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不同特點,他說,唐型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復雜和進取的,宋型文化里各種外來思想與主流漸趨融合,并產生了民族本位文化,其文化精神和動態轉趨單純與收斂。然而在文學上,唐宋時期都同樣涌現出大批的文化巨人。
假如我們能夠更多地從復雜性角度分析延安文藝前后期的變化,就可以說延安文藝前期的主體與成果是“多元共生”;后期就多少帶有單純與收斂色彩。這種單純與收斂在文藝隊伍和文藝社團方面并不明顯,因為直到1946年7月,還成立了“延安中央管弦樂團”這個延安唯一的大型正規化樂團。延安文藝后期的變化由文藝整風運動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體現出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綱領性的文件,指明了革命文藝發展的工農兵方向。從此,文藝創作要有工農兵的、大眾的、歌頌的內容,強調文藝的普及性作用以及民族形式等成為延安文藝的主導方向。延安文藝的原生態是復雜的,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天然地緊密地聯系著。“多元共生”當然更加有利于文藝的繁榮與發展,但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發展變化階段,文藝的服從性和服務性就容易被提出和被強化。這大概也是歷史的真實和延安文藝的必然結果。
眾多的文藝社團,相關的文藝政策和領導人對文藝的喜好等,所有這些,都助推了與之相關的文藝經典的形成。如《黃河大合唱》的誕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張光年),在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帶領抗敵演劇三隊,從陜西宜川縣東渡黃河,轉入呂梁山抗日根據地。光未然途中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狂風惡浪搏斗的情景,聆聽了高亢、悠揚的船工號子。次年1月抵達延安,就寫出了《黃河》詞作,在除夕聯歡會上朗誦了這部詩篇。冼星海聽后非常興奮,當即表示要為演劇隊創作《黃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簡陋的土窯里,冼星海抱病連續寫作六天,完成了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型聲樂作品《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詩性大型聲樂套曲,氣勢宏偉磅礴,音調清新,樸實優美,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強烈地反映了時代精神,表現了在抗日戰爭年代中國人民的苦難與頑強斗爭精神,也表現了我們民族不可戰勝的力量。《黃河大合唱》幾乎超過了所有藝術經典的影響。在延安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演,引起巨大反響,很快傳遍整個中國。它由詞到曲,創作時間之短、作品反響之大,與其鮮明的民族風格(聲樂套曲)、時代精神和易于被民眾接受的形式密切聯系,這些元素是《黃河大合唱》成為經典的必要條件。
當然革命文藝經典的生成還要受物資條件制約,電影藝術就是代表。著名導演袁牧之,30年代在上海主創《桃李劫》(編劇兼主演)、《都市風光》、《馬路天使》三部故事片,其中《馬路天使》被稱為早期現實主義電影的登峰之作。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侵略,袁牧之放棄都市繁華,毅然來到延安,創建延安第一個電影機構——延安電影團,利用極其簡陋的設備拍攝了延安第一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但在延安,袁牧之沒有創作、導演出經典的故事片,連紀錄片也少之又少。延安時期物質的匱乏對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的限制不言而喻。
趙樹理的小說似乎更容易被當時的民眾所接受,其中最突出的元素是將混沌質樸的民俗變成文學創作題材,包括家庭、家族和鄉間社會的民俗、戀愛婚姻習俗等等。趙樹理還成功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他的《小二黑結婚》(1943)、《李有才板話》(1943)一經發表就產生了極大影響并最終成為文學經典。
丁玲的情況比較復雜,也更能夠代表延安時期文學經典的生成特點。由于時代環境和個人經歷等因素影響,丁玲延安時期的文學創作散文類(雜文、隨筆、通訊、報告文學等)寫作量明顯高于她所擅長的小說。從到達延安到創作出經典小說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花了十余年時間。與《黃河大合唱》和《白毛女》的產生和成為經典比較,丁玲創作出小說經典文本的時間長,其在民眾里的影響也遠不及《黃河大合唱》和《白毛女》。從受眾角度分析,文學作品需要個人閱讀,個體的、文化水平的以及大段閑暇時間的要求,在當時都極難滿足,也就極大地限制了文學作品的經典生成和廣泛傳播。因為在紅軍到達陜北之前,延安是全國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也是文化教育的荒原。陜甘寧邊區成立以后這種狀況有了很大改變,但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據《解放日報》統計,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的文盲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學齡兒童在學的只有四分之一⑦……物資的、文化的、地域的、時代的因素均作用于作家主體,形成復雜和多層面的力量,助推或者限制藝術經典的產生。另一方面,則是作家自己的因素影響了文學經典的生成。
丁玲文學創作的三個階段都有經典文本產生。如張揚女性覺醒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書寫戀愛與革命的小說《韋護》和表現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創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前,在延安曾經創作了《我在霞村的時候》等9篇有代表性的小說,我們不禁要問:延安文藝產生經典文學文本為何需要如此長的時間?用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體制特點加以說明恐怕過于簡單。有學者指出,丁玲延安時期的小說文本,存在個人文學話語和政治主流話語的游離,其矛盾之尖銳,調和矛盾之困難,似乎超過了其他藝術門類如繪畫、音樂和話劇等。
1982年,丁玲回憶說:“隨著當年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發展,蘇區就有了自己的革命文藝……當年蘇區文藝的特點是‘工農大眾文藝,是‘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在“工農大眾文藝”和“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的創作理念下,丁玲認為作家應自我定位為“帶有特殊性的藝術任務的戰斗員”,使作品成為偉大的藝術,不但屬于大眾,而且能結合和提高大眾的感情、思想、意志。在文藝大眾化的過程中,作家應深入民間“適合群眾”,而非迎合流俗“取媚群眾”,亦即“要使群眾在我們的影響和領導之下。組織起來,走向抗戰的路,建國的路”。丁玲所說的革命文藝一般是指革命文學。
在“普及”與“提高”的雙軸下,反映群眾生活的真實與鼓舞革命抗戰的熱情,成為當時作品的時代主旋律。但是文學尤其是小說這種文體,更加強調全方位地表現社會與人的生活,復雜細膩地展示人物的個性與心理世界。這種個體性與復雜性的凸顯,與戰爭時期單純、激昂、粗礪的審美風格相去甚遠,作家如丁玲有些無所適從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游移的話語中逐漸把握其間的藝術張力,沒有長時間的沉淀似乎很難解決,于是我們可以說,丁玲延安時期小說存在的兩種話語之間的游離,成為她革命文學經典文本生成的條件和必經之路。由此可見,革命文藝里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其他藝術形式仍然存在區別,也就是說,在同樣的外在條件下,不同文藝形式生成經典的過程和所依賴的條件不同,需要我們細致分析,區別對待。
延安文藝的13年,從革命文藝主體著眼,在文藝隊伍建設、文藝社團建設方面取得了驕人成績;在文藝經典生成方面,話劇、音樂實績似乎超過了文學。新中國成立后黨對文藝的領導方式、領導體制仍然沿用“延安模式”,可見延安文藝影響之巨大。只是從革命文藝主體和經典生成角度考察當年的延安文藝,我們所得到的啟迪恐怕也是復雜和多層面的。延安文藝的原生態本身就很復雜,從前期的“多元共生”到后期的倡導“工農兵方向”,存在一脈相承的聯系,革命戰爭年代對文藝的服從性和服務性的要求,助推或限制了文藝經典的生成,但不同藝術門類仍然存在差別,就是同一藝術門類的不同主體之間,這些差別也明顯存在,我們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