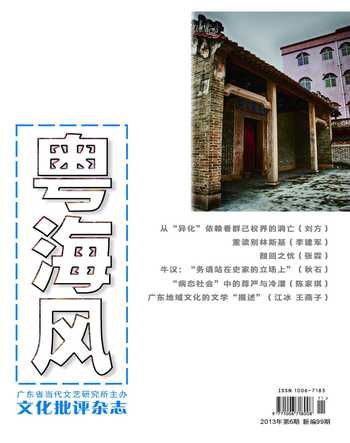誰的魯迅
曾子炳
陸建德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魯迅與許廣平的“三一八”記憶》(《東方早報》,2013年7月28日)是一篇觀點鮮明且作者主觀傾向很直接的文章,語言也極具個性,我研究魯迅對相關的文章自然有興趣,但初讀總難于進入,文中所談論的問題也是我關注和涉獵的,而讀這篇文章一方面給我以新鮮感,另一方面是覺得其中好多問題都是老生常談,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只是作者對之的敘述和解讀有點特別,與我對魯迅的認識以及對相關話題材料的掌握和理解之間總存在著落差,我在閱讀中時不時會碰到一些讓我驚異的話和字句,所以總是跳著讀。坦率地說我三次才看完此文,等到我準備寫這篇文章時才算是從頭到尾一次讀完此文。
當然我寫作此文主要是注意到近來魯迅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和傾向,其中有共性,需要正確面對,可以說這篇文章與當下對魯迅批評思潮的那種內在心理和理路是暗合的,自然魯迅是不需要我們去維護的,相反在我看來現在一些人對魯迅的批評本身就是其存在價值的一個體現,因為從中體現出的問題正是造成我們現實中很多困境的內因,自然也是他們對魯迅的批評使得這些問題得以暴露。
而這篇文章劉緒源已寫過商榷的文章:《有關“三一八”的幾點商榷》,其中涉及事實方面的認識我大多認同,除行文的需要以外,我主要側重反思陸文寫作的內在理路和寫法的問題,也可謂是讀心術的一種表現,而這也是陸先生寫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一個內在視角,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從自我的本位出發,來反思或者說質疑對應的魯迅的思想和內心,這是一種朝向心靈的冒險和探險。
“魯迅曾鼓動青年走掀翻桌子、廚房放把火的決絕道路,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見到熟人因此吃虧。”開首的這段話說得直白又似是而非,化用了魯迅不同文本中的話,前一句應該是來自于《燈下漫筆》中:“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我奇怪陸先生為什么不引原話而喜歡概括,而且其概括可能更多從個人的理解出發的,沒有辨析魯迅的本意以及其現實的對應性,乃至使得人們認為這是魯迅的一個思想原則或是精神追求。而魯迅的思想和觀念非常豐富,現在流行的很多理念,我們都可以從魯迅的各種言論中找到相應的內容,自然我們也可能找到很多相反的言論,比如說革命,魯迅自然是推崇革命的,但對于革命我們也可以找到魯迅很多質疑、批評的話語;我們還要注意到魯迅的觀念更是發展和變化的,不好一概而論。我做魯迅研究早期是敢言,現在越來越不敢就某個問題進行概括,像毛澤東那樣對魯迅的認識和評論也只有他可以這樣講,作為研究者自然是不妥的。我尤其注意到其中的“私情”,這往往會讓人想到男女之間的關系,或者是某種私心自用的現象,讀完后我意識到陸先生是強調前者。魯迅推崇“壕塹戰”是眾所周知的,他在給許廣平的第一封信中就亮明了其社會斗爭的這一方法,這和熟人或是私情沒有太多關系,至少在這里沒有體現出魯迅所謂的“自相矛盾”,只是在陸先生的眼中或者說他的這種寫法就使得魯迅看來是矛盾的了,他將魯迅的某句憤激之語概括成一個思想原則,相反將魯迅一種戰斗的方法歸結到“私情”——這樣的字句在文中總會那么咯眼地出現。
我看到陸先生用“賤奴”來形容楊蔭榆時又讓我失去了閱讀的興趣,我反復回憶魯迅或是許廣平用過這樣的詞匯來指稱楊蔭榆嗎?一時想不到,想來這不應是陸先生對楊蔭榆的認識而是強調這是魯迅他們的想法,魯迅會說楊蔭榆是“賤奴”嗎?即使在私信中我若看到的話也會覺得不快。
陸先生的思路大概是“三一八”慘案是段祺瑞政府有預謀的一次屠殺,同時作為游行主使者的國民黨也是事前知道并慫恿游行群眾去冒險,然后是在這個大前提下思考魯迅與許廣平的某種私情來。然而這一段歷史研究者甚眾,可謂眾說紛紜,難于定論,陸先生沒有介紹和論證就將之作為隱在的前提了,這可能也是我們作為后人來看待歷史的一個問題,所謂事后諸葛亮,這也體現在許廣平的思維之中,我們不能因此來預設當時以及當事人的真實想法和處境的,即使是段執政府也難于讓事件按照其預期來進行的,其中參與的個體以及現實的各種因素都會作用于其中。
按照這樣的思維陸先生就注意到魯迅的所謂思想的矛盾和內心的黑暗來。陸先生對魯迅的質疑可以概括為,煽動青年冒險的魯迅,在民國最黑暗的一天與許廣平“廝守”——這個詞也很奇怪,魯迅與許廣平此時確實確定了戀愛的關系,不過那是白天,家里有人,而且他們對之一直是隱晦的,不至于像現在的戀人那樣;因此我感到《魯迅與許廣平》中提供的材料是可疑的,我懷疑魯迅會毫無顧忌地與許廣平一同到學校去。
具體在史實上,陸先生質疑魯迅事先知道“三一八”游行,知道段執政府方面有鎮壓的準備,因此阻止許廣平參與游行,并在《記念劉和珍君》中隱瞞了這一點,其中可能體現出他們那一天的私情來。而這個問題劉先生已說得很清楚,我以為魯迅是什么時候知道“三一八”的游行,這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即使事先知道又何妨,他有隱瞞的必要嗎?談不上“出賣”,何況他寫作的《記念劉和珍君》在慘案的十幾天后,在沒有可靠的信息支持或是重大利害關系的情況下我們首先應該相信當事人自己的記憶,而不是依據我們現在了解的情況來推測其心態。孤證不立可謂是一個常識,而陸先生認為魯迅參加《國民新報》的一次編輯會就應知道第二天的游行,這是一廂情愿地推測,進而以這個側面的材料來否定當事人自己的意見和記憶乃至認為其中有隱情也過于大膽了。像他認為魯迅是女師大學潮的主使者,也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魯迅是在學潮的中間,受到許廣平的影響而介入,公開支持學生的,按講魯迅在女師大兼課,在最初他似乎并沒有太關注學潮的,研究證明新文化運動中的幾位主將在“五四運動”中都是很邊緣的,魯迅在生活中并非那種奔走于群眾運動,或是那種包打聽式的人物,同時那時正是學生和群眾運動風起云涌的時期,我們不可能預期其中的人對每一次運動都高度關注。
當然我們可以對魯迅和許廣平的某種說法和記憶存疑,但是我們不能按照我們對之的存疑來反思其心理和言行,這往往會將以后的推斷都建立在一個虛擬的基礎上,或者說構成一個循環論證的狀況,這與其說是我們按照現實以及對象的情況來推設,不如說是依照自我的心理和思維邏輯來自我肯定。
陸先生說“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1961)記載了‘三一八那天的經過。這段文字如送交1926年直面‘慘淡人生的魯迅審查,大概是不允公開發表的。‘真的猛士也不是一味的質直”。不知他看過《兩地書》沒有,這樣的思維和寫法委實讓人吃驚,因為許廣平真的想隱瞞這段經歷,她保持沉默即可,何苦要欲蓋彌彰呢。現在來看,許廣平的記錄確實是有些問題的,慘案發生在下午,魯迅在文章中的說法是可靠的,另外陸先生關于許廣平國民黨身份的質疑或許是有效的,我想她新中國成立后淡化個人的這一身份也情有可原,也可能是某種記憶有誤。退一步來說,即使陸先生所推論的都是事實,那么在這個事件中魯迅和許廣平做了什么傷害他人的事嗎?他們因此而愧疚也只是表明其道德感而已。在法律上我們對待可能的犯罪分子也要遵循疑罪從無的原則,為何在思想上對那些并沒有什么罪愆的人搞有罪推論呢。
我感到這可能是陸先生先預設了這樣的前提和結果,然后再找相關的證據,或者說也預設了他對魯迅的認識和態度,然后在魯迅的文字和經歷中尋找各種對應的內容,有時我感到陸先生不是關注事實是什么樣的,而是他想象魯迅是什么樣,或者說他希望讀者會將魯迅想象成什么樣的人,像是前面提到的“廝守”就是如此,而像這樣的話“在下午趕往學校的路上,他們心慌、腿軟,多少念頭掠過兩人的腦際!這是他們一生里最艱難而且難以言表的時刻。”簡直是在寫小說。劉先生希望對魯迅要有“同情之了解”,說得太委婉了。陸先生認為:“這次慘案是魯迅大理石雕像的黑色基座。”這句話也是很值得商榷的,這首先讓人想到“一將成名萬古枯”來,另外就是陸先生對之的質疑也可以看著挖掉魯迅雕像的座基,然而還是魯迅說得好“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所謂魯迅的雕像不過是后人打造的魯迅一個形象而已。
這讓我想到現在人們質疑的魯迅的一句話來:“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他們的理解大概就是魯迅認為國人很壞,可是他們忽略了后面的話:“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于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這就是現實往往出乎魯迅的預料之外,顯然不是魯迅把人想得太壞而是太好,所以他才會寫出這樣的話,相反我在陸先生這里感到是相反的,他們把他人以及現實想象得非常壞,當然他們可能并不認為這是壞,而是習以為常,甚至因此要求他人來,對魯迅的質疑和批評既是一例,認為政府會誘殺那些愛國的民眾,認為魯迅知道這樣的事,然后救了許廣平一命,其實正體現的是這種思維,而這一點是魯迅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所以會憤怒地寫下這樣的名句,而不是懷著愧疚的心理來積聚正義感。
讀完此文,陸先生的立場和意見我們是清楚的,但是他對事物的認識和態度卻是讓人費解的,對許廣平的認識如此,對魯迅也是,我想陸先生是不認同學生運動的,那么曾經熱血學運積極分子的退縮,不是一個好事情嗎?其實不然,他恰恰指責許廣平不該臨陣脫逃,看來最好像劉和珍那樣前仆后繼地去迎接敵人的子彈,這不正是他指責國民黨的思維嗎?而且更加惡劣,近乎他所認同段執政府的誘殺了。而這是魯迅最為反感的,難怪他對魯迅的理解往往相反。
總體來說,他是質疑和批評魯迅的,具體批評什么卻又難于把握,接近于魯迅所說的“可惡罪”,那就是對魯迅的各種表現都不滿——這讓我想起人們對魯迅的批評來,說他對什么都不滿,但又不提出正面的價值來,他似乎不滿于魯迅號召青年起來反抗,卻又責怪他不肯讓熟人去冒險,而在女師大的學潮中可謂是魯迅和許廣平那種“短兵相接”的斗爭,不知為何陸先生非但不以為然,更奇怪的是他不覺得章士釗非法免除魯迅的職位有問題,卻認為后來教育部提前讓魯迅復職就體現出“政府的瀆職無能,無以復加”。后來我想大概在兩個情形下,他們是不會批評的,一個是魯迅“碰”死于敵人的刺刀上;其次就是埋頭吃飯,專造個人舒服的世界,不過如此也就沒有魯迅這個人物了。
還是回到開頭那句話,因為其中不是體現出魯迅的矛盾,而是他的真實和正常以及思想通透的表現,因為這正好與段執政府、國民黨以及陸先生思維不同和對應之處,魯迅是不滿現狀,渴望改革的,但是這種認識、思想與實踐之間是不同的,魯迅推崇革命或是對革命的質疑只有在具體的語境中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但其中貫穿的是他對生命的尊重和思想的一貫性,其中心就是“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在不同的環境中就會表現出不同的言行來,我們認識不到魯迅的真實或是由于我們自身存在和思維與魯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就會自然地將魯迅針對不同環境中所作的不同的認識當作其矛盾的體現。像是魯迅很早就剪辮,但是卻不主張他的學生剪辮,這體現出他深厚的愛以及那種道德智慧,像是某些國民黨人的表現可能是自己不剪辮而慫恿他人來剪辮。
魯迅《在鐘樓上》說過一段有關革命的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么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里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拼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正體現出他的這種思維和個性,希望陸先生以及一些人能夠認真讀讀,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健康人的思維和心理。
魯迅的寫作《記念劉和珍君》也是近乎那種“短兵相接”的斗爭。陸先生卻質疑:“如果魯迅不把自己放進慘淡人生的宏大圖景,直面之后,還是收獲不到與他的天才相稱的洞察。”而在我看來,魯迅在“三一八”中的經歷以及他的所思所想,都是從自我存在的真實出發的,也是忠實于個人的思想和社會追求的;陸先生在認識魯迅的過程中也是先虛擬了一個奮勇直前的斗士形象之后,再來看待魯迅真實的表現,更確切地說陸先生在不滿于魯迅“煽動青年冒險”的前提下要求魯迅應去迎接敵人的子彈,否則就是“茍活”,此時他應該反思和直面個人“內心的黑暗”。這里真實的魯迅或者說活生生的魯迅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魯迅能夠滿足和實現人們對之的期待和要求。
我孤陋寡聞,最初我以為陸先生是研究陳寅恪的,我還奇怪他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后來我一查注意到陸先生曾留學英國,研究外國文學,這讓我想到魯迅和陳西瀅的爭論,有一種時光倒錯之感,現在人們也常說什么留學法日和留學英美者的對立,難免陸先生重新看待這些事件時受到自己教育背景的作用乃至有情感的因素,這樣我感到文中的一些問題不是深文周納,而只是無心之失,這也是促使我寫作此文的一個原因。而陳西瀅或是楊蔭榆,我并非因為魯迅批評過,就認為她們是壞人,相反她們在學者中應該是不錯的,只是在魯迅這里才成為問題的——我們在看待魯迅的批判以及對應的人物應該有這樣辯證的眼光,魯迅的批判一方面是從觀念和民族性上著眼的,另外就是一般人對應于魯迅來說往往都會相對地低劣一些的,這不僅體現在道德水準和思想認識的水平,也在于具體的爭論的過程中,他們的表現往往有所欠缺。這與爭論中陳西瀅站在權貴的立場上卻極力嘲諷魯迅的官員身份,或是梁實秋不知自己是哪個資本家的走狗時卻暗示魯迅拿盧布一樣,而他們這樣的表現就正印證了魯迅對之的批判,只是他們自己不自覺吧。
魯迅是豐富、復雜和博大的,這樣我們對之的認識自然是多樣的,同時也因此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對魯迅的認識不過是盲人摸象,他們摸到什么就說什么也不成為問題,問題在于現在人們對魯迅的質疑和批評,不是說魯迅不能質疑和批評,我特別期待能夠出現超越魯迅的人物,這才意味著進步,魯迅本人希望其作品早點被人忘記,希望自己速朽,這樣才意味著他所痛苦和批判的現象得到了克服。另外我們根據個人的素養以及所獲得的資料形成對魯迅的認識與我們按照自我的心理乃至是需要對魯迅的要求和塑造之間是本質上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的,而現在很多魯迅的研究往往是后者。很多人無法分清其中的差異,記得一位算得上學者的人,在一個公共論壇上質疑魯迅的批判,說他只批判老百姓、一般文人,而不敢批判政府,批判蔣介石等,首先這不是事實,《記念劉和珍君》就是批判政府,所以他們一方面厭惡魯迅的批判,另一方面卻又要求魯迅去批判獨裁者,這也不過是把人引入死地的思維和心理。
當然也可能是他們先將魯迅對象化,然后以魯迅生活中的表現來質疑和批評他們所預想的魯迅,這一點像自相矛盾的故事中那個人的表現,只是如此在他們看來就成為魯迅的矛盾和問題了,而在這個過程中真實的魯迅是不在場的,或者說成為一個鏡像性的存在。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看到魯迅有什么難言之隱或是自相矛盾之處,這可能只是認知者與其對象悖論關系或者是個人內在悖論和智力問題的體現。很多對魯迅的認識不過是先虛擬一個魯迅的鏡像來批評,這不過是個人左右互搏的表現,然而他們往往將自我的魯迅作為魯迅的真實,其實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只是起到某種鏡面的作用,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個人的影像不僅是身體上,也是心理、思想和精神上的,人們若將在這個鏡面中的自己來當作魯迅來批評的話就產生了我所批評的現象,這一點他們自然是難以自覺,而需要批評和指出的,魯迅的文章其部分意義也在于此,我想現在人們對魯迅質疑的一個因素就是難于接受在魯迅鏡像世界中的自我真實。而在這樣的處境中高貴的做法是自我修煉,其次是學會藏拙,然后才是那種不自覺的掩耳方式。
現在我經常看到有些質疑魯迅“偏激”的人,卻以偏執的態度乃至是罔顧事實來顛倒黑白,就好比阿Q批評魯迅不該推崇和踐行改革一般,其中體現出立場決定一切,非黑即白的思維,其根本還是功利使然,這種思維乃至是輿論的盛行,其中體現出我們民族心智的病態,與最近民間戾氣的爆發,對應的是輿論和一些思想的戾氣往往被忽略了,而我覺得后者才是根因,這可能正是需要魯迅并產生魯迅的環境。我們要養成以理性、平和和客觀的心態和智慧來認識和對待任何問題,若如此任何問題都不會對我們造成困擾,而學會尊重有價值的事物也是我們自尊、自愛的表現。
我們不要以為將魯迅拉下神壇并踩上一腳,我們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這或許是我們正站在死亡上,站在深淵邊緣,我希望看到人們能夠踏著先人的足跡前行,而不是踏著他們的身體和功績向著他們的來路狂奔而去,希望大家不要去做那個裸奔的小孩子。
(作者單位:上海市金山區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