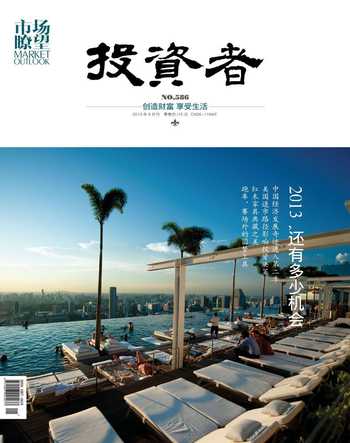美國退市路徑影響投資決策
美聯儲并沒有按市場原來的預期,于9月底實施第一次縮減量寬的舉動,著實出乎市場預料。
這再次反應出今年的“政策市”特點。進入2013年的下半年,香港機構投資者對于未來的不確定并不比上半年要少一些。習慣于看方向操作的基金經理希望通過分析美歐經濟以及美聯儲的利率政策來制訂出中長期的策略安排。但是下半年卻注定不平靜,無論是經濟前景還是美聯儲的退市措施,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從基本面來看,大部分宏觀分析師認為,全球經濟的大方向是在復蘇,但各國的復蘇程度大相徑庭:美國可說是持續復蘇,歐洲充其量只能說止跌,還難斷言會有反彈,日本仍然需要加大安倍經濟學的注資劑量,才有可能驅升通脹;而中國雖然擺脫硬著陸的風險,政府所倡導的經濟轉型卻進展緩慢,這令國際投資者擔憂,中國能否既保持經濟增長,又同時實現有效的轉型。
不過對于金融市場來說,美聯儲的退市路徑卻是影響各種投資工具的最重要因素。
分析師們都認為,美聯儲退市是板上釘釘的事,但不確定的因素卻是一大堆:最重要的是退市路徑會怎么安排,這涉及對于金融產品價格的沖擊究竟是有方向的持續性,還是毫無方向感的間歇性影響。
出于降低本國失業率的目標,美聯儲實施的退市路徑與失業率緊密相關——這給基金經理們出了一道難題,因為美國經濟雖然已經步入復蘇軌道,然而還是時不時出現波動,失業率的指標也有可能會不時出現變化。
因此,9月注定是一個惹人關注的月份。月初澳大利亞選舉,月末德國選舉,9月第3周是美聯儲議息會議來得重要——全世界投資者都在看,美聯儲究竟會否推出退出量寬的路徑圖,以及如何減少購債規模。
投資者原先預期,美聯儲至少會開始償試小幅度的退出安排,但是最終美聯儲并沒有宣布降低購買國債規模的決定,這使得全球QE盛宴的退席時間再次延后。
全球量寬將終結
在深入觀察市場的反映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印鈔活動。
五年前的9月15日,雷曼銀行倒閉,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直接后果是全球金融市場信心幾近崩潰。隨之而來的是全球股市暴跌,香港恒生指數在9月16日,一天之內便削去1052點,跌至18300點,比2007年10月30日的歷史高位31638點削去近42%。
為了救市,全球央行罕有地攜手開閘放水,美歐六大央行聯手向市場注資2.56萬億美元。為了令銀行家們避免再被互不信任的情緒所充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更是放出“不惜開著直升機灑錢”的豪言。此外,全球金融市場開始進入人類史上規模最大,同時也歷時最漫長的量化寬松(QE)年代。
回頭來看,上述情況均已經成為或正成為歷史。不可否認的是,量寬在美國已經獲得部分成功,至少美國經濟已經出現持續復蘇的跡象。在上述背景下,作為全球量寬之“元兇”,美聯儲開始放風,準備在今年末或明年初開始有序縮減購買美債的規模。
在香港,不少基金經理和宏觀策略師們均認為,美聯儲在今年底前開始減債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債券市場已經提前反應了上述預期——10年期的美國國債的孳息率狂飚便是明證。
但顯然基金經理們對于美聯儲如何實施減債過程仍然存有頗多疑惑。對美聯儲進行預測其實是一門半帶賭性的技術活,基金經理不得不做好兩手準備,如果發現自己對美聯儲的退出路徑判斷失誤,需要及時調整倉位。
減QE路徑影響資產價格
基金對于美聯儲退市路徑的判斷主要依據兩個重要變量,第一,誰將接任即將退位的伯南克;第二,退市是按連續性操作還是間歇性操作。
對于第一個問題,如果是強硬派侯選人上臺,極有可能會在9月當月便開始實施退出方案,減少購債規模,并加速退市的步伐;而如果是鴿派人物上臺,則市場有望得到更多的適應空間。
被視為鷹派人物的美國前財長薩穆斯9月中宣布退選美聯儲主席之職之后,大家的疑慮更主要落在第二個問題上。
對于將來的退市路徑,有美資對沖基金認為,停止購買美債可能不一定會太早開始實施,主要原因是,作為政策者,可能更希望看到政策有連續性,因此極有可能會剛開始時減少購買的量較大,而后再均勻地按月實施。
另一派觀點則認為,美聯儲有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間歇性地減少購債的步伐。持這種觀點無意于認定美聯儲會被經濟數據牽著走。這樣做實際上有一個弊端,一旦經濟復蘇受阻時,美聯儲可能不得不再增加購買美債的規模,而不是減少購債,但一旦在減少購債后又突然增加購債,會向投資者釋放出混亂的信號。通常持這一派觀點的機構投資者會認為,美國經濟恢復情況已經較為穩定,為了配合這種持續性的經濟復蘇,美聯儲將會采用相應的持續縮減退出規模的方式來實施量寬的退出政策。
機會來臨?
上述兩種不同的路徑判斷,會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投資策略。顯然,如果美聯儲采用持續性的退市步伐,會令投資者形成持續的升息預期,債券價格將遭受打擊;但如果是采取間歇性的退出路徑,股票市場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更大,這會令價格波動加劇。
在9月中美聯儲未如預期減少購債規模后,全球資產價格很快出現較大波動。最明顯的是日股沖高(因預期流動性將不會太快流出日本),而美國的地產信托基金、公共事業等高派息類股則出現大幅上揚(因繼續QE規模將抑制市場利率,而該類資產收益率優于債券)。但之后后者又出現較大調整。這種波動預示著市場未來一段時間仍然是兩派觀點的角力場。
不過從大方向來看,上述兩種路徑都預示債券市場的資金將會流出,而股票市場將會受益。有香港機構已經從這一角度開始著手布局。
美國首當其沖,可能在退出量寬初期仍然會受惠。主要原因是流出債券市場的資金極有可能會首先進入美股市場。投資者在“相對回報”概念之下,會選擇更有回報的投資工具。
近期美股屢創新高,便是這種預期的反映。不過在美股指數進入高位后,基金可能會先行獲利,轉一下頭寸安排,因此美股將會出現調整。
與美元掛鉤的香港市場也有望受惠。和那些資金不斷外資的東南亞經濟體不同,香港資本市場自由度極高,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就使得流出美債的資金在選擇新興市場的時候,往往會把香港作為資金在境外的第一站。
有人認為前不久超賣的東南亞新興市場也有可能受惠。對此觀點,業界并非完全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外匯儲蓄良莠不齊,那些經常項目出現虧損的國家,仍然有可能在下階段成為對沖基金阻擊的目的——而日本為了強化前期日元貶值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極有可能會進一步令貨幣貶值,屆時東南亞國家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