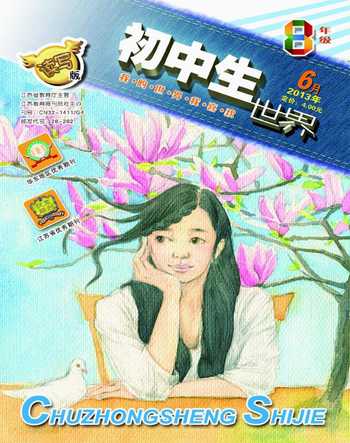守候世界上最漫長的實驗
付雁南
如果說“時間就是金錢”,那這個位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玻璃漏斗無疑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實驗裝置。
86年前,一位名叫托馬斯·帕內爾的物理學家為了向學生證明“瀝青是液體而不是固體”,設計了這個實驗。他將瀝青加熱,倒入一個封口的玻璃漏斗。等到瀝青完全凝固之后,他將漏斗的下端切開,開始記錄每一滴瀝青滴落的時間。
如果補充一些數據,這個實驗也許就不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為了等待瀝青完全凝固,帕內爾花費了3年時間;而到第一滴瀝青滴落,他又耗費了8年。事實上,直到60歲去世那年,他只等到了3滴滴落的瀝青。
隨后接管實驗的另一位物理學家約翰·梅因斯通,用50多年的時間,也只迎來了5滴滴落的瀝青。盡管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5滴“來之不易”的瀝青,全部被他郁悶地錯過了。
這個持續了86年的實驗,已經被評為“世界上最長的實驗室實驗”,不過,在梅因斯通看來,實驗還遠遠沒到完結的時候,“要等到實驗完成,至少還需要100年”。
盯著瀝青實驗裝置的人們,很容易產生時間靜止的錯覺。那些堅硬的、可以用榔頭輕易敲碎的瀝青,以匪夷所思的緩慢速度流過短短的漏斗柄——通常情況下,這段不到10厘米的路程,耗費的時間要超過10年。
一些昆士蘭大學的校友領著兒女、孫子重回學校的時候,常常會感慨實驗裝置“和幾十年前沒什么變化”;而那些通過網絡攝像頭觀看實驗的人,也常常會發現,相隔幾個月的畫面,幾乎看不出任何不同。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看到瀝青滴落的瞬間。”梅因斯通說,“事實上,從實驗開始到現在的80多年,還沒有人真正看到過這一時刻。” 過去幾十年,梅因斯通經歷了5滴瀝青的滴落,卻因為種種原因,總是和那些瞬間擦肩而過。
最接近的一次發生在1979年,當時,那個像淚滴一樣的瀝青滴和漏斗的連接處已經變成了一根細絲。梅因斯通觀察了一會兒,覺得要等到它滴下來,至少還要一天時間。結果,等他第二天來到實驗室,第5滴瀝青已經掉進了燒杯里。
自從1961年接手這個實驗,梅因斯通已經幾次重演了這樣擦肩而過的遺憾。1962年,當第4滴瀝青搖搖欲墜的時候,當時只有27歲的梅因斯通剛剛結婚,正和妻子一起出門度了一個短暫的蜜月。結果,等他蜜月回來,嶄新的瀝青滴已經穩穩地落在了燒杯底上。
當1988年的第7滴瀝青再次被錯過之后,梅因斯通決定借助科技的力量。他在實驗裝置旁邊擺上了一個攝像頭,24小時監控實驗進展。
2000年11月,當第8滴瀝青即將滴落的時候,梅因斯通心安理得地去了倫敦。他說,自己當時覺得“毫無壓力”,“畢竟還有一個攝像頭在盯著它嘛”!結果,當瀝青真的掉落的時候,梅因斯通收到了兩封讓他悲喜交集的郵件。第一封的內容很簡單:“瀝青掉下來了!”而第二封的內容則是:“存儲設備出現了故障,攝像頭拍攝的滴落畫面沒有保存下來。”
直到今天,梅因斯通還能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有多失望。他回到澳大利亞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升級監控系統,并且在實驗設備的周圍擺上了3個獨立的攝像頭。
如今,就像每一個負責任的科學家一樣,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物理系教授梅因斯通每天都在嚴密監控自己的實驗裝置。無論工作日還是周末,他都要堅持每天觀測實驗數據,實驗室的技術人員也會每天向他匯報實驗進展。當然,他也會在想起來的時候隨時查看網絡攝像頭的畫面。
在“最長的實驗”變得著名之后,梅因斯通在很多場合都會被要求回答同一個問題:“你覺得第9滴瀝青會在什么時候掉下來?”
而他每次的回答也完全一致:“我真的不知道。”這位物理學家解釋說,瀝青的掉落時間取決于在當地平均室溫的環境下,瀝青表面的黏度系數。他同時聲稱,這個持續了80余年的實驗并不能簡單地說明“瀝青是液體而非固體”,更準確的說法是,瀝青是一種相態復雜的混合物。
梅因斯通說,隨著漏斗里剩余的瀝青越來越少,瀝青滴落的速度也會越來越緩慢。從監控錄像的畫面來看,這滴讓人們等待了12年的瀝青,已經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淚滴形”,仿佛隨時都會滴落到燒杯里。
梅因斯通喜歡用富有哲理的言辭來評價這個實驗。他說:“自然界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的不可預測,這也是我們生活的調味品。”
(選自《中國青年報》2013年1月9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