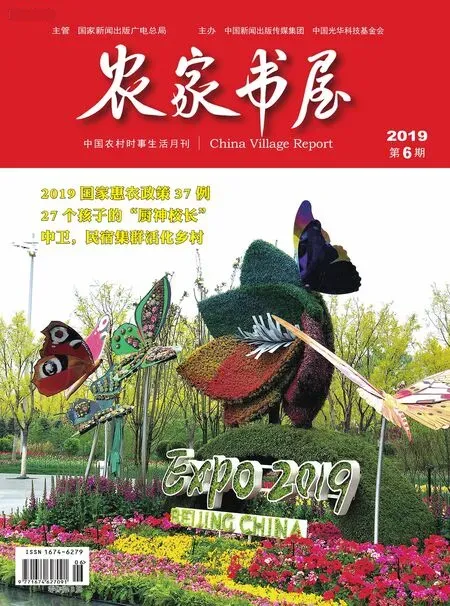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知多少?
白紅義
改革開放30年,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長大成人,成為新一代農民工。面對父輩候鳥一樣家在農村、人在城市的生活,新一代農民工渴望成為市民,把家搬到城市里,子女在城市的學校接受教育。然而,他們舉家進城的門檻是那樣的高,住房、教育、醫療是一個個攔路虎,一般的農民工家庭難以跨越。
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在哪里?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講師張國勝博士在其《中國農民工市民化——社會成本視角的研究》一書中指出,農民工市民化進展的緩慢,表面上是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土地制度等二元體制改革的滯后,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改革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應的社會成本。
何為“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
2005年,中國科學院估計每進入城市一個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約為1.5萬元。2006年,建設部調研組稱,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設施配套費,小城市為2萬元,中等城市為3萬元,大城市為6萬元,特大城市為10萬元(不含運行和管理成本)。
2009年,張國勝認為,東部沿海地區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10萬元與9萬元,內陸地區的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6萬元與5萬元。
2010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認為中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201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指出,推動城鎮化,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中的定義,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最終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轉變為當地市民的過程。因此,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就是指實現農民工在城鎮定居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投入,也即要讓農民工享有與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項權利和公共服務所需的公共投入。
該報告主要討論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需要政府投入的成本。據報告執筆人金三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員)、許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研究員)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介紹,課題組在測算時主要包括六項成本: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成本;醫療保障成本;養老保險成本;民政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障支出;社會管理費用;保障性住房支出。
政府如何支付農民工市民化成本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組對重慶、武漢、鄭州和嘉興四個城市的實地調研,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總共約8萬元左右。其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會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約為560元。
報告還指出,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妥善安排,不會成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
該報告執筆人金三林和許召元稱,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而是伴隨著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
短期來看,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遠期來看,養老保險補貼是主要支出。其中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總成本的1/3左右,養老保險補貼約占總成本的40%-50%,但養老保險補貼受養老金支出政策的影響很大。
金三林和許召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農民工市民化成本中有不少內容已經隨著我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部分解決了。再比如在8萬元的成本中,有3至4萬元是政府對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后的補差(即平均來看,農民工領取的養老保險金要高于企業和個人所繳納的總額),而這部分費用無論是不是推進市民化,按照目前的政策以后政府都是需要承擔的,從嚴格意義上并不能看作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其他的城市管理費用也是如此,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這部分管理費用實際已經發生了。”
另據課題組的調研,如果不考慮養老保險的遠期支出,則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為2.4萬元(主要是教育和住房保障,包括新建學校),以及主要用于低保等民政補助和公共管理(含市政建設)的年度支付約560元左右。
金三林和許召元指出,“由于目前的農民工已經享受部分公共服務,因此農民工市民化所需要增加的支出比上述測算結果更小,這樣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只要積極籌劃,特別是做好未來的風險防范(主要是養老金體系),政府完全有能力進一步加快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讓農民工也更好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