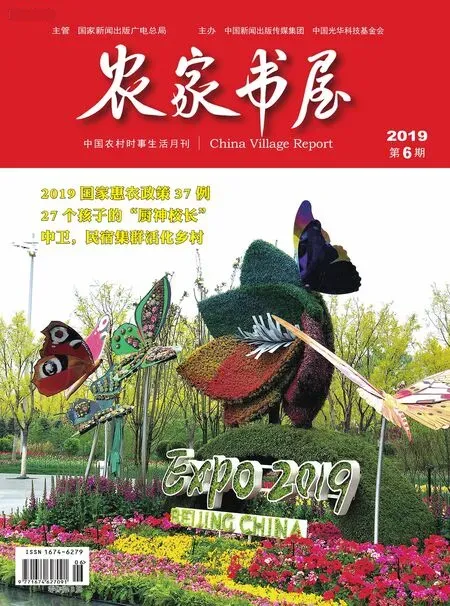圓桌
本期主題:農民工子女與職業教育
背景: 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的規模、結構和辦學條件得到快速發展,但傳統職業教育中專業定位滯后、生源差、師資弱等問題依然存在,職業教育落后和專業技術人才奇缺的局面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難題。
編者:有學者認為農民工子女進城后通過職業教育掌握技術,既利用了富余的職業教育資源,還可填補技工缺口;也有人認為不應將農民工子女往職業教育的路上“趕”,討論較多的有社會階層固化、貧困的沿襲等問題。鑒于職業教育的發展程度和國民認知,無論是地方政府就地中高考方案,還是學者提出的農民工子女與職業教育相結合的建議,或許都有爭議。
北京交通大學查建中教授:所有教育都應是職業教育
美國的杜威教授說過一句話:“用昨天的方法從事今天的教學,是對孩子們明天的剝奪”,這個話很尖銳,卻也一針見血。面向職場的教育無論是否關乎“職業”都應是職業教育,無非是針對職場各層次人才的培養而已。大家知道,長三江、珠三角,熟練工人一度緊缺,產業轉型升級階段尤其需要新一代技工。當前社會正在拒絕使用學校的畢業生,并非產業不需要人,而是培養的人才“質量”有問題。
教育環境脫離職場環境,必將在理念、機制、師資、課程體系,教學方法評估各方面都產生不同程度的問題。“學以求知,學以致用,學以共處,學以做人”是一個普世教育準則,“學以改變”則是新目標,每個人都要學習掌握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的能力。現在的專業教育中相當多的師資都是學校到學校,沒有產業經驗和職場經驗怎么培養職場未來的接班人?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郭宇寬:健全制度,尊重匠人
前段時間有網友議論,說郭德綱和趙本山要徒弟向他們拜師磕頭。且不論真假,我想這體現了職業傳承的內在規律,教會徒弟餓死師傅,職業教育需要一套制度保證技藝和職業的傳承,以保護教、學雙方的積極性。傳統的職業傳承靠血緣和學徒制度來維持,比如學炒菜,不用考大學讀博士,跟著師傅慢慢學習那點小竅門,但師傅不輕易教完。過去常講當學徒要給師娘倒三年洗腳水,做三年學徒才慢慢能學出來。
中國歷史上有很強的尊重工匠和技藝的傳統,如景德鎮的瓷器工業之所以興盛,正是依賴工匠傳承的體系才得以在工藝上有突破。此后,當燒瓷的工藝、瓷的裂變、釉彩的配方等不再被重視,瓷器工藝便日漸衰落。有一句老話,今天要重新發掘,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借此反省中國的職業教育,包括流動人口弱勢群體未來的發展,朝尊重一個職業的內在規律的方向想,可能會發展得更好一點。
北京現代職業學校合作辦學辦公室主任武舒軍:職業教育從娃娃抓起
北京現代職業學校重視實際技能高于理論知識,很符合農民工子女的需要,2003年起至今學校已向北京市的煤、水、電、油、糧食、運輸、物流等基礎產業輸送了近3000名員工。我認為,農民工子女在中職發展要比上高中、大學發展快,這也是一條捷徑。京石高速出京方向有兩個加油站,其站長就是我們的學生,她今年不到30歲,月薪至少一萬元。
據我觀察,最初孩子從農村來到城市并不適應,時間長了就敢說敢笑了,他們對學習的渴望似乎更強烈。工作期間出成績的往往是農村學生。為什么?他急于改變現狀。我們最初招的合作辦學的學生來自湖南湘西,畢業后干物流、飯店服務管理、電子商務,這幾年處境有了很大改善,有人甚至返鄉創業了。2008年,有個學生在北京干了三年后回到吉首進了一家運輸公司,當地人還不了解物流,他給經理提建議成立物流公司,從湖南長沙攬業務。如今,他們的業務拓展到常德、懷化。我想,職業學校的老師能不能到小學、初中、高中開展職業指導?職業選對了,關乎孩子的一生。
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衛宏:掃除社區服務的空白
在北京市南部的一個區縣,往年初中畢業生里大概有2000多人是農民工隨遷子女,我想,我們能否嘗試在社區開展職業教育?目前,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社區的服務還是空白。以我所在的“農民之子”社團為例, 2009年起在北京天通苑半塔村的社區設了圖書室。每天下午三、四點鐘放學后,有二三十個孩子到社區里讀書;周末,很多大學生自愿給孩子提供輔導并組織興趣小組活動。
無論學習好壞,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需要職業教育,因此,社會公益機構可以深入到需要職業教育的家庭或者孩子身邊,深化社會服務,提供職業指導、職業咨詢,乃至把企業用人信息和社區教育相結合。將來有機會,我們希望和專業性的職業學校或是社區學院開展更多合作,把更豐富多樣的社區服務內容(包括職業教育),帶到孩子身邊。
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社會工作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盧磊:職業教育的核心是人
我認為職業教育應包括技術教育和全人教育,核心在于公民意識培養和能力建設,如溝通能力、跟同事相處的能力、享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遇到問題時懂得求助及反饋等。多關注城鄉結合部社區、流動人口聚居在城市的社區,或者農村的社區,我想,社區化依托于民間組織或系統的社區組織,或將超越以學校為主體的服務模式,北京有社區嘗試把農民工的公共服務納入其中,如“工友之家”面向全國的創業培訓中心,針對需求提供職業培訓服務,就是一種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對接。在深圳、東莞和珠海,偌大的工業園區有十幾萬人卻鮮有報刊亭。我在珠海工業區調研發現,有個工友待了十多年依然是普工,他不懂得如何更好地發展自我,也沒有太多上升的渠道和空間。對這個群體來說,什么樣的東西是本質的、可持續的?可能誰都沒有答案。
民間公益機構“打工之友”創建者張志強:三個孩子的選擇
我有兩個外甥,一個初中畢業以后學做涼菜,現在月薪2000元,另一個什么都沒學,當營業員,月薪2500元還有提成。我的孩子是留守兒童,他在北京的中職學校讀了財會專業,學校安排實習時月薪1200元,今年漲到1800元。職業教育對這些孩子們到底有沒有用,這是個問題。我覺得,職業學校傳授給孩子的技能跟實際工作并不完全匹配。
我們一直告訴孩子要上大學跳出龍門,但實況恐非如此,上大學是一個高成本的付出,每年約有800萬大學畢業生在找工作。就業難和技工荒的難題并存其實缺乏最基本的支持,現在有很多魚龍混雜的培訓機構,鋪天蓋地全是短期培訓學校,因此應該先讓父母和孩子建立對職業學校的正確認知,同時,職業學校也應加強就業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