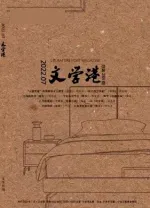母親的牡蠣
戴巧珍
牡蠣在我們家鄉西店叫蠣黃。這個軟體生物內柔外剛,愛煞了世間人。我常拿它與母親相比。
它的殼像一個放大了的指甲背,或者說像一面縮小了的蒲扇。拿一把尖利的蠣刀對準它的殼頂撬開了,它淡藍色的肉體泛著銀色的光芒,掬著一汪汁水,打著褶皺的裙邊在水波里微微蕩漾。用蠣刀把牡蠣的筋割斷了,拿起蠣殼連水帶肉往嘴里傾倒,一陣讓舌尖打顫的鮮味在嘴里漾開來,沖擊你身上的每個細胞,讓人忍不住皺眉、嘖嘴,深深地贊嘆。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就有這樣的細節描寫:十八世紀高貴的法國婦女舉止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著牡蠣,頭稍向前伸,免得弄臟長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動,就把汁水吸進去,牡蠣殼扔到海里。”除了美食,據說它還滋陰補陽,連《本草綱目》都載著。它的殼經火焙成灰,是絕好的砌墻材料,可與石灰媲美。
我們家就在海邊,海濤聲常常入了我的夢,海鷗常常立在我家的屋檐上。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農村實行農田承包到戶之后,我們家也從隊里承包了一些牡蠣養殖。可是,父親一直病著,早把家里戳出了個花錢的大窟窿,僅靠這點收入遠遠不夠。母親打算擴大牡蠣養殖。這個決定讓她墜入了一個痛苦的深淵。
母親長相姣好,人稱“白洋襪”,因為有一次她入田插秧,雪白的雙腿讓過路人誤以為穿著白洋襪。沒有出嫁之前,一直是外婆的掌上明珠。但她為了愛情,為了兒女,她毅然決然地變了。而牡蠣的生存能力酷似我母親。據說,牡蠣產卵大都在大潮汛期間進行。海潮洶涌,牡蠣迎潮而上,勇敢地生兒育女。在合適的水溫下受精卵不到一天即發育成幼蟲,幼蟲一直在海水里游呵游,二十天左右,柔軟的幼蟲居然長成了硬硬的外殼。這個時候,生存的智慧,促使它們找到附著的海邊石頭——漲潮時浸入水中,退潮時凸出水面。有海水浸潤時,可盡情的吸收水中的浮生物等營養,與游過的魚蝦嬉戲歡鬧;凸出水面時,可盡情地呼吸新鮮空氣,觀賞日月星辰花開花落。
牡蠣有多好的依靠呵,柔弱的母親真想有一個依靠——她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牡蠣身上。
擴大生產就得花大價錢買蠣石。蠣石是從奉化買的。母親舍不得租拖拉機的錢,就與病弱的父親一趟一趟用手拉車運輸。母親在前面拉,父親在后面推。早上三四點出發,回來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這樣的運輸每年得持續半個月。可以這樣說,每一塊蠣石,都沾上了父母的心血汗水。
可與運蠣石相比,養牡蠣、收牡蠣的艱辛絲毫不遜色。
冬季收蠣時,每晚午夜剛過,天地滴水成冰,母親搓了兩個飯團子,與父親一起撐著竹排出發去海里。他們要在天亮之前乘著漲潮把大海深處的蠣石運到海灘邊上。然后顧不上喝口熱水,一扁擔一扁擔地把蠣石運到蠣棚里堆成一座高山。而這些,其他婦女是不用做的。
之后,父親可以回家休息,而母親則要挑蠣肉。幾年下來,母親練成了一副好手藝。抓一塊蠣石在條凳上,手起刀落,蠣殼打開,蠣肉就如跳水的運動員一樣翻飛著落入旁邊的蠣肉桶中。隨著高山般的蠣石從母親身體的一側到另一側,母親一天的苦役方才告一段落。
蠣棚是簡陋的稻草棚,冬日的海風常常像凄厲的餓鬼一般眥著嘹牙嘯叫著撲向母親。特別遭罪的是母親的那雙手。自從開始養蠣,她原先細嫩白皙的手就像一坨破肉一樣,一個冬天滴滴嗒嗒地往下掉皮肉和血珠子。那些寒風卻變本加厲地撕咬這些傷口和裸露的肌膚,母親的手背會像發酵的饅頭一樣腫脹起來,變得清亮、透明,皮下的血管清晰可見,仿佛一碰即可化為一攤膿水。我經常為母親的手流淚,為母親的手祈禱。
可是母親咬著牙堅持,一年一年的,我從沒聽她叫一聲苦。每到收蠣賣蠣季節,母親用腫脹得像紅蘿卜一樣的手指頭數著大小不一的票子,想到這些票子是實實在在屬于自己的,它們可以讓丈夫的醫藥費有了著落,孩子的學費無憂,買谷種、莊稼秧子的費用有了保障,她臉上就漾出欣慰的、讓我終生難忘的笑容。
收成好時,一季有三五百元的收入,這筆錢在當時來說,是比較可觀的。可是,這些錢卻沒有完全利惠于我們。看看我們每年過年的菜:海鮮除了蠣肉,魚蝦極少上桌,豬雞鴨肉雖是有的,卻是一丁點。與村里一般人家比,十分的寒酸。家里孩子僅我們姐弟倆,可是從沒見大人給過壓歲錢。過年的新衣裳輪流做,得了今年就沒有明年的。我穿小的衣裳有時候就直接讓弟弟穿。
養牡蠣得來的錢呢?看著我們疑惑的目光,母親說:“細水長流!現在把蠣石投放得多一些,到時候養蠣得來的錢就多了,我們家就有好日子過了!”母親說這話時,兩眼灼灼有光如火炬,父親笑著點頭,我和弟弟的心都被她的宏偉夢想點燃了,我們乖巧得不向母親要錢買一根棒棒糖,卻從此都不怕困難,年年把我們的學習獎狀貼在墻上。
就這樣,每年養蠣純收入的三分之二,全買了蠣石。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蠣石一年年增多,養蠣賺的錢越來越多,可我家的生活水平依然老樣。
然而在一九九二年的冬天,積勞成疾的母親躺到了病床上,而此時,我們家在海田上的蠣石數量達到了我們剛承包時的十倍,成為全村之最。這些沉重腥咸、大小不一、被母親的手溫一年年暖過、而今仍在盼望主人的石頭是母親歷年的心血見證,但母親卻已沒有力氣再侍弄它們。它們像失去依靠的孩子一樣先是流落到父親的兄弟那里。后來,伯父也嫌養蠣太苦,把它們放棄了。母親送寶貝一樣轉送他人,又幾易其主。到九十年代中期,村里已無幾人還從事這苦營生。忽有一日,村里剩下的鐵桿蠣迷竟石破天驚地使用了廢棄的汽車輪胎來養蠣。據說這種輪胎牡蠣不僅運輸方便,產量還很高。
母親心肝一樣的光溜溜的石頭最終沉沒于大海,而母親坎坷跌宕的養蠣生涯也永遠地沉隱于歲月深處。
唯一讓母親欣慰的是:母親與父親彼此珍惜,用蠣石砌成了愛的堡壘;兒女成才,我與弟弟都學習成績優秀,長大后各自有了幸福的事業和家庭。
選自《早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