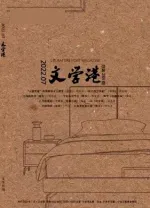凝望漸行漸遠的背影
趙柏田
南宋時,上林湖畔有個叫高翥的,是江湖詩派里“較有才情”的詩人(錢鐘書語),一生游蕩江湖,詩酒銷磨,臨老了,在湖邊搭了一間草屋,號“信天巢”,自稱,這個屋子雖然小僅容身,卻有數不清的書籍供他“障俗塵”。在方向明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西皮散板》中,時時出沒著這個南宋詩人的身影(在某行政中心的歷代名人浮雕里,此人又令人啼笑皆非地被誤作“高者羽”)。上林高翥,這個一千多年前詩情飛揚的名字,在方向明眼里就是一盞俗世生活上空的燈——生活必須被文學照亮。高翥的放棄與堅守,乃是他今世生活的一個樣板。當方向明在他的“半畝方塘”里讀詩文、讀帖、讀畫,營構著他的藝術人生,想必也有這種“不與世爭閑意氣,且隨時養老精神”的閑適自如吧。
愛書人方向明如是描繪他兼作書房的客廳:圖書二壁,中有半窗一幾;除此之外,床頭柜是書,食品柜是書,電視機兩旁是書,女兒的鋼琴也成了書架。每次出門,行囊中必塞滿書,各地大小書店,更是時常逛蕩,成了他的書庫兼閱覽室,某年在臺北街頭的誠品書店,竟逛至凌晨兩點,才拎著三袋書回到酒店。
他讀魯迅,讀沈從文,讀老舍,也讀王陽明的心學和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當代作家里似乎更喜歡以先鋒起家的莫言、蘇童等作家。這種閱讀方向延續著八十年代以來文學青年的那種趣味。然后,“很多的閱讀與少量的寫作”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嗜書若是,也正是為了印證知堂所說,“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長的精神上的快樂”。
這個書蟲的形象,僅是方向明諸般人生形態中的一個側面。我與向明兄相交垂十年,他是我學長,后來又成了同行。每次他來寧波,或者我去慈溪,說得最多的卻不是書事——或許在向明兄看來,訪書、求書,只是三二素心人可以相談的雅事——而是他興興頭頭地做著的那些事:以名畫家陳之佛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藝術館開館;輯錄出版七個近代鄉賢詩人的吟稿“溪上詩叢”。有時他還會以極大的褒賞的語氣,說起當地一個作者的長篇小說,一個來慈溪打工的外地青年詩人(這些詩人、作家后來都出了書獲了獎,向明兄不只為他們出書,自己還操刀寫評論)。有一次他突然欣喜地跟我說,發現了本地一位曾以養蜂為生的老詩人,1945年生人,二十多年里跟著他的蜜蜂們逐花而居,寫下了好幾本詩,“太陽在這里放牧,你聽,多好的詩啊!”后來我在向明兄的博客里讀到了他寫給這位老詩人的一封信,中有“您用了一生來吟唱”等句,信末自署:“您的小友:木耳”。
凡此種種,我看到的是向明兄與生俱來的熱誠和那種對文化的尊崇之心。從文之前,向明兄做過慈北名鎮鳴鶴鎮的鎮長,此鎮有白湖,清中葉就有士人結社于此,民國十九年,弘一法師在湖邊金仙寺駐錫,在此地收一俗家弟子胡宅梵,賜法名“勝月”,十余年間師弟鴻雁頻傳。對鄉賢的追慕竟使向明兄做出了一樁令我十分感佩的事,他點校出版了胡宅梵的詩集《勝月吟剩》。這幾年慈溪經濟名聲在外,北上廣名家大刊紛至沓來者,一如過江之鯽,舉凡把慈溪設作《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頒獎基地等等事件背后,都有著向明兄奔忙的身影。
話回到這本《西皮散板》上,作者自謂,西皮散板是一種無板無眼的唱腔,然在我看來,正由于這種發自天然的崇文之心,這本集子里的文字也都可親、可愛了起來。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都有著一個向心,說的都是人在文化空氣中浸潤的種種情致:
——比如他以西湖為情人,到了西湖必去看李叔同和蘇東坡。
——比如他去看福建土樓,看到的是從形態上固化了的以族權為核心的禮法制度。
——比如他到了白馬湖,看著那一泓秋水,就想到那個年代里的朱自清夏丏尊,直覺得湖邊的一棵樟樹,甚至樹上的一根枝椏,都可以安頓他的身與心,以致說出這般民國風的話來:“湖面上的風輕輕地拂過我的臉,我像一個孩子一樣睡去。我也要做夢,夢里也有風。我甚至愿意就這樣一直躺著,在白馬湖的一棵大樟樹上睡去。”
——再比如他在臺灣,看到保護完好的不僅僅是有形的器物,更多的是無形的東西,于是油然而生一種叫文化自覺的念頭:文化往往要遭逢某種生死存亡臨界點才會產生自覺。
而最令我動容的,則是他與弘一法師的一場對話。這場對話把向明兄身上的那種文藝范演繹到了極致。那是在廈門南普陀寺,一次關于生命與美的尋訪:
你先是以和煦的目光看著我們。你瘦了,身板倒很結實,走起路來僧衣飄動,生出風來。你肩上背著一把傘,老式的油紙雨傘,我知道那是你母親留給你的遺物。你沒有說話,好像又說了很多。你用目光與我交流。你的目光里,有沉靜,有憂傷,還有悲憫。(《我來看你了,弘一法師》)
亂云飛渡的年代里,牽念他目光的,還是白洋湖畔著長衫的那幾個背影和他們長短不一的吟哦。對陳之佛、邵洛羊這些慈溪籍藝術家以及童春、洪允祥、柴小梵等“溪上七子”的書寫,筆底更是常帶感情。這些漸行漸遠的背影和著那個年代,讓他出神地長久凝望。而《西皮散板》中的許多文字,未始不可作為這種凝望的姿態來解讀。在《以佛的修為做入世的事業》中,向明兄引用了陳之佛1946年在國立藝專校長任上一篇演講稿,其中數語也可讀作他對這個浮泛年代的批評:
“……如果都迷惑于物質的享受,迷惑于淺狹的功利主義,天天被困于名韁利鎖而不能自拔,美的情操駁雜,趣味卑劣,生活枯燥,心靈無所寄托,那我們雖稱為人,實在已失去了人性。”
人性之美正是這本散文集的又一引人入勝處。向明兄一向來是個把生活安排得很妥帖的人,這種細心周致正見于他寫老家屋后那條路,寫家人聚餐,寫父親、伯父們、母親、岳父、舅婆、妻子、女兒以及兒時的村里人的種種筆端,俗世里交集著的種種悲欣,也正在尋常的煙火里。一次由于母親的反對而夭折了的旅行,在一個成長中的少年心里激起的,是一次16公里的逃離。多年以后,昔日的少年已為人父,他終于醒悟到,每一個兒子都活在母親的愛中,他注定逃脫不了由這份愛衍生的幸福、安慰、疼痛、苦惱、叛逆和責任:
“有那么些年,我自以為沖出了16公里以外沖出了母親的包圍,其實我永遠走不出母親的目光。”
有此凝望,有此牽念,才是真人生。而得一真字,文字才有魂,散亦不散了。《西皮散板》,正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