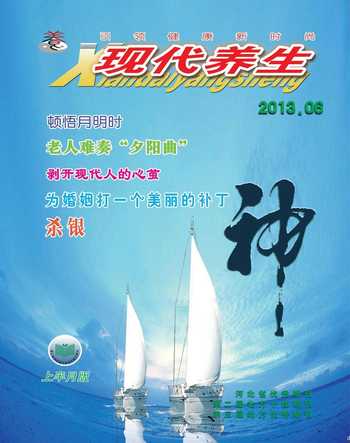頓悟月明時
楊劍平
在大陸最南端秀麗的邊陲重鎮——海安,有一座兩千余年茂林修竹、翠綠欲滴的石蓮寺,蘇東坡第三次被貶時曾在這里小住。其大雄寶殿門前有一幅楹聯:“佛本一乘,根源有別,故說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教育萬法、體性無殊,不可取法、舍法、非法、非非法”。當此聯映入我的眼簾,便不禁拍手叫絕。沒有想到如此偏遠地段竟會有如此高水平之人,雖然我不知此聯出于何人之手,但我敢斷定絕非等閑之輩。大幾學佛之人往往由于水平有限,很易落入法執的窠臼,而產生偏執與傲慢。門派之內的紛爭,門派之外的攻伐,甚囂塵上,令人厭惡不已。而此幅楹聯則是在告誡后世學者絕不可得佛法只言片語而妄自尊大,修佛學道且莫死讀書,讀死書,要探究領悟佛學中的實質精神,不要被“法”所困死。既要鉆進去,還要跳出來,才是真正的修道者。
其上聯是說佛法本無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不同等級的區別(乘著、車也,喻載運之工具,乃指方法),只是因人的智慧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故而佛為了普渡眾生的方便,所以才有了高低不同的多種教法。教內不要有大小乘之爭,頓漸之別,密顯之紛……教外各派之間不要瞧不起。佛、道、儒三大教派本是一家。一切圣人只是因無為法而有差別罷了。究其宗旨,說的都是一個內容,要洞見自己的真心本性。從自己所有不實,易失的感官追求中解脫出來,達到自己內心空靜的永恒幸福中去。不是嗎,人世間任何感的幸福感(眼、耳、鼻、舌、身)都是暫時的易失的,用佛語來說是虛幻的。并且任何人世間的“幸福”中都存在著對立面的隱患。老子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所謂“樂極生悲、物極必反”。所以人世間的所有幸福都是不圓滿的,是有缺憾的。而在空靜中悟到了自己的真正本性那種幸福感卻是空前絕后的,是人間凡人所永遠也體會不到的,用句俗語來講則是每個細胞中都充滿著快樂,而且又無對立面之隱伏。
其二,世人皆處于無明之中,即使科學再發達,對己、對宇宙也都是處在朦朧之中。今天我們人類連一個小世界的太陽系都未能沖破,并對地震、海嘯、星球相撞等都是無能為力。所以人類駕馭客觀規律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想主宰宇宙則必須徹見心性,人類才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否則永遠是大自然的奴隸。
什么叫解脫?即從欲界、從身體感官有限的虛幻的欲望中解脫出來,從蒙昧無明的妄心中解脫出來,也就是忘身忘心,讓自己的本心從五蘊中解放出來。先自救,然后再去解救眾生。
其下聯是說,盡管因人施教,方法多種多樣,但在根本理論上是一致的,無差別的。所以學者不要偏執地有所取舍,任何理論方法都是正確的,但也,都是相對的、有限的,不究竟的,所以才“非法非非法”。“非法非非法”這是哲學中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佛經中的應用。更具體一點則應是“是法、非法、非非法”。“是法”是肯定佛所說的每一個理論、每一個方法都是正確的。“非法”則對“是法”的否定,即每一個理論、每一個方法又都是相對的,每一種理論方法都是佛有針對性講的。在此階段適用,在下階段未必能適用,不能死搬硬套教條地到處亂用。“非非法”又是對“非法”的否定,就是說佛法并不是沒有一定的方法,而是這種方法理論是無法言說的。所以單純的肯定,單純的否定都是不正確的。實際上是讓我們辯證地去看待任何方法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正是脫胎于此。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恩格斯寫道:“辯證的思維只有對于人才有可能,并且只對于高級發展階段的人(佛教徒)。”馬克思在1861年給恩格斯的信中也談到“對我來說真是一件大樂事,他贈送我二卷他所著的《佛陀的宗教》,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修道伊始必須得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必須得從有為入手,這是入門打基礎。這也便是“是法”。當氣機暢通,精氣飽滿了則又必須從有為中解脫出來,用無為法去修心入空,這便是“非法”。但這個無為法仍是一個法,只不過與有為法一個是“實”,一個是“虛”而已,所以都不是道,都不符合“中道”。要連這一無為法也要去掉方才能進入真正的涅槃正智,即:“非非法”。釋迦牟尼在臨終時說:“我說法四十九年,其實我啥也,沒說過,如果有人說我說過什么法那是在誹謗我。”為什么他否定了自己的一切教育行動呢?不是他真正沒有說過什么法,而是這“非非法實在難用語言來表達,用相對的語言是難以表達絕對的道。徹底的明心見性是在“滅受想盡定”中完成的,那是無意識態中的事,這相對的語言概念又怎么能準確表述呢?無奈釋迦牟尼最后只得發出“不可說、不可說”的感嘆。對絕對真理只能體證,無法言說,故佛學中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來形容。因此,我們要突破具體的“法”的繭殼,去追求佛學的精神實質。禪宗傅大士悟得徹底日:“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這是對“非非法”的最好解讀。只要你的心真能空靜下來,還需要什么“有為”、“無為”法嗎?當下即是。
在四禪八定中最后一定乃是“非想非非想定”,這是“想之極致”想蘊幾乎已盡,但仍然還有意識存在。這與“非法非非法”是一個原理,都是否定之否定。所以在心的修為中,也逃不脫否定之否定的約束。“想”是我們的思想意識,也乃妄念,這是我們在修道初期所必須具備的,否則我們如何才能學習領悟佛學的實質和修為的方法呢?修佛的前行有為法必須通過妄念才能實現,所以不要一提妄念就緊張害怕,妄念也有其有益的一面。“非想”是當我們有了基礎便要讓心靜定下來,進入空境。但要知道進入空境后,這一空念也是妄念,所以還要除掉,進入到“非非想”!在佛學中“想”屬于第六識;“非想”屬于第七識;“非非想”屬于第八識。要轉識成智必須通過“想——非想——非非想”的道路前進。“非非想”有二層意思,第一是連“非想”的念頭也不能有。第二層意思是此定并非是一點意識沒有,還是有意識的痕跡,只是意識幾乎處于停止罷了。即使到了第九識禪定“受想滅盡定”也仍存在有微“我”之念。
佛道的否定之否定修持道路,青原惟信禪師給予了形象的表述:“老僧30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人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然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這是對事物的肯定,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分別得清清楚楚,這完全是第六意識中的事。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是對上述肯定的否定。此際已進入空境,分別心已無,萬事萬物本是一源,不分彼此,這是第七識已泯滅轉化的結果。
“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這是否定之否定,當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后,萬事萬物歷歷映照于心,事來則有,事去則無,但絕不會起心動念了,這與第一階段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是有著本質的不同,看似回歸,實則提升進步了!已是兩個層次中的事了。佛道“否定之否定”的修證道路,在此處是昭然若揭,最明顯不過了。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也談到三個修證程序:第一,“有覺有觀”,身有所受,心有所知。第二,“無覺有觀”身體感受不存在,忘我了。但心理意識還有。第三,“無覺無觀”,身心受想都不存在了,無我真空了。在觀世音法門中也,是如此:首先是集萬念于一念,聽著海濤聲而入座。漸漸海濤聲聽不見了進入空靜之中。實際上,這無聲和有聲都是有相。最終連能聽的自性也不存在了,這才是進入了真空境界。故觀音菩薩說:“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所雙亡,當體自空。”清朝雍正皇帝說:“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真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于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相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有三關之說“初關——重關——牢關”。初關:初見本心,暫見性空,好像在室內從窗孔中望見的天空,相當于初禪。重關:忘我空性已進入恒定,宛如站在院中仰視著天空。相當于四禪。牢關:徹底明心見性,進入了真空境界,猶如站在山巔上遠眺浩瀚之宇宙長空。相當于第九次禪定——受想滅盡定。
佛學、道學是人體科學的頂峰,絕非封建迷信,只是目前科學水平有限,人們還未能正確解釋罷了。
繼續在石蓮寺中徘徊,倘佯,在一塊巨石上發現了蘇軾的一首詩:“水曲山能住,泉清石更奇。眼光波鏡洗,心事佛燈知。花果杯中酒,園林畫里詩。高僧傳妙偈,頓悟月明時。”我不知道寺中高僧傳于他什么妙偈,但“頓悟月明時”卻正是開悟時的真實境界。什么是“非非法”,“非非想”的境界,頓悟中的空寂光明便是。什么叫開悟?覺悟了自己的本心,體證到了大道便是開悟。這是學佛求道的人們所追求的,開悟了就是人與宇宙真正合一了,“吾既是宇宙,宇宙既是我”,人天統混于一派無限光明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時空界線已打破,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這便是真正的般若正智,也便是佛的境界,仙的境界。
佛法的修持向來有頓漸之分別與爭論。有人說上根之人無需漸修,聞一句佛號,看一本經書,便能立地成佛。但我認為沒有漸修之量變過程,又何談頓悟?至于說到上根之人也正如南懷瑾所言“我始終未見過”。我想上根之人也許有之,但實屬罕見,當屬個案。故釋迦牟尼在楞嚴經中說:“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對理論問題是可立即頓悟,但要想真正在修證上開悟那必須得一步步地,踏踏實實練功,有了量的積累當質變時才會以頓悟的方式出現,所以要想當下即是、立地成佛,那是美好的理想。否則,釋迦牟尼就不會耗費19年的苦修才得其大道。人心是自足一切的,但要把五蘊一層層剝去,必需以時日,特別是命功的修為更是一步也馬虎不得,色身不能解脫絕對不可能達到無我,心物一元這是真理。所以,在修證佛法的道路上也是必須遵守哲學中質量互變規律的發展形式。萬事萬物沒有漸變,絕對不可能有突變,這是真理。踏踏實實練功,一步一個腳印方是正途。即使是六祖慧能悟后也是需要再去用十幾年時間進行修證。
真正頓悟在命功上是必須要做到“脈解心開”,即“心輪”一定要打開。這也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法本體的所在之地。在道家則居于中丹田,乃表養圣胎之所。“心輪”打開,其八脈便猶如八瓣蓮花一般。故佛教把蓮花作為一個吉祥的標志,在每尊佛像下以蓮花作為底座。而“心輪”的打開又必須以打通中脈為基礎。中脈按印度瑜伽和密宗的說法是猶如麥稈粗細,而在其間仍有一脈名為心識脈,放佛一根五色的細絲線,此乃生命之靈根。打通中脈就極不容易,而打開“心輪”則更為困難,所以談到頓悟那將是絕非易事,必須要有堅定的命功為前提,方能一窺究竟。
在道家來說,中脈即沖脈,打通中脈稱之為“中黃直透”。有個別的所謂密宗權威,大罵道家沒有中脈,這實居于狹隘的宗派之見,非真正修道者的品質所為。
根據我的實踐體會,要想打通中脈,則必須先打通脊柱中的督脈,然后才能打通脊前身體正中的中脈。從坐姿的感受則是從會陰至百會一氣貫通,而從站姿的體會則是從涌泉至會陰,再至百會一線貫穿。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中脈,從足至頭居身體之正中主宰一身的陰陽脈,控制著整個生命。我認為不論叫什么名稱,這一切都不重要,關鍵是它的功效。通中脈,通來通去無外是為了進入禪定,在空靜中接受宇宙的先天一炁,而絕不是江湖上的那一套爭高競低,如果真是這樣,我真不知某些人學佛學學了一輩子,他們的長進究竟在哪里。
也有的人將頓悟理解為某個練功階段的進展,即“大悟十幾次,小悟千百回”,也有的人將頓悟理解為偶見心性……這類所謂的頓悟實際上是概念的混淆,絕非大道上的頓悟。正如大慧禪師所云:“廓徹大悟,胸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憨山禪師也談到頓悟是“打破八識巢臼,頓翻無明窟穴”,這才是真心的頓悟。
蘇東坡的頓悟,也是建立在他長期修佛學道練功的基礎上的。無論對動功還是靜功,他都有過認真研究與苦練,他說道自己是每夜三更至五更便披衣起而練,“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內觀五臟……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有了長期漸修苦練的基礎,所以,再經高僧指點,他突然便頓悟了,于是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
其詩中“水曲山能住”即是寫實景,也,是寫情:我蘇軾雖遭貶謫到此蠻夷地段,遠離了繁華京城,但我心平如鏡,在這石蓮山我也能怡然于心,能安心下住,“泉清石更奇”這里的泉水清澈,山石如花,比起京都更是別有一番天地。“眼光波鏡洗,心事佛燈知”。我的委屈眼前的海灣水能照知,我的志向佛燈也完全能理解。“花果杯中酒,園林畫里詩”一酒解千愁,過去的一切,都讓它過去吧,即使在這僻壤里我也很瀟灑快樂,“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人生只不過一場游戲而已,功名富貴也不過是一場云煙罷了。“高僧傳妙偈,頓悟月明時”。這是整個詩的詩魂,我們知道中國的古代傳統文化都是文、史、哲、道不分家的。往往是詩中有道,道中有詩,詩道并茂。蘇東坡亦不例外。所以在這里他遇到了知己高僧點撥,明白了佛道的真諦,他追尋多少年的真理此刻“頓悟了”,當然,同時也是暗指人生中的頓悟。佛理上的頓悟指的是能見到自性光明時,便是“明心見性”。而人生上把萬緣放下當即也是光明一片。萬法唯心,一切都在于自己如何認為。蘇軾之所以一生三次被貶,可他仍很堅強樂觀,毫無頹廢消極,可以說這和他修佛學道是分不開的,在佛法中他曉得了人生的真諦。于是他親手在寺內栽下了兩棵鐵樹以紀念這頓悟的珍貴時刻。歷史上很多人感嘆人生的無常,常常是如唐朝詩人姚合的詩句一樣:“白日西邊沒,滄波東去流。名雖千古在,身已一生休。”望著夕陽落日,洪波東逝徒發“人生苦短”之悲傷幽情。但蘇東坡不一樣,人生他頓悟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他即不墮入李白的“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的頹廢心態。也不落進辛棄疾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功利窠臼,他是在追求“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灑脫的宇宙意識。他立志要做到“海到盡頭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而這一理想他明白則必須在真心自性的頓悟得道中才能實現。對此,滾滾濁世的俗人們是永遠無法能領悟到的,這也便是蘇東坡比其他文人高明的所在。
轉到在釋迦牟尼大殿前又見到這樣的楹聯:“殿前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云封”。這實在是高妙至極,這既是寫景,又是寫情,極寓禪意。這告訴修道者,人與天原本是無路可通的,但只要見到自性的空靈、光明,便可一觸而就,便有了登天之梯了。“月”者自性光明也。“山門不鎖待云封”,山門也寓指是人的“天門”,道家有諺:“天門常開,地戶永閉。”意思是說要把天門百會常開啟,不要關閉。“待云封”即指的是要讓天上宇宙中的能量,道的浩然之炁由天門人體,從而提高自己的生命能力。“云封”道炁之入也,這也便是得道和長生的真諦!同時也是說明佛道之門永遠是向世人敞開的,無奈俗人不求真理,卻造成了“終年無客門常開”的空曠冷寂,這豈不悲乎?也可能是世人也與李白一樣都有著“煙濤微茫信難求”的畏難情緒吧,所以才不入佛門寺廟……如此簡陋的石蓮寺中的楹聯把佛法中的要點一一都點撥了出來,它猶如一盞耀眼的明燈在啟迪接引著后世的修道者,這真是千古幸事!據寺中主持說此寺彌勒菩薩曾經顯圣過,并有巨碑石刻為證。我們姑且不論此傳說的真偽,但本寺的文化價值卻是無與倫比,故此寺絕非佛教界中的普通一寺。我久久佇立凝思遐想,仿佛也融入了這蓮花般的山石中……此際,好像空中隱隱約約飄來了一句“是寺、非寺、非非寺”的聲音……
【編輯:遲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