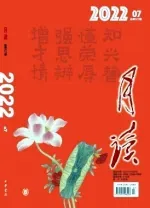如何走出腐敗高發(fā)期
王翠娟
記者:請談一談您正在讀的一本書,選擇這樣一本書是否有特殊原因?
房寧:在時下關(guān)于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諸多論爭中,如何認識和有效應對腐敗問題無疑是一大熱門話題。值得反思的是,一些人在認識外部世界時經(jīng)常出現(xiàn)“對象化”傾向,即把自身需要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轉(zhuǎn)向西方,認為效仿西方體制是解決問題的終極答案。在這些事關(guān)大局和方向的重大問題上,新華出版社出版的《走出腐敗高發(fā)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一書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見解和啟示。
從世界范圍看,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既是物質(zhì)生產(chǎn)過程,也必然伴隨著政治發(fā)展和社會轉(zhuǎn)型,而且往往會伴生著腐敗易發(fā)高發(fā)現(xiàn)象。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將所有社會成員卷入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之中,人們渴望實現(xiàn)流動、改變身份、擁有財富,其途徑大致有兩條:一條是經(jīng)濟途徑或者說生產(chǎn)性激勵渠道,即通過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實現(xiàn)其價值追求;另一條是政治途徑或者說分配性激勵渠道,即通過政治活動、集體行動來爭取政治權(quán)力,對社會價值進行“權(quán)威性分配”以便獲取利益。在這一社會急劇變動的時代,開放政治權(quán)力,無疑就是開放社會流動的政治途徑,必然引起各個社會群體和集團的政治斗爭和權(quán)力爭奪,社會進程主題轉(zhuǎn)向政治斗爭,結(jié)果往往是社會動蕩,甚至引發(fā)社會集團競相通過政治參與牟利尋租。走出腐敗高發(fā)期,最根本、最現(xiàn)實也最有效的兩條路徑是:讓公共權(quán)力與政治責任掛鉤,讓政治權(quán)力與私人利益脫鉤。
在一項為期三年的“東亞政治發(fā)展研究”項目中,我們通過對日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起點和發(fā)展環(huán)境相近的亞洲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實證研究亦發(fā)現(xiàn):工業(yè)化進程中注重分配性激勵,“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雙重開放”模式所引起的政治爭奪效應,是造成社會轉(zhuǎn)型期腐敗高發(fā)的重要誘因。如相互競爭的政黨經(jīng)常以反腐敗為政治斗爭武器相互攻擊,同時又以政治迫害為由,將腐敗問題政治化以躲避攻擊。最終,以反腐敗為政治斗爭工具的各方又會以政治妥協(xié)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結(jié)束利用反腐敗名義進行的相互傷害。反之,在工業(yè)化進程中開放權(quán)利通道,而關(guān)閉權(quán)力通道,則有利于把社會參與的潮流導向生產(chǎn)活動和經(jīng)濟領(lǐng)域,引領(lǐng)社會群體與集團通過經(jīng)濟行為、經(jīng)營活動爭取社會流動、身份改變和占有財富的機會,而不是通過政治性活動結(jié)黨營私、相互傾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以生產(chǎn)性激勵模式為主的道路更有利于后發(fā)國家的經(jīng)濟繁榮、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這也與《走出腐敗高發(fā)期》一書作者的研究成果殊途同歸。
記者:“絕對的權(quán)力產(chǎn)生絕對的腐敗”不失為探尋腐敗根源問題的一種解釋,那么相應的,解決腐敗問題的一條途徑是加快完善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shè),您對此怎么看?
房寧:從抽象意義上說,古今中外的腐敗形態(tài)各異,但有三要素大體不變:動力、機會和成本。全球化以來的世界歷史表明,腐敗的動力源于工業(yè)化階段迅速增加的財富以及財富分配差距在國家公職人員心理上形成的落差,這種心理落差總會突破一些人的心理防線和道德底線,并造成潛在的利益沖突和腐敗誘因;腐敗的機會則源于頻繁發(fā)生的經(jīng)濟活動,特別是在“建設(shè)財政”條件下,現(xiàn)金流、物資流巨大而且頻繁,交易機會眾多,客觀上為腐敗行為提供了機會;腐敗的成本實際上就是反腐敗的力度,反腐敗的力度越大,腐敗分子的風險就越大,一旦暴露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這就是腐敗行為的成本。在我國現(xiàn)階段,腐敗問題很大程度上面臨高動力、多機會和嚴處罰的形勢。腐敗作為“社會之癌”不是由一個原因所造成的,治理腐敗同樣不可能“一方治百病”。
從某種程度上說,反腐敗工作是觀察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一個絕佳“視窗”。中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核心是“三統(tǒng)一”的民主模式:堅持黨的領(lǐng)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要給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權(quán)利,這當然要通過法治手段來實現(xiàn)。黨的領(lǐng)導要維持動態(tài)平衡,讓社會通過一個核心來運轉(zhuǎn),而不是片面地通過各個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的博弈來實現(xiàn)。與之相適應的是,中國業(yè)已形成“黨委統(tǒng)一領(lǐng)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xié)調(diào)、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支持參與”的反腐工作格局,其實質(zhì)是由政治核心驅(qū)動的頂層治理模式。由此,在廉政建設(shè)中推動政治發(fā)展,在政治發(fā)展中促進廉政建設(shè),在有序政治參與中統(tǒng)籌兼顧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和民主的關(guān)系,不斷凈化政治生態(tài)。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特點是以問題推動制度建設(shè)。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制度的變遷往往和重大歷史事件有關(guān),政治制度就是在解決重大社會經(jīng)濟問題、政治問題的實踐中逐漸地規(guī)范化,成為一種制度或者法律。針對問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來講更穩(wěn)妥。一種矛盾、一個事件、一個問題的解決,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慣例,第三次是制度——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中國的明朝在腐敗高發(fā)期中被關(guān)外鐵騎改朝換代、“破產(chǎn)關(guān)門”,英國和美國卻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國崛起的特殊“接力”。面對腐敗高發(fā)和社會動蕩的問題疊加,之所以有的國家政權(quán)能成功重組,有的卻慘然倒閉,關(guān)鍵在于能否針對“問題域”進行有效管用的頂層設(shè)計與創(chuàng)新。
記者:您認為反腐敗工作應做好怎樣的頂層設(shè)計?
房寧:我們必須在黨內(nèi)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之間找到最佳結(jié)合點,實現(xiàn)經(jīng)濟基礎(chǔ)變革與上層建筑改革的良性互動,以應對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復雜化的挑戰(zhàn),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預防和化解利益相關(guān)性和非利益相關(guān)性沖突,防止利益沖突背后的腐敗現(xiàn)象和不正之風滋生蔓延,使得經(jīng)濟社會在發(fā)展轉(zhuǎn)型中實現(xiàn)軟著陸。
(選自《學習時報》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