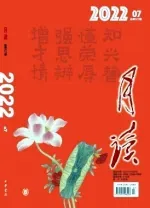私恩與公法
鄧忠強
唐貞觀三年(629),濮州刺史龐相壽犯了貪賄罪,被朝廷“追還解任”,受到免職處分,并追還贓款。不料龐相壽毫無思過之心,為了保住烏紗帽,竟不知羞恥地向唐太宗上書,“自陳幕府之舊”,哀求太宗念在“故舊”的情分上予以寬恕。
原來,李世民當皇帝之前被封為秦王,龐相壽曾在秦王府做過事,是他過去的老部下。照一般世俗眼光看,老部下犯了事,請求老領導老首長照顧一下,開開綠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唐太宗雖然貴為皇帝,卻始終未忘故舊之情,看了龐相壽的上書后,禁不住“深矜之”,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馬上派人撫慰他說:“你過去是我的屬下,現在拿了人家的財物,只是為了滿足貪求的欲望。我現在賜給你一百匹絹,恢復你的官職,還是去原地上任吧,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貪贓枉法的事。”
見皇上如此寬容龐相壽,宰相魏徵直言相諫說:“龐相壽為人‘猥濫,貪婪卑鄙,遠近聞名,可說是罪不可恕。現在陛下因為顧念‘故舊私情,不僅赦免了他的‘貪濁之罪,又加以重賞,還讓他官復原職,這樣做無助于他棄惡從善,重新做人。況且,過去秦王府故舊熟人很多,如果這些人犯了法,都依仗與陛下有私情而受到庇護,那么只會使貪鄙者得意,為善者害怕,社會怎得太平安寧?”魏徵嫉惡如仇,態度鮮明,他指出對貪官寬大為懷,溫情優待,只能是姑息養奸,貽害無窮,后果不堪設想。
這一番曉以利害的勸誡,唐太宗聽得是聲聲入耳,句句上心,不禁翻然悔悟,決定收回成命。他召見龐相壽說:“我昔日為秦王,自然要為王府作主;現在我是皇帝,已是天下之主,既為天下之主,就不能‘偏與一府恩澤,專憑私情來照顧你這個王府老部下了。”可以想見,唐太宗的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居高臨下、身不由己之感,但在國法面前,他最終還是舍私情而奉公法,表現出公正廉明之態。于是,太宗“賜物而遣之”,送給龐相壽一些東西,將他遣送出京。龐相壽原以為可以僥幸保官,哪知“復職”美夢終成泡影,他默然無語,只好帶著無限的傷感流涕而去。
看來,在龐相壽事件中,即使像唐太宗這樣的一代明君,有時也可能為私情所惑而壞公法。如果沒有魏徵的及時諫阻和監督,或者唐太宗不愿納諫,仍然一意孤行,濫用權力,對龐相壽給予特權庇護,那么,龐相壽這個腐敗分子,豈不是會更加有恃無恐,照貪不誤,奢靡享樂不止?因此,作為領導者,面對私情與公法的選擇,不可不慎。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位古人的執法佳話。東漢順帝時,蘇章升任冀州刺史,他的一個老朋友在他屬下任清河太守。有一年八月,他按例巡視部屬,發現那位故人有“奸藏(贓)”行為,決意將其繩之以法。為此,他來到清河,特地備下酒肴,請這位故交喝酒。席間兩人暢敘平生友情,相談甚歡。太守高興地說:“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外之意是,他除了老天爺保佑,還有蘇章這個上級幫助他掩飾罪過,渡過難關。但他萬萬沒想到蘇章會說:“今夕蘇孺文(蘇章字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這事的結果是,蘇章“舉正其罪”,列舉太守的罪行并加以懲治。消息傳開,冀州境內知道蘇章大公無私,都望風敬畏。
這個蘇章反貪的故事令人深思。清河太守犯了事,要不要查處,這完全在蘇章這個頂頭上司的掌控之中,他如果不辦,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事就可平安過去;如果依法辦事,這位故人就要被懲處,他們多年的交情也將從此終結。蘇章的處置辦法很有人情味,又富有戲劇性。他先以私人名義請老友赴宴,顯示了濃濃的私情友情;然后以刺史名義懲治貪官,秉公執法,顯示了清正嚴肅而又有情有義的高風亮節。與唐太宗相比,同樣是面對貪官故舊,蘇章在執法上則更顯自覺、嚴正和堅定。他把公與私、情與法,處理得一一得體,既有對朋友的私恩柔情,又有違法必究的鐵面無私,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令人嘆服。
人在社會中生活,不可能沒有親朋故舊。親朋故舊違規犯法,應該如何對待?君不見,當今有的人利用職權,包庇袒護;有的人托人求情,為其開脫;有的人一團和氣,大事化小;有的人則公正嚴明,甚至大義滅親……形形色色,態度不一。在私恩與公法的問題上,看看唐太宗和蘇章是怎樣應對,就不難做出正確的選擇。
(選自《學習時報》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