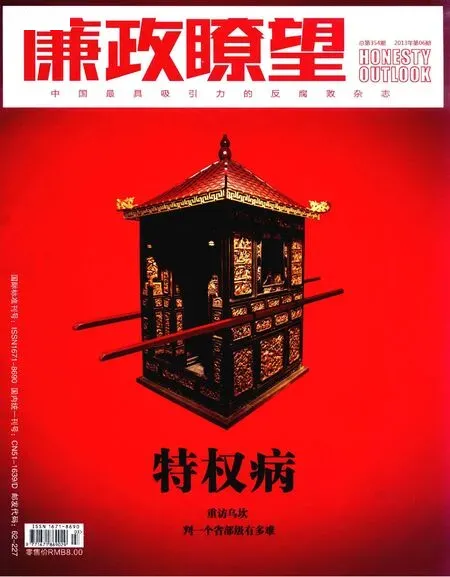鰣魚味道
劉俏到
春夏之交正是昔日鰣魚入饌時。世間鰣魚有三種,即長江鰣、印度鰣、美洲鰣,其中以長江鰣為“三鰣之冠”,長江鰣又以鎮江鰣魚為上品。鰣魚肉細味鮮,古已知名,比如《紅樓夢》庚辰本雙行夾批里,就曾形容某段描述細膩之極,有似“三月于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鰣矣”。難怪明代洪武元年定有“薦新”之禮,即每月初一向太廟進獻時鮮食物,其中四月初一進獻的五種美食當中,就有鰣魚。到了清代康熙,還曾下旨“飛遞鰣鮮,以供上御”。
鰣魚怎么吃?元人《日用本草》說得清楚:“凡食鰣魚,不可煎熬,宜以五味同竹筍、荻芽帶鱗蒸食為佳。”可為佐證的,是宋代賀鑄的詞句“苦筍鰣魚鄉味美,夢江南。”其實宋詞中的鰣魚似乎都與苦筍并列,看來二者真是食界絕配。至于烹調之法,蘇東坡最是熟悉:“芽姜紫醋炙鰣魚,雪碗擎來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氣在,此中風味勝莼鱸。”
話說明代把鰣魚列入太廟“薦新”的食單之后,就好象打上了“宮廷特供”的字樣,令食者亦得意洋洋。萬歷年間的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就曾驕傲地告訴我們,“六月鰣魚帶雪寒,三千江路到長安”;“賜比群卿恩已重,頒隨元老遇猶難”。那叫一個皇恩浩蕩哪。于慎行的詩名叫做《賜鮮鰣魚》,我們下意識里也應當認為那是很鮮的魚,那畢竟是御賜的宮廷特供呵。
但理想總是豐滿的,現實總是骨感的。三十年后的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談到了御賜鮮魚的殘酷真相。原來,鮮鰣最初在南京孝陵供奉,之后船運到京,供太廟“薦新”。雖然船工日夜兼程,且有冰塊保鮮,但畢竟為時長達一個半月,結果鮮鰣都“臭穢不可響邇”。沈老師曾經跟船一次,“幾欲嘔死”。到了京城,臭魚當然不能進太廟,于是“洗刷進充玉食”,以腐充鮮而已,換作現在肯定是要被工商查沒的。但太廟“薦新”之后還要作為御膳原料,或賜給于老師一類的高層領導享用,“侈為珍味,然實不堪下箸”。
最搞笑的是有名京官到南方做官,夏天里忽然責怪廚師,說為什么燒菜不用鮮鰣魚。廚師聽得糊涂,說“最近每天都有做啊”。京官不信,叫拿來看看。一看之下,驚訝不已,說:這形狀倒是很象,“但何以不臭腐耶?”一時傳為笑談,卻不知于大學士心目中的鮮鰣有無臭味?當然,這也不能笑話人家,畢竟彼時船慢,非人力可為。其實當年那些運魚的冰船沿途騷擾民眾日久,上下皆知,弘治皇帝曾想廢除鮮品進貢,但想到是祖宗定下的舊規矩,實在不敢動。
事實上,正宗鮮鰣極為難得。因為鰣魚十分愛惜自身鱗片,一觸魚網便不再動彈,故又稱“惜鱗魚”。加上鰣魚性情暴躁,離水即死,所以市場上幾乎看不到活鰣。何況如今長江鮮鰣近于枯竭,人工飼養的美國鰣魚亦達數百元一斤。即使最近公務消費大幅壓縮,但想必降價仍難。回想明代王叔承的《游金焦兩山記》里,“斤可十八錢”而已,按照現時米價兩元每斤計,查諸史載當時米價,可折算那鮮鰣僅僅五元每斤——果然是滄海桑田啊,不過想跨越時空去嘗鮮者,務請牢記鰣魚多骨,不可貪了便宜卡了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