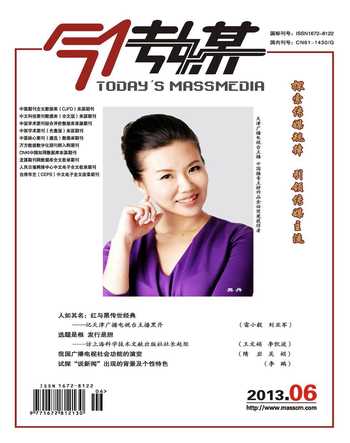從《論語》看孔子的傳播思想
毛仁興
摘 要:縱觀中國古代傳播史,早在先秦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諸子就實踐了豐富的傳播活動,積累了多樣的傳播方式。他們積極游說諸侯,為人際傳播;辦學授徒,為教育傳播;著書立說,為大眾傳播。多樣的傳播活動不僅為中華文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對傳播的方式、傳播的功能形成了獨到的見解,如教化傳播與穩定政權的關系、傳播技巧、傳播的雙面效應等等。綜而觀之,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子的傳播思想,不僅富有創造性,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從《論語》當中,選取涉及傳播的、有代表性的《論語》原文進行分析,探尋孔子的傳播思想。
關鍵詞:傳播思想;孔子;《論語》
中圖分類號:B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6-0142-02
《論語》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思想。歷史學家柳詒徵曾表示:“自孔子以前的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1]”肯定了孔子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表明了孔子是中華文化傳播的先驅,并強調了其在中華文化傳播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
《論語》為儒家代表典籍,研究孔子的傳播思想,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論語》,能夠發現《論語》中的內容涉及富含傳播的諸多內容,如傳播原則、傳播與人際關系、傳播與政治、傳播與倫理、傳播的內容與形式、傳者的修養、傳播與反饋等等,蘊含了孔子豐富的傳播思想。
一、傳播原則
傳播,即“信息的交流和分享” [2]。而傳播當中的人際傳播是最普遍的傳播現象,隨著人類群居的出現就出現了人際傳播,所以群體的出現就存在著人際傳播。孔子對人際傳播的理解,是建立在孔子“仁”的哲學思想基礎上的,強調人倫,強調規范行為,如“仁”、“義”、“禮”、“信”等。在這其中,“禮”又是核心,同時也是傳播的基本原則。
在《論語》中,關于“禮”的語錄非常多,《顏淵》中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段關于“禮”的要求就體現了傳播的原則:凡是不符合“禮”的內涵的,既不能主動傳播(非禮勿言),也不能接受傳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可見,“禮”的要求在孔子的傳播思想中就是傳播行為的道德規范,必須遵循。在《陽貨篇》“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中,孔子指出了人際傳播中的規范:不要總是傳播別人的壞處,下位者不要無故毀謗上級。此原則不僅是“禮”的要求,也是傳者的修養和社會傳播的規范。
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是基本的傳播原則,而越禮的傳播行為則是孔子憎惡的。《八佾》中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越禮在庭院中奏樂舞蹈,而這時天子使用的規格,孔子對此非常氣憤,認為這種行為傳播了季氏的政治野心,對社會穩定安寧是不利的。這種思想和孔子“仁”“禮”的倫理道德思想密不可分,傳播秩序同樣遵循禮儀的要求,以“禮”維護傳播秩序,維持社會穩定,這是傳播的基本原則。
二、傳者的修養
孔子強調倫理規范是傳播的基本原則,自然個人的道德修養也是傳者的基本要求,傳者的政治態度、品德、人格不僅決定傳播內容的選擇,也對傳播效果產生影響,傳者修養同樣是傳播活動的重要一環。
在《論語》中,諸多語錄都體現了對傳者修養的要求。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僅是統治者還是傳播者,只有個人修養達到水準,政令才能通達,傳播才能達到效果。《子路》中“茍能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在孔子看來,個人有正直的品格,才能在傳播過程中教育他人,傳播效果和傳者的修養密切相關,而孔子本人就是實踐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對個體提出了修養要求,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說,不要憑空猜測他人,不要思想絕對化,不要堅持己見,不要自以為是。孔子所側重的是人格修養,同樣也是傳播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
再如《子罕》中的“法言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在這里,孔子從傳播過程中受者的態度角度進行了思考,有道理的批評性話語,能夠不聽嗎?聽了之后改正才難能可貴;迎合自己意見的話,能不喜歡聽嗎?聽了之后能加以分析才難能可貴。
由此可見,孔子不僅對傳者的修養提出了要求,也對受者的修養進行了規范,而在以人際傳播為主要傳播手段的先秦時期,傳受雙方的修養對傳播效果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孔子對傳受雙方修養的思考,體現了孔子傳播思想的光芒。
三、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
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是傳播過程的重要因素,在孔子的傳播思想中,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的關系建構在他的哲學與倫理思想框架內。如“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傳播過程中,傳播內容要符合“仁”的要求,形式也要符合“禮”的要求。再如《陽貨篇》“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反對空有夸夸其談的花言巧語,強調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應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是做人的標準,也是傳播的要求。
四、傳播方式與方法
在《論語》中,關于傳播手段、方法的論述比較零散,但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傳播原則、傳播時機、傳播技巧、傳播方法、傳播效果、反饋等諸多方面,體現了孔子傳播思想的廣博。
《衛靈公篇》中“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因為一個人會說話就提拔他,也不要因為他不是好人就否定他說的話,涉及的是對傳播內容要進行判斷以及判斷的原則。
《衛靈公篇》中“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談的是把我傳播時機的問題,值得與人交談而不和他交談,就失掉了可靠之人;不值得與人交談的卻和他交談,就會失言。在此,孔子辯證的討論了智者如何把握既不失人,亦不失言的傳播時機問題。
《庸也篇》中的“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孔子指出,傳播對象因人而異,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傳播內容也有所不同,這是作為傳播者應該掌握的傳播技巧,也可以說是孔子的傳播受眾觀。
對于傳播技巧,孔子也有獨到的理解。《憲問篇》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這既是做人之道,也強調在不同的傳播環境下,應采取不同的態度:當政治清明的時候,言語正直,行為正直;當政治黑暗的時候,行為正直,言語謙順。
而孔子本人亦是傳播技巧的實踐者,《鄉黨》篇“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在不同的場合,孔子的表現也是不同的。傳播技巧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這些描述不僅體現了孔子為人處世的態度,也表明孔子已經意識到在不同場合采取不同傳播態度的必要性。
在傳播過程中,孔子很重視對傳播的反饋。他曾批評學生顏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說顏回對老師所說的話沒有不喜歡的,這不是對我有幫助的人。表明孔子非常重視教育傳播反饋意見的重視,他希望學生對自己的傳播行為提出反饋意見,并且是負面意見,而不是一味的贊同,因為這對于他調整自己的傳播行為無益。
最后,孔子對作為傳播活動接收器和反饋器的受者,也有自己的觀點。孔子認為不管是對學業的態度,還是傳播的結果,受者應采取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實事求是才是聰明的智慧。作為受者,也并不是被動接受傳播,也應發揮自己的主動性,正如《述而》中所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知之;知之次也”,多聽,多看,然后選擇好的加以接受并記在心里。對受者主動性的肯定,不僅探討了傳播效果的影響因素,還體現了整個傳播活動的動態性,這是難能可貴的。
通過上述梳理不難發現,在《論語》當中,孔子對傳播活動的諸多方面進行了論述,他的傳播思想觀點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這和他的傳播活動是密切聯系的。孔子通過“有教無類”的教育活動、整理典籍等活動,親身實踐著傳播活動,使他的思想體系得以傳播。儒家在先秦就已成為顯學,孔子的傳播活動與傳播效果毋庸置疑。
本文通過梳理孔子的傳播思想不難發現,孔子的傳播思想雖然只是零散的基本觀點,但涉及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孔子的傳播思想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有著重要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研究。
參考文獻:
[1] 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甘惜分主編.新聞學大辭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