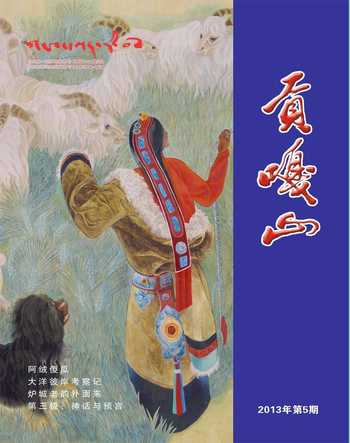爐城老韻撲面來
郭昌平
先棗是土生土長的康定人,我們是發小的朋友,他對康定的認識和理解在當今康定人中是少有的,他對康定的執著和深情也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加之他那散文般的敍事風格,康定的風情在他的筆下便栩栩如生,余味無窮。早在幾年前,當先棗剛寫完第一個中篇《雪嶺鎮》時,我就提前拜讀過,當時就被他的敍事風格以及他對老康定的把握所折服。后來聽說他又寫了“雪嶺鎮”的系列篇《黃金地》和《御林巷》,便一直渴望早日讀到,去年收到他以這三篇小說合成的小說集《雪嶺鎮》后,甚是高興,迫不及待的用了兩天時間把它讀了一遍。
三個中篇小說寫的都是發生在一個名叫“雪嶺鎮”地方的人和事,原本這是小說,人和事都是虛構的,本不該對號入座,可是我卻情不由已的認為這不是虛構,這就是先棗用文筆作畫筆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當年老康定的人文風情畫。讀后猶似喝了一杯陳年老酒,甚是過癮,老康定當年的山山水水,父老鄉親,街街巷巷,歷歷在目,呼之欲出。
兒時的康定城沒有現在的規模,方圓不過一個多平方公里,狹長的一溜溜沿折多河兩岸分布開來,東西也還是有幾條街巷,人不多,雖不至認識全城的人,但大家見多了,也都相互面熟,說起來也還是八九不離十的。有人就有故事,不大的康定城好象從來就是盛產故事的地方,只要到“貓胡子”茶館座上一時半會,爐城內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大凡小事就會知道很多,如果再有空到中橋一帶曬曬太陽,聽聽閑龍門陣,你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康定通。
康定寄居于大山之中,大山中的人,見識不多,心地卻是出奇的善良。康定也是一座突出的“慢城”。夾皮溝中,太陽出來得遲,落山得快,于是也就養成了一種不急不忙的性子,睡夠了,起床,打桶酥油茶,慢慢喝。夜晚吃了飯,閑來無事,到茶院聽藍文品老師講評書,日子過得不溫不火,就圖一個自在。街上相互見面都要打個招呼,甚或是站下來擺幾句,街那頭娃娃些就會扯開嗓子喊:“爸爸吃飯了!”,于是乎連忙招呼:“走,到家喝一口去。”下酒菜不多,頂天幾顆炒花生米,遇巧了,“打牙祭”還能怎上幾塊回鍋肉,算是有運氣。臨走還得一再給主人家說“道謝了!”。那時沒有高樓,卻有親情,大家相互關心,相互照應,一城人其樂融融,那溫馨味至今對于我來說都是銘心刻骨的。
帶著這樣的心境進入《雪嶺鎮》,一幅當年老康定的風情畫由先棗的雙手為我們徐徐展開。那些我們見過或是我們聽老輩人講過的康定“名人”開始逐一登臺,那些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遺聞趣事又紛紛從頭道來。“瘋子喇嘛”的瘋言瘋語;“花碎嘴”的茶館評書;“洋人公館”的電燈;翁仁和老先生的夫子氣;阿佳婆婆的奇遇;假洋漢兒桃花運;馬旅長的威風;海大爺的江湖;煙道上的風險;劉軍長公館的盜案;大炮山下的棒客······這些人和事連在一起,你想說它不是當年的那個康定都難。先棗將虛構的故事和真實的情節揉在一起,將歷史上有過的人物和編創的人物和在一處,將真有的地名和虛假的地名化為一堆,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于真中看假,于假中解真,一個當年的康定風情就這樣在一片云遮霧障之中推了出來,不能不說是他的高明之處。
《雪嶺鎮》沒有一個從頭貫穿到尾的故事,就好象先棗坐在中橋頭曬太陽,看到誰就講誰,不急不忙,娓娓道來,看似很散,過了一個人,這個人的故事也就告一段落,再來一個人于是又接著講,好象誰與誰都不搭界,但細細品味,就會發現這些故事都是雪嶺鎮的事,沒一個跑了出去,正是這些好象相互都不搭界的東西,共同組合成了一個有滋有味,有血有肉的《雪嶺鎮》。
如果說《雪嶺鎮》只是一幅散文般的水墨風情畫,那《黃金地》和《御林巷》則是康定兩幅寫實的人物工筆畫。他實實在在以康定為背景,為我們講述了兩個蕩氣回腸的故事。
《黃金地》主要寫一個名叫管青云的陜西人到雪嶺鎮當學徒受冤枉,憤而離開去挖金,還挖到了一砣狗頭金,于是圍繞這砣金子在管青云身上便產生了一段傳奇。這段故事由管青云為線,一頭連著雪嶺鎮,一頭連著挖金場,情節就在這條線上逐一鋪開,雪嶺鎮在經歷了前面幾場折子戲后,終于進入了一場大戲。
據說當年的“打箭爐”,就是一個遍地都是金子的地方。遠在陜西的人都知道它的大名,他們說到了打箭爐,穿起草鞋走一圈,到水里都可以沖出金來,到底是不是這么一回事,沒人去驗證,反正他們為了祖祖輩輩那從不曾停息盡早擺脫貧困的夢想,不辭千里,從遙遠的陜西來到這大山之中,來的人不曾離去,新的人又來了,打箭爐里的老陜越來越多,甚至建出了一條老陜街來。到打箭爐來的人多了,家鄉還為他們取了一個名,叫“爐客”,大約就是客居爐城之意吧。“爐客”在爐城,有人發了,也有人跌了,發了的人風風光光,買地建房,沒有發的人,八方奔波,有務農的,也有挖金的,還有混不下去的,咬咬牙,翻過折多山,繼續西進,去尋找新的財源。從此甘孜大地上到處都留有他們的腳跡。他們不僅帶來了老陜不折不繞的頑強精神,也帶來了他們家鄉的文化,如今巴塘的面食,康定的“鬧山鼓”無不留有他們的痕跡。
管青云當是他們這一代人的代表,在這遠離家鄉的大山之中,磨爬滾打,與當地的老百姓生死相依,為這方土地作出了他們應有的貢獻。
先棗的這篇小說,與其說是虛構,到不如說是記實,因為從管青云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曾經認識的那些老陜,就在康定的老陜街上,在西康人民為抗戰集資捐獻飛機的活動中。
老陜街上的一幕剛剛告一段落,先棗又帶我們跨過上橋進入了康定的另一條巷子----御林巷。
這是一條康定實實在在有過的巷子,也是我兒時十分熟悉的巷子,就在原清真食堂邊上,巷子的一頭正對著康定上橋,進巷子不足一百米又分出一條巷子,在清真寺后面,圍著可以轉到馬市上,我們又稱此地為兩岔街。
先棗的《御林巷》是不是就寫的這條巷子,他一定會說不是,小說嘛,都是虛構的,人物是虛構的,環境也是虛構的。確實也是這樣,現實中,康定兩岔街是找不到“賓騸匠”和“雷樂之”這兩戶人家的,也沒有發生過他小說中寫到的故事。但是當我讀完《御林巷》,我總認為先棗這篇小說就是寫的這條巷子,就是寫的這條巷子里的人和事。小說對人物的描述,對故事的鋪陳,對環境的渲染與我頭腦中當年老康定的氛圍一模一樣,如果御林巷還在的話,我感覺我一定會在這條巷子中去找到賓騸匠和雷樂之兩家人住的地方,就是那條石板鋪就的小巷,就是那排木架撐起的小房,木板門開關的吱呀聲,聲聲在耳。甚至那天晚上鬧兵亂,我也仿佛覺得我就在現場,親眼看到賓騸匠撿到那五砣銀元寶。以及雷樂之兵亂之后到城外買碗豆回來在路上救下一個亂兵,那地點我也覺得十分熟悉,一草一木依稀可見。
先棗的這三篇小說我是一氣讀完的,當放下手中書本,我真有一點不能自拔的感覺,腦子完全沉浸在當年那個老康定的氛圍之中,書中的各色人等,不斷的在我的眼前晃動,真有其人的,又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不是真名的,我知道他一定寫的是誰,我會在自己記憶的大海中去努力搜尋這個人的一切信息,創作的人物,我會自動為他對號入座,從眾多康定人中去尋找他的原型。那些天我感覺我被先棗的《雪嶺鎮》“折磨”得有點“痛”,有點“苦”,思維老是不斷在老康定城和“雪嶺鎮”之間來回,在一種晃忽之中體驗著一種閱后的愉悅。這種體味在我閱讀有關康定的文學作品中是從未有過的。他筆下的人物并不高大,就是康定城中隨處可見之人,但這些人經他的手一寫,都有血有肉的站了起來,讓人可親可信,觸手可及,甚至我總認為這些就是我曾經的街坊和鄰居,是那樣的熟悉和親近。他所敘述的故事也并不驚天動地,就是街邊的閑龍門陣,然而經他一說,卻都活靈活現,有鹽有味,讓人欲罷不能。這大約就是文學的魅力之所在,先棗用文筆豐富了康定的生命,康定也因《雪嶺鎮》而多姿多彩。
最后,我到有一點純屬個人的想法,先棗這三個中篇寫的都是“雪嶺鎮”發生的故事,三者間看似沒有多大聯系,其實相互之間內在的韻味和敍事的風格都是一致的,如果將這三個中篇改寫成一個長篇,將這些故事合成一個大的故事,鋪陳開來,那這座“雪嶺鎮”一定會更加有味,更加過癮。哈哈,一點陋見,苛求先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