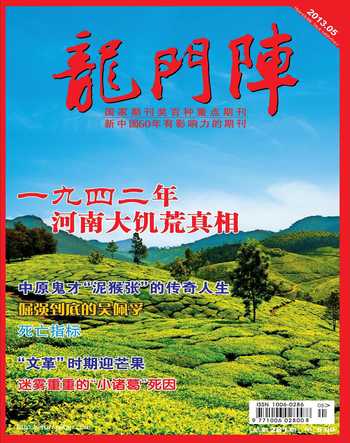絮語話粥
張桂英
作為“50后”,說實話,我對粥本來沒有多大興趣,只不過打小就頓頓喝它,更有甚者,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公社中學讀兩年制高中時,700多頓晚餐竟餐餐是“清一色”的玉米粥。當時正是“樣板戲”鋪天蓋地之時,《紅燈記》中那場“粥棚脫險”可謂深入人心,可我還是一提到“粥”就心里發怵。
不知從哪一天起,我竟想對“粥”一探究竟。這是因為我們把年逾八旬的母親接到威海小住,她對魚肉海鮮不屑一顧,只對粥情有獨鐘。曾與母親在北京、青島、哈爾濱等地的星級賓館吃自助餐時,母親也只鐘情于“小米粥”、“玉米粥”等粥類。自母親來到威海,我每餐都為她煮粥,孫女自3個月能食五谷雜糧之日起,便也“入鄉隨俗”跟著太奶食粥,現在已20個月,她對那些眼花繚亂的乳制品都“淺嘗輒止”,卻對粥每餐不厭。
古人將大米、小米、玉米等糧食煮成稠糊,既好吃又養人,于是起名為“粥”。史書《周書》中就有“黃帝始烹谷為粥”之說,可見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古人就開始吃粥了。“僧多粥少”,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俗語,可見“粥”是國人賴以維生的膳食。據推測,“粥”在古代應該是一種普通主食,要不曹雪芹生活困頓時,怎么就說過的是“舉家食粥酒常賒”樣的生活呢?
歷代文人大多喜愛粥。記得歷史上張文潛、蘇東坡、陸游、袁枚、鄭板橋、曹雪芹等人都稱贊過“粥”。北宋詩人張文潛在《粥記》中說:“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谷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宋代蘇東坡有書帖曰:“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覺,尤不可說。”南宋詩人陸游也偏愛食粥,他還是一位精通烹飪的專家,曾用山芋、蘿卜、芋艿、白菜等家常蔬菜煮出一種萬人仿效的甜粥,并在《食粥》一詩中吟道:“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或許正因這食粥養生之道,陸游活到了85歲高齡,是南宋詩壇鮮有的大壽星。清朝詩人袁枚在《隨園食單》中專門為“粥”擬定了“黏稠且滑而不膩”的標準:“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合,柔膩如一,而后謂之粥。”清人鄭板橋也曾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描述冬日里吃粥的生活情景:“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涂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林語堂讀了這段文字為之動容,他感慨萬千地說,這反映了中國人對待飲食的鄭重態度。電影藝人成龍在一次回憶從影經歷時,談到年少時母親為他熬的紅豆粥,心情久久難以平靜,許多觀眾也潸然淚下。確實,很多人都難以忘懷母親為兒女們做過的那碗“紅豆粥”,它香甜可口,溫馨暖人,融入了母親濃濃的愛意,淌進了兒女們的心里。
粥不僅能充饑、養生,還能治病,古人將粥的妙用發揮得淋漓盡致。2100多年前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有西漢名醫淳于意(世稱倉公)用“火齊粥”為齊王醫病的故事。東漢末年,醫圣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論述道:“桂枝湯,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多種佛教書籍也記載“粥”有“資色、增力、安樂、益壽、辭清、消宿食、防風、除饑、消渴”等益處。因此,“粥”經常被用作“食療方”,“藥粥”便由此而來。特別是大病初愈的人,應先用溫軟平和的食物來調理一段時間,這時,喝粥便成為首選;待氣脈和緩,再用肉食來補,猛藥來攻,方能痊愈。讀《紅樓夢》便可知年老力衰的“老祖宗”賈母、孱弱多病的少女林黛玉也經常食粥調養。只是在這鐘鳴鼎食的貴族之家,粥的主要成分已變成人參、燕窩等高檔之另類了。
其實,粥在中國飲食文化中還有特殊的內涵。“憐弱濟貧”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那些樂善好施者常以大鍋熬粥來幫助生活困頓的人,為粥食注入了“友善”的理念。古人施粥行善的暫且不說,就說近些年來的施粥之舉無不令人感動。2006年8月,在浙江溫州華蓋山腳下,幾位老人用自己的退休金及熱心人士的捐款辦了一個“紅日亭施粥攤”,他們數年如一日,每天給生活清苦的人施粥。老人們還在施粥亭里面添置了桌椅,供年老體弱的人坐著吃粥。2009年元旦,一位曾當選為重慶十大慈善人物的農民工準備了50公斤大米、15公斤蘿卜、10公斤豬肉和部分白菜,熬制了熱騰騰的“肉末粥”,施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為他們送去溫暖。2009年1月3日,農歷“臘八節”,北京廣化寺用桂圓、紅棗、大米、江米、核桃、豆子、白薯等20多種原料,熬了幾大鍋香噴噴的“臘八粥”,可供四五千人食用,從凌晨5時便開始向那些生活困頓、無家可歸的人施粥。這些慈善人士將愛心和責任感滲透在這一碗熱粥中,溫暖著無數人。
在不同的節令里食粥,“各得其所,各盡其妙”。寒冷的冬季,粥要比其他食物更滋養身心。粥的種類也異常豐富:黃澄澄的“小米粥”,紅稠稠的“瓔珞粥”,白融融的“糯米粥”,還有小豆粥、胡麻粥、酥粥、清粥、八寶粥等等。冬日的清晨,霜露遍地,霧靄騰騰。當寒風牽起了衣角,潔白的雪花飄過窗前時,坐下來喝一碗熱粥,心中的春風就會悄然而至。冬日的屋內不甚暖和,此時來一碗熱氣繚繞的粥,就禁不住捧起來,輕輕舀起半勺,緩緩吹著熱氣,送入口中,一股涓細的暖漿流進身體,頓時渾身都溫熱了許多;慢慢咀嚼米粒淡淡的甜,吞咽后,口中清清的谷香依舊讓人回味無窮;不知不覺已吃了半碗,不僅腸胃感到溫暖,整個人的身體也倍覺舒適、通暢。而在烈日炎炎的酷夏溽暑,一碗“綠豆粥”、“西瓜粥”,又讓人神清氣爽、心曠神怡。
從地域看“粥”,也饒有趣味。北方人做粥,多用五谷雜糧,盛粥的器皿也多是厚重結實的大“海碗”。一家人圍坐在熱乎乎的火炕上,大口大口地喝著熱氣騰騰的粥,最見北方的風土人情。而在南方,凡是能做菜的食物都可以用來煲粥。小火慢慢熬制,翻滾沸騰,香氣四溢。熬好后,用青花小瓷碗盛了,配以清淡的小菜,再一點點細啜下去,是一種婉約到極致的南國情調。還記得美食熱愛者鐘潔玲曾寫過一本名為《此味只應天上有》的書,一度非常走紅。她在書中推薦云南麗江的“毋米粥”,“毋”者,“無”也,“毋米粥”,即將米煮到“水乳交融”,只留米的精華,不見米的程度,清甜綿軟順滑,乃是“粥”中極品。
食粥,雖是中國社會最普遍的飲食現象,但它同清靜淡泊的茶文化一樣,須慢慢品味,方能體會粥中的美味;熬粥更不可心急,要有一種淡然溫厚的心境,慢慢熬制,才能熬出粥中的精華。所以老人常說:“女人不過40歲,是熬不出一鍋好粥的。”此言得之。
如今,我每天清晨或傍晚,都會靜靜地守在廚房鍋灶旁,在乳白色水霧的蒸騰繚繞中,不慌不忙地輕輕攪動湯勺,心底又情不自禁地感嘆:遠在黑龍江的母親,什么時候能再來威海,喝上一碗女兒熬煮、曾孫捧上的暖粥呢?
(責編:孫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