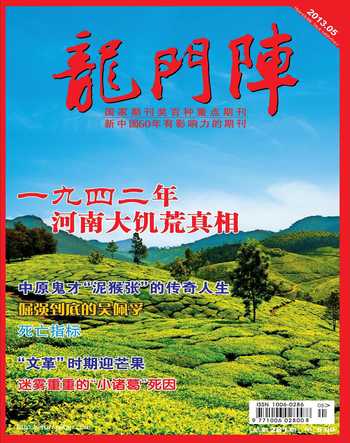錢勰的傲骨
晏建懷
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xiàn)實,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的,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史稱“熙寧變法”。這場牽動全國的政治大變革開始之后,朝廷上下波詭云譎,黨爭驟起,許多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有的謫貶海外,有的老死蠻荒。于是,見風使舵者多了,明哲保身者多了,士風早已不似當年。不過,盡管政治運動殘酷,但士大夫中卻始終不乏堅守本真和原則者,他們一身傲骨,兩袖清風,錢勰就是這樣一人。
錢勰是五代吳越國最后一位國王錢俶的孫子。趙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錢俶納土歸降,免去了一場血雨腥風的生死大戰(zhàn)。錢俶歸附以后,宋朝的歷代皇帝都對錢家給予特殊的優(yōu)待,錢俶和他的后代在宋朝世世為官,屢受要職,如錢俶被相繼加封為“淮海國王”、“南漢國王”、“鄧王”等。
錢勰在宋朝做官,早就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他像祖輩父輩一樣,忠心于大宋王朝和皇帝,更忠實于士大夫的精神和操守。他任流內銓(編者注:吏部官職署名,負責選拔和管理中下層文職官員的機構)主簿期間,雖然官職卑微,但由于能力很強,業(yè)績突出,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宋神宗曾單獨召見他,與他交流政事和學問,非常驚喜,當面表示:“將任以清要官。”時任宰相的王安石正推行變法,急需人才,他聽到這個消息,趕緊安排弟弟王安禮來找錢勰談心,說愿意推薦錢勰擔任御史,頗有拉攏之意。對于錢勰這樣一個低級事務官來說,這無異于“天上掉餡餅”的大喜事。當時王安石如日中天,官員任命他說了算,而且皇帝也有言在先,所以,只要錢勰輕輕點頭,這事立馬能成,但錢勰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錢勰為何拒絕?原來,王安石作為鐵腕宰相,一直以支持和反對變法為用人導向,支持變法就迅速提拔,反對變法則堅決不用,甚至很多官員還因此丟官去職,貶謫蠻荒。錢勰一直以清流自居,對變法持反對態(tài)度,因此,即便高官厚祿,封官許愿,他都敬謝不敏了。王安石知道錢勰不依附自己,便沒有重用他。
錢勰當過外交官,留下了堅拒禮金的千古佳話。為了爭取力量抵御遼國,宋朝一直與位于朝鮮半島的高麗國保持友好關系。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高麗的老國王病逝、新國王登基,宋神宗派錢勰等人出使高麗,參加吊唁和登基儀式。錢勰向宋神宗辭行時,問為何選中他。宋神宗說:“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面對皇帝的信任,錢勰心懷感激,暗下決心,一定要像已故宰相呂端當年出使高麗一樣,保持宋朝士大夫的氣節(jié),不卑不亢,不拿不貪,出色地完成任務。錢勰到達高麗后,高麗新國王果然客氣,除了讓他吃好、住好、玩好外,還多次送重金給他,但均被錢勰一一拒絕。不想,在回國的路上,高麗國王又派使者飛奔而至,一定要送給錢勰4000兩銀子。錢勰奇怪地問使者:“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并堅決地再次拒收。使者一聽,立刻痛哭流涕地說:“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副使)已受。”其實,當時士大夫出使沒有幾個不收紅包的,這是心知肚明的“潛規(guī)則”,他的副使都坦然收受了。但錢勰卻義正詞嚴地說:“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錢勰既不為使者的“脅迫”而心軟,又不因“潛規(guī)則”而接受,他愛惜節(jié)操就像鳥兒愛惜羽毛一樣。
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錢勰出任開封知府,但開封知府從來就是一個燙手的山芋。開封府作為京都,到處是老奸巨猾的大官小吏,到處是耀武揚威的皇親國戚,就連開封府內的小吏,也個個是使棒子的高手。錢勰走馬上任之際,開封府的老吏知道他既廉潔又剛正,還是個不開竅的榆木腦殼,便想給他來個下馬威。老吏把前街的混混、后巷的癟三都找來,擊鼓告狀,幾天下來,訴狀多達700份,堆積如山,老吏便等著看好戲。誰知,錢勰思維敏捷,能力甚強,隨來隨審,剖決如流,一月下來,無一件積案。那些平時橫行霸道慣了的“官二代”、“富二代”,都懼怕錢勰,只好暫時收手;有些個案,哪怕是宰相批條子、打招呼,錢勰也置若罔聞,照樣從嚴、從快處理。由于錢勰做事太認真,上自宰相,下至小吏,得罪的人真不少。所以,他這個開封知府注定干不長。不久,錢勰就在一片唏噓聲中,外調越州(今浙江紹興市)任職去了。
宋哲宗繼位后,翰林缺學士,就把錢勰召回京城,讓他出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當時的宰相是章惇,雖然博學善文,為人剛直,但心胸狹窄,報復心重,凡得罪過他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即使多年好友,也毫不留情,如蘇東坡曾因政見不同,與其爭執(zhí),便被一貶再貶,最后竟被貶到孤懸海外、偏僻蠻荒之地海南。錢勰為中書舍人(編者注:官名,起草有關詔令)時,曾奉旨為皇帝起草貶謫章惇的詔書,其中寫道:“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無大臣之節(jié)。”雖然這評語經(jīng)皇帝審閱并同意,但錢勰擔心章惇把這筆賬算在自己頭上,故不敢接受。宋哲宗稱自己知道此事,不用避諱,而章惇表面上也無怪罪之意,背地里卻發(fā)動御史不斷彈劾他。錢勰因此罷官,貶至安徽與江西交界的池州(今安徽池州市),任期未滿,便溘然早逝。不過,在那個政局驟變,黨爭激烈的時代里,錢勰倒也死得其時,否則,以他這一身嶙峋傲骨,倘若晚些時日,其結局也許比蘇東坡還慘,最后貶死于茫茫海外也未必不可能啊。
(責編:孫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