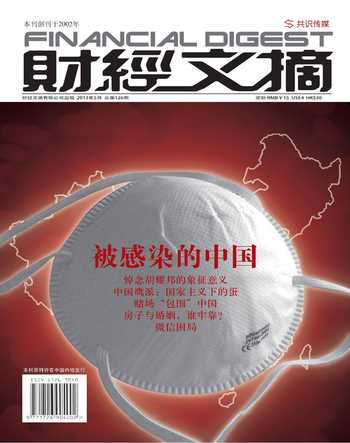微信困局
李馨


純屬誤會!
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微信收費”這事兒還是蠻恰當的。
在年初風起云涌的通信熱點中,“微信收費”力壓群雄,它包著“用戶利益”的精裝外衣,在網絡中被瘋狂轉載,迅速傳播。
信的轉,不信的也轉,人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發泄對運營商的長久不滿。而工信部的表態、輿論領袖與業界精英此起彼伏的聲音、媒體的熱炒都讓這團迷霧愈顯撲朔。
運營商糾結著信令被看成是狡辯與意欲雙重收費的前臺詞,馬化騰的“微信絕不會向普通用戶收費”被抓住“普通”二字的小辮子成為收費的“宣言”,苗圩的“運營商收費是合情合理的”在各大媒體的標題上變成了“微信有收費可能”,并再次加劇了人們對于“微信收費”的臆測。盡管最后“微信將向用戶收費”這一偽命題在4月中旬以后沒有了懸念,但互聯網企業與運營商之間的問題,才剛剛開始。
4月20日,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微信跑贏了電話和短信成為通信之王,再次引發了關于信令的爭議。到了4月23日,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通信發展司司長張峰表示:“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新業務是否收費由市場決定。”這一明確的表態沒有明確人們心存的疑慮,也沒有為“微信收費”畫上完美的句號。
既然無法看清未來,不如撇掉這些久久不退的表面浪花,找回“微信收費”之爭的核心。
收與不收?無解
4月23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文章引用了游友移動創始人李劍波的話來解釋信令:“兩個用戶之間打移動電話,基站通過信令尋呼找到用戶,并告訴用戶對其分配了哪些資源,何時可發起連接等等,而手機需要向基站回復的內容,也通過信令傳遞。”不停地向服務器發送心跳包的微信導致了基站信令資源的頻繁占有,遠遠超出了電話僅在撥通時所占用的資源。
可以說,“信令風暴”是個真命題,它確實是運營商面臨的困境,北京郵電大學舒華英教授肯定了這一說法。“信令就像是高速公路的指揮通道,指揮通道占得太多了必然要出事的。”他認為,既然占用了這部分資源那么收費也是必要的一種手段。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張昕竹也認為“現在需要適當地考慮”對信令進行收費,因為不收費有可能會帶來對信令資源的浪費行為。“騰訊需要修改底層軟件,運營商需要修改承載的網絡,網絡優化可能減輕信令的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最有效的收費方式就是向用戶收費。誰受益誰付費,收費越下沉越接近用戶,收費有效度越高;而越遠離用戶,定價越可能扭曲。傳統運營商的商業模式就是對用戶直接收費,然而互聯網產生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互聯網公司之間的競爭不僅是產品業務的競爭,更是模式的競爭。這就與運營商的傳統商業模式產生了巨大的裂縫,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當老模式與新模式一起出現在用戶面前,用戶的心自然偏向了互聯網企業。
收費有其合理性,但張昕竹也認為:“我覺得到目前來講收費還不是特別好的解決辦法。微信是一種很偉大的產品,這個產品它自己都沒有收費,沒有商業模式,收費會把它扼殺在搖籃里。”
收費既沒到時候,也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而微信包括其他OTT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占用信令資源,然后簡單付費的問題,還涉及到整個游戲規則。運營商通過壟斷維持自身商業模式的有效性,提供普遍服務,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這個圍墻慢慢被打破了。新的格局出現,公平卻沒有建立起來。
規則?待定
“這是個開始,不會是結束。”
不止一個人在提到微信一事時這樣說,OTT對運營商的沖擊不僅不會止于此,而且會帶來越來越大的沖擊。在這一過程中,要解決的已不是一個騰訊的問題,而是游戲規則。
隨著“電信”一詞的定義被持續擴大,原本相對于信息服務、增值服務而言的電信概念越來越模糊,就如微信,它是互聯網服務,卻具有通信、電信的屬性,但并不是電信級產品。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大多數人卻處于“電信”“通信”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境之中。
從功能來講,微信等應用提供的服務和電信提供的業務沒太大區別,只是通話質量有些區別。但隨著帶寬增加、網絡改進、應用更新,擁有和電信服務相媲美的體驗并非不可能。
張昕竹說:“從建立游戲規則的角度,需要未雨綢繆,現在已經不是簡單的微信問題了,涉及了整個電信、通信架構。游戲規則從法律層面要明確整個市場競爭的框架,前一段時間老談‘電信法,電信法還沒出臺就過時了,再談就應該是‘通信法了。從法律框架和監管層面來說,也要有很大的一個變化。微信只是一個個案,現在很難說收費好還是不好,它是雙刃劍。騰訊自己也承認,費用讓運營商承擔,結果就是商業模式被摧毀,運營商的盈利部分,短信、移動語音就會像固話、長話的結果一樣。”
隨著強調產品競爭的電信時代到了強調生態、平臺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完善整個生態系統的建設實現共贏才是各方希望看到的結果。OTT需要運營商搭建網絡,運營商需要OTT貢獻流量,這兩者并不是相悖的。最終需要建立規則,然后把市場的問題還給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