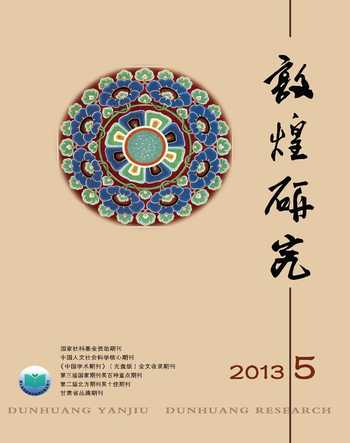敦煌壁畫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對置成因分析



內(nèi)容摘要:初唐以降,敦煌石窟諸多經(jīng)變在繪制位置上日趨固定,某些經(jīng)變相互間逐漸形成一種空間搭配關(guān)系。其中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即是一例,二經(jīng)變多繪于主室南、北壁,呈對置之勢。此格局被后期諸窟所沿用,并最終形成一種流行范式。這種范式既表達了彌陀與藥師二法門的有機融攝和互補,又彰顯了佛教對世俗凡眾死生兩極的無微關(guān)懷。
關(guān)鍵詞:西方凈土變;藥師凈土變;對置;信仰
中圖分類號:K879.21;K879.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5-0051-09
On the Contraposition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Western Paradise Sutra and of the Bhaisajya-guru Sutra in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MI Defang
(Institute of Dazu Rock Carvings, Dazu, Chongqing 402360)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locations of many sutra illustrations had become more fixed in Dunhuang caves, and some of these illustrations appeared in opposed pairs, such as the illustrations of both the Western Pure Land and the Bhaisajya-guru's Pure Land, which were usually painted on the south and north walls, respectively, in the main chamber. This tradition was followed in later times and became a fixed model, not only expressing their mutual complementarity, but also emphasizing the meticulous care of Buddhism for the life and death of humans.
Keywords: Illustrations of the western paradise sutra; Illustrations of the Bhaisajya-guru sūtra; Contraposition; Faith
收稿日期:2011-08-01
作者簡介:米德昉(1972- ),男,甘肅省永登縣人,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佛教文化藝術(shù)研究。
初唐以后,敦煌石窟中一些經(jīng)變相互間逐漸形成一種穩(wěn)定的對置關(guān)系,這種對置在石窟左、右壁間表現(xiàn)得尤為典型。諸經(jīng)變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組對置是: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法華經(jīng)變與華嚴經(jīng)變、報恩經(jīng)變與思益梵天問經(jīng)變、彌勒經(jīng)變與天請問經(jīng)變等。本文選取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對置之案例,在分析二經(jīng)變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與意義的基礎(chǔ)上,探討其對置形成的原因。
在敦煌石窟中,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最為常見的布局是,前者居于主室南壁,后者居于主室北壁,二者在空間方位上呈對稱狀。此格局形成于初唐,之后成為固定模式歷代相循。目前學界盡管對此現(xiàn)象有所關(guān)注,但深入研究尚未展開。如藤枝晃在《關(guān)于220窟改修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到“(敦煌)許多洞窟里,《西方阿彌陀凈土變》和《東方藥師凈土變》于左右壁相對,其他經(jīng)變,也不雜亂。可謂有一種原則,但不嚴格,容許有所改變”。藤枝晃氏將此種經(jīng)變布局稱作“對稱式”,對于其成因、意涵等未作論述①。楊明芬在《唐代西方凈土禮懺法研究》一書中認為: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對應關(guān)系表達了佛教十方“宇宙空間觀”,反映了佛對眾生“未來生命”與“現(xiàn)世安樂”的雙重關(guān)照②。楊氏只是提出了極具啟發(fā)意義的觀點,但對于此對置的形成及其思想關(guān)聯(lián)等沒有展開深入論述。另外,梅林[1]、王靜芬[2]、王中旭[3]等不同程度地論及敦煌石窟經(jīng)變對應問題,但針對西方凈土變和藥師凈土變之對置,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尚未展開,鑒于此,筆者以為有必要在前賢研究的基礎(chǔ)上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 唐前期敦煌石窟
彌陀與藥師圖像之造作
西方凈土變的造作主要依據(jù)為凈土三經(jīng),即《無量壽經(jīng)》(曹魏康僧鎧譯)、《觀無量壽經(jīng)》(劉宋畺良耶舍譯)和《阿彌陀經(jīng)》(姚秦鳩摩羅什譯)。在西方凈土變產(chǎn)生之前,反映凈土意義的造像基本以單體彌陀(無量壽)像或說法圖為主。我國彌陀佛像東晉時已有造立,《歷代名畫記》卷13云:“(戴逵)曾造無量壽木像,高丈六,并菩薩。”[4]《法苑珠林》載,孝武寧康三年(375)釋道安“于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5]。南北朝時期造像增多。如:炳靈寺第169窟第6號龕西秦建弘元年(420)時西方三圣組像[6]、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的劉宋元嘉二年(425)西方凈土變浮雕[7]、四川茂汶出土的南齊永明元年(483)石刻無量壽造像[7]、麥積山石窟第127窟北魏西方凈土變[8]、南京棲霞寺千佛巖南齊時無量壽雕像[9]、河北邯鄲南響堂山第2窟北齊浮雕凈土變(現(xiàn)存美國菲利爾美術(shù)館)等[10]。隋唐以前,彌陀造像以單尊或二菩薩脅侍者為多,其凈土變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畫面結(jié)構(gòu)簡單,內(nèi)容稀少。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nèi)容總錄》,將西方凈土變分為觀無量壽經(jīng)變與阿彌陀經(jīng)變,二者在圖像格式上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兩側(cè)多出未生怨、十六觀及繪在畫面下部的九品往生[11]。根據(jù)彌陀信仰的流布及其影響力來看,敦煌石窟在唐前期應該有較多的彌陀類造像,但由于諸多石窟經(jīng)過后期改造、重繪、整修等擾攘,目前所存彌陀造像遺跡較少。現(xiàn)在能夠確認的即是西魏第285窟彌陀說法圖,共有相同的兩鋪,分別繪于東壁門南、北。畫面構(gòu)圖為主尊結(jié)跏趺坐,施說法印,左右脅侍四菩薩及四弟子。此窟有大統(tǒng)四年、五年(538、539)發(fā)愿文題記[12]。還有北魏第251窟、西魏第249、435窟南、北壁繪有蓮池說法圖,有學者視此為西方凈土變之雛形③。另外,隋代第393窟西壁繪一鋪彌陀凈土變相,構(gòu)圖上突破說法圖藩籬,已是成熟的經(jīng)變圖像。
藥師凈土變所依據(jù)的經(jīng)典主要有《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jīng)》(西晉帛尸梨密多羅譯)[13]、《藥師琉璃光經(jīng)》(劉宋慧簡譯,已佚)、《佛說藥師如來本愿經(jīng)》(隋達摩笈多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jīng)》(唐玄奘譯)、《藥師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經(jīng)》(唐義凈譯)[14]。此五種譯本,后來較通行者為玄奘本。
唐前期藥師像的造立亦流行各地,但所存數(shù)量少于彌陀造像。目前能見到的如炳靈寺第169窟第6龕,繪有一尊小禪定佛,榜題“藥王佛”[6];云岡石窟第11窟(云岡中期,471—494)西壁一小龕下有銘文:“佛弟子□□/□沙□□芽(藥)師琉璃光佛一軀……”[15];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壁彌勒龕內(nèi)有孝昌元年(525)時期藥師佛造像[16];河南浚縣發(fā)現(xiàn)的武平三年(571)三層四面造像碑中,西面下層龕為藥師佛結(jié)跏趺坐說法圖,龕下殘存題記中有“□師佛……”等[17]。
敦煌藥師經(jīng)變最早出現(xiàn)于隋代石窟,有4鋪,即第394、417、433、436窟。其中第394窟繪于東壁門口的上方,第417窟繪于窟頂后部平頂下半,第433、436窟繪于窟頂人字披東披。第417窟藥師經(jīng)變形式為:藥師佛結(jié)跏趺坐于中央蓮臺,右手施說法印。八大菩薩侍立兩側(cè),佛座前畫一多層輪式燈架,燈架兩側(cè)分別跪著六位手捧燃燈的十二神王。第394窟藥師經(jīng)變的構(gòu)圖第與433窟的近似,藥師佛結(jié)跏趺坐于中央,兩側(cè)立日、月光二菩薩、胡跪十二神將及立兩燈架。初創(chuàng)期藥師經(jīng)變構(gòu)圖簡單,總體章法尚未脫離南北朝時期說法圖的形制。
進入初唐,敦煌石窟彌陀與藥師造像形式日益成熟,由過去簡易的說法圖格式演變?yōu)轼櫰拗频淖兿啵覕?shù)目亦與日俱增。現(xiàn)存西方凈土變共有181鋪(觀無量壽經(jīng)變92鋪,阿彌陀經(jīng)變89鋪),其中,隋1鋪、初唐18鋪、盛唐25鋪、中唐44鋪、晚唐32鋪、五代21鋪、宋16鋪、西夏24鋪。藥師經(jīng)變共112鋪,其中,隋4鋪、初唐1鋪、盛唐2鋪、中唐23鋪、晚唐32鋪、五代32鋪、宋8鋪、西夏10鋪。從對此數(shù)量的對比發(fā)現(xiàn),在信仰勢力上彌陀盛于藥師,前者在盛唐時已進入興盛期,后者則晚至中唐。五代以后,佛教在敦煌的興盛期已過,雙方經(jīng)變繪制減少。
二 敦煌石窟西方凈土變與
藥師凈土變之對置
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之交涉始于初唐,中、晚唐及五代為高峰期,至宋、西夏數(shù)量下降。現(xiàn)就二經(jīng)變在石窟中的對置情況加以列表,分析如表1:
由表1統(tǒng)計看,我們可以得出這些結(jié)論:
(一)在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的對置中,多數(shù)情況為前者居于主室南壁,后者居于主室北壁。梅林先生從律寺角度出發(fā)對此方位進行了解釋,認為:“莫高窟受鳴沙山自然山勢影響,坐西朝東,作為石窟寺建筑,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南北開向不符。既然石窟寺與律寺同構(gòu),尤其是二者附洞與同類配院(殿)方位上的關(guān)聯(lián),使我們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從南北開向來審視莫高窟石窟寺。如此,則其南壁實當西壁,北壁實當東壁。”[1]由此看來,西方凈土變居南壁(代表西方),藥師凈土變居北壁(代表東方)符合方位關(guān)系。
(二)從初唐至西夏時期,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對置達77例,其中各自獨占壁面,單一對置的情況較少,有16例;余則二經(jīng)變分別組合其他經(jīng)變形成對置關(guān)系。
(三)在各自壁面的經(jīng)變組合中,中唐時期同壁經(jīng)變數(shù)量以2鋪居多;晚唐五代時期,同壁經(jīng)變數(shù)量驟增,以3、4鋪組合為多,如第138、61窟單壁繪制不同經(jīng)變5鋪。這一階段增加的經(jīng)變有報恩、楞伽、思益梵天問、天請問、華嚴、法華等,并有如意輪觀音、不空 索觀音類密宗經(jīng)變出現(xiàn)。固定搭配格式中,除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外,尚有法華與華嚴、報恩與思益梵天問、彌勒與天請問等經(jīng)變的對置。一窟之內(nèi)繪制幾幅乃至十幾幅不同內(nèi)容經(jīng)變,這一現(xiàn)象正好說明了這一時期敦煌佛教諸派雜糅的發(fā)展風貌。
(四)宋西夏時期,敦煌諸石窟經(jīng)變種類明顯減少,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在對置形式上仿佛回歸到初唐,呈現(xiàn)單一對應態(tài)勢,原先一些組合經(jīng)變突然消失。
(五)在同壁多鋪經(jīng)變組合中,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位置有向壁面中間靠攏之勢,尤其當經(jīng)變組合數(shù)量以奇數(shù)出現(xiàn)時,此二經(jīng)變基本都占據(jù)中間位置。據(jù)此我們認為,敦煌石窟在處理南北壁經(jīng)變搭配時,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在各自壁面的經(jīng)變中居于主導地位,凸顯了彌陀、藥師二佛在表達義理思想中的統(tǒng)領(lǐng)性格。
三 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
對置成因分析
在諸凈土思想的流布中,彌勒信仰興起最早,印度部派佛教時期就已有彌勒信仰流傳①。自傳入我國,彌勒信仰便風行一世,南北朝時期其造像極為普遍,數(shù)量超過了釋迦以外其他佛像①。克孜爾、庫木吐拉、敦煌、云岡、龍門等地石窟都有彌勒造像,說明彌勒凈土信仰在隋唐以前極有勢力。7世紀末,武則天謊稱彌勒下世,登基稱帝,從而使彌勒信仰遍及全國。玄宗時因民間發(fā)生“假托彌勒下生”擾攘民心之事,遂敕令“禁斷”,自此彌勒信仰受抑[18]。
中唐以前,藥師信仰尚未完全興起,敦煌石窟西方凈土變基本與彌勒經(jīng)變相對置而出現(xiàn)。二者對應在盛唐時尤為頻繁,彰顯了這一時期西方凈土與兜率凈土在信仰層面上的融合[19]。但在此交涉中,西方凈土信仰逐步走向繁盛,彌勒凈土信仰則日趨式微,這種變化根因除了上述社會政治原因外,在于二者法門之境界差異。詳言之,其一,西方凈土為佛層次;彌勒凈土則處于菩薩階位。其二,西方凈土較之彌勒凈土更為殊勝、莊嚴。其三,彌陀本愿勝于彌勒本愿,更能贏得信眾皈依。其四,彌陀法門修持方式更為簡易,且借助佛愿力加被更易往生。其五,彌陀現(xiàn)已教化眾生,使成菩提;彌勒則為未來佛,至五十多億年后才下世說究竟法②。唐道鏡《念佛鏡》卷2《念佛對彌勒門》言:
問:何故不念彌勒生兜率天?云何念阿彌陀佛往生凈土?答:為兜率天不出三界,天報既盡,還墮閻浮提,所以不愿生天。若往生凈土,出過三界,直截五道,一生彼國,直至菩提,更不墮落,所以愿生。又兜率天少時受樂,彌陀佛國中樂最勝,故名為極樂。長時受樂,無有限期,以是因緣,勝于兜率百千萬倍。[20]
這些差異是彌勒逐漸讓位于彌陀而走向邊緣化的主要因素。
在彌勒信仰熱降溫、彌陀信仰日盛的過程中,藥師信仰漸次抬頭,在道俗間日趨流行③。表現(xiàn)在石窟經(jīng)變布局上,以往“彌陀對置彌勒”的格局被打破,藥師經(jīng)變擠走彌勒經(jīng)變,最終形成與彌陀經(jīng)變相互對置之定格。不過自此彌勒經(jīng)變并未在敦煌石窟消失,數(shù)量也未減少,只是在石窟位置中退居“二線”,要么與彌陀經(jīng)變并置,要么與藥師經(jīng)變并置。隋唐至西夏,彌勒經(jīng)變在敦煌石窟有100鋪之多,[12]286-287說明彌勒信仰亦有一定的勢力,只是已非主流而已。
早期藥師經(jīng)變在位置上處于窟頂或東壁門口上方等,窟頂處藥師經(jīng)變相關(guān)位置有彌勒經(jīng)變配置,由于案例少,故不能形成體系。
彌陀與藥師信仰的興起為二者經(jīng)變之對置奠定了基礎(chǔ),究其因,這種對應反映了二者在義理和思想方面的融攝與互補。
彌陀經(jīng)典云:阿彌陀在因位時,曾為國王,因聞佛法而“棄國捐王行作沙門,號曰法藏”,為證菩提道果,法藏在世自在王如來前發(fā)四十八大愿,法藏曰:“我建超世愿,必至無上道;斯愿不滿足,誓不成等覺。”[21]法藏本諸大愿,累劫修行,證得法身,號曰阿彌陀,座主極樂。西方凈土環(huán)境增上,人事殊勝,往生此土,永不退轉(zhuǎn)。阿彌陀佛以大悲愿力攝化有情,欲令離苦得樂,斷除生死。西方凈土依正莊嚴,微妙奇麗,“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西方凈土不僅為眾生成就了一個不可思議之美妙國度,敞開往生之門,同時,彌陀法門以其簡單易行之善巧方便,為眾生鋪設(shè)了一條求證究竟之路。《佛說阿彌陀經(jīng)》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zhí)持名號,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圣眾顯現(xiàn)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既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21]347
藥師佛以其十二宏愿給予世間有情濟世之道。藥師經(jīng)典稱:東方佛土,有世界名凈琉璃,教主藥師琉璃光如來。藥師如來在因地行菩薩道時,以大悲心發(fā)十二大愿,攝導眾生。東方凈土“亦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并有日光、月光二菩薩輔助教化,十二神將饒益有情。藥師佛依過去因中的本愿力及現(xiàn)證佛國之無邊功德,濟度眾生。依世尊開示,眾生只要按照藥師法門“至心受持”,即會免遭“九橫死”難,更“令諸有情,所求皆得”[22]。
藥師如來之十二大愿,重心在于發(fā)菩提心拔除眾生所受的一切現(xiàn)世之苦——疾病、貧窮、饑餓等,解決關(guān)涉人類切身利益的諸多問題,引導眾生在享受“現(xiàn)世樂”的基礎(chǔ)上發(fā)大乘心踐行佛法。對于世間人類而言,既得福報、眼前利益是消除當下困境之良藥,因而對此渴求尤為迫切。藥師法門以濟世為重,奉持藥師法門即可獲得一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之福益。
佛教諸經(jīng)稱,十方諸佛,佛佛平等,無有高下。西方凈土與藥師凈土,深大圓廣,統(tǒng)攝無量,二者“等無差別”。《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jīng)》云:“愿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而未定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有八菩薩,乘神通來,示其道路,即于彼界種種雜色眾寶華中,自然化生。”[22]406修持藥師法門亦可往生極樂凈土,可見二凈土思想之融合性。但作為釋迦施教之法門,雙方在依正行愿、善巧方便、果報功德等方面各有所重。此乃緣于眾生根性、時地因緣之別,佛陀遂開示不同法門,隨機攝化有情。《凈土十要》卷10云:“瑠璃世界釋迦亦勸往生。然藥師經(jīng)正旨為助生極樂。勸人息滅惑業(yè)成就念佛三昧。還同折門教意。非比阿彌如來純以念佛攝一切人往生彼土也。”[23]因此,我們看到彌陀凈土傾向于度化眾生,令之愿生極樂,成就菩提,永不退轉(zhuǎn)。藥師凈土雖亦敞開往生之門,但其“正旨為助生極樂”,重于眾生在世果報,獲得暫時精神解脫。
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一些抄經(jīng)中,經(jīng)末題記反映了功德主有關(guān)彌陀或藥師之信仰。如S.2838《維摩詰經(jīng)卷下》尾題中有云:
經(jīng)生令狐善愿寫,曹法師法惠校,法華齋主大僧平事沙門法煥定……愿圣體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遠,同氣連枝,見佛聞法,往生凈土。
P.2837V《辰年施入修造冊錄》有云:
白楊樹一根,施入修造……為亡母愿神生凈土。
抄寫于公元895年的S.1128“施舍疏”中有康賢者“為亡父母,神生凈土,合家保愿平安,施道場粟三碩,施入修造”。諸上題記反映了施主為愿自己過亡先人往生極樂凈土而作抄經(jīng)、供養(yǎng)等功德,可見彌陀凈土信仰所含攝之“度亡”性格。
而在藥師信仰方面,類似的功德卻折射了信眾對消災延壽等福德的訴求。陳文帝《藥師齋懺文》云:“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又,方憑藥師本愿成就眾生。”[24] S.0053《藥師如來本愿功德經(jīng)》卷末題記云:
□壽妻為身染患,敬寫此經(jīng)。
S.2616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jīng)》題記:
弟子賈崇裕愿平安,廣德二年(764)十二月十五日發(fā)心寫《藥師經(jīng)》一卷。
顯然藥師形象在信眾心目中是一個“救世主”、“大醫(yī)王”,是現(xiàn)世生活的福音。雖然藥師亦有東方凈土可資往生,但彌陀西方凈土以殊勝的依正果報和更為簡易的修行方式已深入人心,成就來世已有所依。唯眼前苦厄之解決尤為迫切,因而藥師佛以自己大智悲心所敞開之“消災延壽”法門贏得信眾由衷的青睞。
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代表了一西一東兩個佛國世界,彌陀、藥師二佛不獨在階位上相對等,他們所居方位亦呈對應之勢。因之將二經(jīng)變置于洞窟左右二壁,既體現(xiàn)了對等的信仰勢力,也契合了中國人追求對稱的邏輯心理。從佛教義理言之,釋迦開啟彌陀、藥師二法門,含攝出、入世之道,體恤有情,可謂悲智圓滿。
四 小 結(jié)
敦煌石窟諸多西方凈土變與藥師凈土變對置案例說明了佛教對眾生死生兩極的關(guān)照。早期佛教在義理思想上傾向于對眾生如何成就來世而廣開法門,因而重于“救死度亡”[25]。南北朝時期敦煌石窟中大量出現(xiàn)諸如“薩埵飼虎”、“割肉貿(mào)鴿”、“月光王施頭”等本生故事,通過舍身、自殘等行為獻身佛法,從而獲得圓滿果報。顯然早期佛教精神在于使人甘于忍受人生苦厄,在苦難中仰賴佛法,完全漠視現(xiàn)世之樂。自唐宋以來,佛教在中國化的進程中日趨世俗化,凈土信仰的隆興說明其對人生終極關(guān)懷一如既往。然而在當時,信眾是一批更為入世的群體,他們對來世充滿了向往,往生凈土是其信仰旨歸,但又不愿放棄對現(xiàn)世福報的追求。如果宗教既能滿足人生現(xiàn)世利樂之享受,又能達到未來終極之解脫,這是最能觸動凡眾心靈,使之稽首歸命的法門。釋迦隨順世間,巧施言說,開出濟世、度亡二法門;適化時機,契應常理,以大悲憫心救度法界有情眾生。
參考文獻:
[1]梅林.律寺制度視野:9至10世紀莫高窟石窟寺經(jīng)變畫布局初探[J].敦煌研究,1995(1):111-127.
[2]王靜芬.唐代莫高窟壁畫所見與畫史記載寺院的經(jīng)變題材比較[C]//池田溫,等.敦煌文藪(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217-256.
[3]王中旭.生天:《彌勒變》、《天請問變》的流行與對應——敦煌吐蕃時期經(jīng)變對應問題研究之一[J].敦煌學輯刊,2011(1):72-79.
[4]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M].余劍華,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4:123.
[5]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53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384.
[6]董玉祥.炳靈寺石窟第169窟內(nèi)容總錄[J].敦煌學輯刊,1986(2):148-158.
[7]劉志遠,劉廷璧.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shù)[M].北京:中國古典藝術(shù)出版社,1958:4.
[8]閻文儒.麥積山石窟[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189-192.
[9]項長興.棲霞寺千佛巖第一大佛——無量壽佛[J].江蘇地質(zhì),2000(4):199.
[10]劉東光.響堂山石窟造像題材[J].文物春秋,1997(2)27-47.
[11]史葦湘.關(guān)于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M]//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6-188.
[12]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內(nèi)容總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15.
[13]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21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532-536.
[14]釋印順.藥師經(jīng)講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0:13-14.
[15]閻文儒.云岡石窟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00-104.
[16]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M].東京:同朋舍,1941:308.
[17]白文.關(guān)中唐代藥師佛造像圖像研究[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48-155.
[18]王欽若,等.宋本冊府元龜:卷159[M].北京:中華書局,1989:328-334.
[19]張子開.試論彌勒信仰與彌陀信仰的交融性[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53-61.
[20]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47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127.
[21]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12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267-269.
[22]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14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05-408.
[23]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61冊[M].中華電子佛典協(xié)會,2009:753.
[24]高楠順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52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334.
[25]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61.
① 藤枝晃認為:7—10世紀莫高窟的單個洞窟,“常繪《東方藥師凈土變》于右壁,《西方阿彌陀凈土變》于左壁,再配以《華嚴經(jīng)變》和《法華經(jīng)變》,加繪其他經(jīng)變,右壁則以《思益梵天變》、《尊勝陀羅尼變》、《天請問變》為多,左壁則以《楞伽變》、《彌勒變》、《報恩變》為多。”見藤枝晃《關(guān)于220窟改修的若干問題》,載《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0年,第69—70頁。
② 楊明芬從信仰、經(jīng)變分布、對置原因等方面作了論述,認為:“在義理層面上,是以西方凈土和東方凈土代表十方,來表示佛教的宇宙空間觀;在信仰層面上,是以阿彌陀佛信仰作為未來生命的歸投者,以藥師佛信仰作為現(xiàn)實安樂的仰賴者。”見楊明芬《唐代西方凈土禮懺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83頁。
③ 持此觀點者有:段文杰《早期的莫高窟藝術(shù)》,《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1年,第173—184頁;史葦湘《關(guān)于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敦煌莫高窟內(nèi)容總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7—202頁;賀世哲《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與“雙弘定慧”》,《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shù)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shù)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0頁;王惠民《敦煌西方凈土信仰資料與凈土圖像研究史》,《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19、185頁。
① 此表內(nèi)容依據(jù)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nèi)容總錄》,其中“觀無量壽”、“阿彌陀”二稱謂是依據(jù)總錄,未加變動。
② 此鋪內(nèi)容以七軀藥師尊像為主,寧強先生認為表現(xiàn)的是藥師佛去病救災之宗教“儀式”(Healing Ritual)。NingQing, Art,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the Dunhuang Cave of the Zhai Famil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 20.
① 現(xiàn)存漢文記載最早的佛教經(jīng)典諸《阿含經(jīng)》中都提到了彌勒。《中阿含經(jīng)》卷13《說本經(jīng)》:“世尊!我(彌勒)于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如來。”(《大正藏》第1冊,第510頁下。)《長阿含經(jīng)》卷6《轉(zhuǎn)輪圣王修行經(jīng)》云:“當于爾時,有佛出世,名為彌勒如來。”(《大正藏》第1冊,第41頁下)《增一阿含經(jīng)》卷19云:“爾時,彌勒菩薩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大正藏》第2冊,第645頁上)
① 據(jù)日本學者塚本善隆統(tǒng)計,北魏在龍門石窟共造像206尊,其中有釋迦牟尼像43尊,彌勒像35尊,觀世音像19尊,無量壽像10尊。參見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東出版社,1974年,第260頁。葉昌熾氏認為“(南北朝時期)所刻之像以釋迦、彌勒為最多”。參葉昌熾撰、韓銳校注《語石校注》卷5,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453頁。
② 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在分析彌勒凈土衰落的原因中提到:一是佛的名號差異,彌勒的名稱只體現(xiàn)悲,而阿彌陀的名稱既體現(xiàn)了悲又體現(xiàn)了智,可謂悲智圓滿;二是本愿的差異,彌勒的本愿少,而阿彌陀的本愿多;三是現(xiàn)在說法,阿彌陀佛現(xiàn)在就在西方說法,而彌勒則要等56億7千萬年之后才下生。這三個差異導致彌勒凈土被彌陀凈土所取代。參見松本文三郎著、張元林譯《彌勒凈土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66頁。
③ 藥師信仰在敦煌較為風行,此不光表現(xiàn)在藥師造像的繪制上,僅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藥師寫本經(jīng)卷達295部。參見李玉珉《敦煌藥師經(jīng)變研究》,《故宮文物月刊》1990年第3期,第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