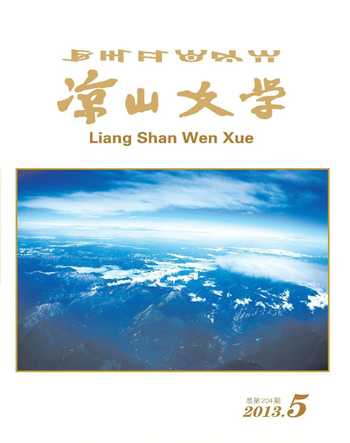遠方,有多遠
皇泯
寄語
回來哦,回來!
路,跌倒在峽谷里,呼喚是一架云梯。
回來哦,回來!
凍僵的波濤,從脹裂的冰縫里拱出了月亮圓舞曲。
回來哦,回來!
回憶是六月六攤曬的七種顏色,不會霉變。
回來哦,回來!
母親借助老槐樹凝神遠眺,伸長了擁抱游子的雙臂。
哦回來,時空沒有回音壁,心中有一只展翅的鳥,盤旋。
盤旋如巢,無論游子漂泊何方,都會棲落一雙小憩的翅膀……
讀書
有人說過讀飄逸的云,那云是語言;
有人說過讀凝固的山,那山是文字;
有人說要讀蚯蚓拱穿的彎彎曲曲的路,路是冷調子的月光;
有人說要讀螢火蟲燒紅的點點滴滴的血,血是暖調子的陽光。
還有人說要讀自己。
把自己寫在澎湃的波濤上,印進嬌嫩的綠葉,發表于無垠的天空。
最好是要目。最好是頭條。最好是封面的套色膠印。
你恐懼了,你也讀自己。
而你的影子每天要做三次大的修改,永遠也沒有定稿的時候。
二十四個春秋不短也不長,時間本來沒有長短。
從你知道讀書想讀書的那天起,你便開始讀自己,讀來讀去——
讀出了沒有斷句的破折號和沒有結尾的省略號。
頓號會得哮喘,逗號頭重腳輕。
分號背著沉重的包袱,而你又不愿在句號的圓圈里框死。
當你寫下自己的時候,所有的文字都要帶引號。
因為你寫了自己,你便不是讀者了。
源
翻過這個坡就是生育資江的那一片處女地了。
那纖索拉出來的號子,那槳葉搖出來的曲調,和那泡沫一樣漂游的故事,是在這里萌芽的。
有一系列隆起于水平線上的古銅色肌體,是連綿不斷的山脈在排筏的排列組合里編成壯觀的隊伍,卻節節敗退于吆喝聲中。
你赤腳去尋源。
有流水告訴你,小石子是長不大的山,小石子是來不及交媾的精子和卵子。
于是,你忘了拾綴黃昏里的童年。
一顆顆上天的眼睛連成一串項鏈,掛在歲月的脖頸,成為一位漂亮的公主。
你是這空曠而蠻荒之地的公子?
娃娃魚可知道你們的婚禮日?
在敞露神奇的詭秘的暖腹里,有你們孕育的娃娃魚。
許多年后,娃娃魚長不大。娃娃魚永遠是娃娃魚。
長不大的孩子不懂得父親和母親。
即使長大了的娃娃魚還是這源流的孩子。
漩渦
走進多少漩渦,也走出多少漩渦。
有一位十九歲的少女的目光是一支長篙,點破了你欲望的沖擊波,點穿了你結舌的語言。
有一片羞云飄來,云是思念染紅的。
有一片風老了,老了就有皺紋,皺紋,是思春的河流。
許許多多在寒夜的淚孔里放飛的星星,一直沒有歸巢。
沒有歸巢的再也不是青鳥,是一個眨著眼睛的謎。
那一位十九歲的少女呢?把十九年的歲月搓成了一根童話的長線。
她說,她要放飛風箏!
你的記憶卻亮開一把風剪,把線斷成了——
一截遠逝的幻影;一截近逼的殘骸。
走出多少漩渦,也走進多少漩渦。
地球,是一個小漩渦,人生,是一個大漩渦。
有一天,那旋轉的力會把你旋成一顆流星,也會把十九歲的少女旋成一顆流星,盡管不是同一個時刻,但會納入同一條軌道。
鄉音
一意孤行于歡騰的節日里,深邃的思想如潮潤了三百六十五天的鞭炮。
潰散的音樂,從窗口里溜出來,淤積在沉默的坑洼里,鋪平了家門前的路。
沒有雪,沒有冰凍,一雙溜冰鞋在進行系帶子的滑行。
好幾次險乎被傾斜的城市甩脫了,卻在慣性的回灣里旋成了一個螺旋體。
“不要給我鄉情的長鞭!”
“不要給我鄉情的長鞭!”
長長的回音又在抽著你。
如蒙眼驢背著磨盤重復乳白的童謠;
如老鷹旋著黑森林抄襲金黃的夢幻;
如晚風繞著炊煙詠嘆淡藍色的思念;
如月亮繞著地球轉,如母親繞著兒女轉。
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現實與夢境,天堂與人間,黑與白,陰與陽……
你被旋轉和交織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你拋下一堆爆過火星的紙屑,你再也不敢點燃那脆弱的引子。
你仰躺在波濤上,把胸膛裸露給蒼天,讓舒適的微笑漂入了親友的懷念。
也許這是最殘酷的訣別,也許這是最慈善的歸來。
那一條小巷
從一那條古老的麻石小巷,你來了。
小巷,便有一股涼爽的風吹入我燥熱的人生。
如今,我們又住在這條小巷里,小巷,這支破碎的竹笛還有圓潤的音響么?
上樓的梯級要拐一個彎,時間在這里折疊成重復的路。
你又不愿抄襲自己,正如我的囈語。
于是,你要走出這條小巷。
小巷生長一種愿望,嫩生生的沒有牙齒,咬不動古老的習俗,你就連皮帶殼吞了。
從那條古老的麻石小巷,你走出來了,盡管小巷之笛韻縈繞在你我之間。
你說,是路標——豎起來的小巷。
我想,是一串腳印——小巷那破碎的笛孔。
月夜
緩緩地月光,爬過高墻,爬過樹林,爬過草地,坐在石凳上。
今夜圓了的月,明夜次第殘缺。
而今,夜風不來,卷不走麻石巷口癡迷的等待。
幽會的日期已一推再推了,二十八年都等在這月兒圓。
臨行前,你邀約這個夜晚這個圓月,因此,所有的月牙都成了你漂回的船。
是銀河的岸被漩渦擊潰,時空隧道里沒有了載舟的水么?
是以往的圓月都流盡血色,蒼白成貧血的思念么?
整整二十八年,期望著白云是寫錯了地址而飄來飄去找不到收信人的信箋。
是的,在這石凳上,第一次從陌生坐到熟悉,盡管那一夜的時間太短太短,那一夜的思念卻悠長悠長呀!
石凳上的月光被陽光染紅了,那是永遠的羞澀啊!
泉歌
用一把龍頭二胡,從靜謐的月塘墈拉出了流淌的泉水。
潺潺的泉水,又洗亮了民間的小調、古老的謠曲和時髦的樂趣。
也許,是春水溫柔的誘惑,也許,是夏潮熱烈的召喚。
你要走了,帶著——
弓上顫抖的歡樂,弦上詠嘆的憂傷。
泉啊,一點也不知道嗎?
你已上好琴碼,調準琴弦,給古老的曲調凃上了黃燦燦的松香。
古陶罐
當音符撒向你光滑的裸體時,唇上已閃爍耀眼的釉彩。
古陶罐,象征一段復活的歷史。
象形文字或古樸的圖案,很自由,幾千年風暴,刮不亂舒緩的節奏。
我獨自舉著膜拜的經幡,將檐角翹起的銅鈴叩響。
寺門是神秘的洞窟,佛在青山外。
揮手拂去紛亂的流蘇,你瞧著我笑,一對雙星,活躍了凝重的夜。
隔了許多個世紀,拾起碎裂的陶片,想拼湊一個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的圓。
手指頭伸進罐口,找不到底。
再也關不住的心音,如鳥飛出來,整個季節,都布滿了生命的音符。
記得古蓮復活后,在陽光里開花。
我想堅貞的愛戀,便是古蓮。
不為現代生活飄香,卻裝飾了破碎的古陶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