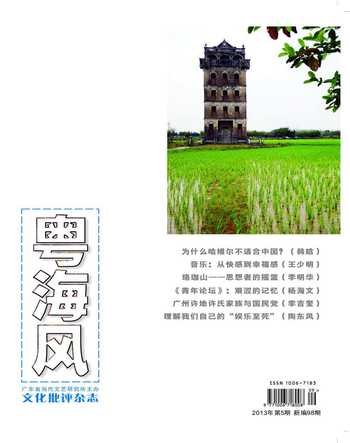當下散文詩寫作面臨的制約
[澳]莊偉杰
近年來,關于散文詩文體特征的爭論一直不斷,可以說,對散文詩文體的藝術探索至今依然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目前散文詩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那么,到底散文詩是什么,它與詩與散文的關聯及本質差異在哪里?應如何不斷強化其文體意識,讓散文詩回到它自身,成為一種別的文體所無法取代的、且與人的心靈和生命契合的獨立文體?散文詩所糾結的種種問題都需要每個熱愛散文詩的人們加以深思和做出回應。
耐人尋思的是,目前旅居海外的著名學者、20世紀80年代散文詩界的重量級人物劉再復,最近在一篇《返回散文詩》的短論中如是說:“散文詩介于散文與詩之間,這是常識。關于散文與詩的區別,論說很多,但在我看來,除了外形式(詩分行有韻律等,散文則不必)不同之外,內形式還有一大分別,這就是詩可以‘曲說,即可隱喻、暗示、通感等,而散文則只能‘直說,即直接表述散文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我曾把散文定義為作家人格的自我雕塑。那么,散文詩的好處,正是它既可以直說,也可以曲說,它無須詩的音樂節奏,但有內在情韻;它無須散文那樣敘事,但比詩更實更具體一些;它可自我塑造,但塑造的是內在的心靈性形象,而非外在的實體性形象。”作為切身體會或一家之說,劉再復是這樣理解散文詩并付諸寫作實踐的,并聲言選擇散文詩作為寫作的一種重要手段,是因為使用這種文體時心手都比較自由。因而,他慶幸自己始終沒有被“物化”、被“異化”的感覺,反而覺得寫作時個體精神贏得飛揚,自由贏得了實現。
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長期在散文詩創作與研究、編輯與出版等重要領域辛勤勞作的鄒岳漢先生,從自身的實踐經驗和對散文詩文體的認知出發,認為:“散文詩的獨立性,是在詩的大范疇內與其他詩體相比較而產生的獨特性。這種獨立性萬萬不可缺少,缺少了,散文詩就會失去它存在的價值。但如果把這種‘獨立性擴展到詩的范疇之外,那問題就大了——離開了‘詩性的基本規范,散文詩將失去與散文小品相區隔的最后邊界,散文詩也將喪失自己的家園。”(鄒岳漢:《編者的話:當代散文詩文體從理論到實踐的新發展》,《2011中國年度散文詩》,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他認為散文詩的獨立性只能在詩性的基礎上去尋求,否則會自我迷失和失去讀者,同時把“詩性”原則看作一個理論問題和重大的實踐問題,關系到散文詩文體的生存和未來的健康發展。應該說,這是目前較為流行的觀點。
以上兩種頗具代表性的言說,均有助于我們較全面地認識散文詩的文體特色、美學追求乃至運行機制。對此,我想補充的是,如果說一切好的文學作品首先都是跟心靈走在一起的,或者說,文學說到底是心靈外化的東西,散文詩尤甚。那么,作為一種語言藝術(形式),每種文體都應有屬于自己的身體語言和文體特征,這就注定了散文詩不僅具有“詩性”這種獨立性(或稱內質),同時應該具有散文的外在特征(或稱外表)。正是這種“內”與“外”合一互見(或稱“和合視界”),使得散文詩(文體)所具有的彈性與張力乃是其他文體所難以替代的。這讓我想起“香蕉人”的形象,即指在海外生長的華裔后代,他們外表上依然是黃皮膚黑眼睛,但內質上已經洋化(從小教育、生長環境、思維方式等因素使然),他們可能不是“混血兒”,也不算洋人,外在表征依然是華人,但形成的內在氣質已洋化了。正因為如此,用洋人或中國人稱呼他們都是不妥帖的,我們只能用“華人”或“華裔后代”來稱呼或界定。這就是“香蕉人”的獨特之處。可見,散文詩作為一種文體,具有自身獨特的美學原則,而這恰恰決定了其存在方式乃至生命方式。倘若說,對于小說,情節與形象塑造是營造和結構故事發展的關鍵要素;對于詩歌,韻律與分行是構造詩句的生命形式;對于戲劇,人物對話是顯示戲劇沖突的特殊途徑;對于散文,情感生命是維系散文內在規律的根本保障。那么,好的散文詩給人帶來的應是心靈與心靈的溝通交流,是詩性豐盈的語言盛宴,是精神對話的享受。這種對話,可以是愉悅性的,比如自然之愛與人性之愛;可以是靈動性的,比如生活情趣與人生感悟;可以是沖擊性的,比如靈魂救贖與生命懺悔;可以是自發性的,比如思辨色彩與精神啟示;等等。一言以蔽之,在筆者看來,散文詩應該作為寫作者(或知識分子)心靈與情感最為自由而詩意的一種對話方式。它與其他文學藝術形式一樣,同樣需要更多地融入人文情懷、生命精神和現實關懷。不是用刻意雕琢的文字,而是用生命用心靈去踐履。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探討,直面當下散文詩的現實境況,筆者想從整體性框架出發去思考散文詩的命運際遇,并就當下散文詩寫作面臨的三大制約加以透視,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同質化傾向與文體意識薄弱。在當下社會多元格局卻又如此“同質化”、“單一性”的功利主義消費市場的彌漫下,文化秩序的混亂、心靈世界的貧困、思想深度的缺失、傳統文化命脈似連又斷的嚴峻現實直逼我們。散文詩如果為了進入大眾視野而媚俗,或為了迎合主流而趨同,都是不足取的。這等于“心為物役”,即還不如不寫(劉再復語)。至于那種自設“小圈子”寫作,或四處拉大旗作虎皮,或只是以散文詩附庸風雅,給自己臉上貼上文化標簽,以達到能盡快弄出名堂之目的,企圖進入意識形態領域并獲得官方(獎勵)認同的,著實令人匪夷所思。更有甚者,動輒就居高臨下,好像自己就是散文詩壇的江湖老大,能給散文詩壇帶來不少好處,不惜代價到處占山頭,說白了就是想霸占散文詩壇的話語權。這些帶有功利化的思想實際上已喪失了作為文人應具備的操守,即并非為散文詩而散文詩,而是為了個人榮耀和功利而散文詩,致使散文詩界回到“小集團式”的寫作時代,乃至亦步亦趨于“同質化”傾向。君不見如此驚人的“熱鬧”已逐步走向驚人的庸俗,也同樣會走向驚人的荒涼。這并非聳人聽聞,而是當下散文詩壇存在的一種“怪圈”。其實,寫作本身是相當個人性的,但功在整體性的事業,而非功在某地某群。是故,任何群落如果只是一味突出各自的光點而掩飾自身的缺點,不僅不利于澄清詩史和整體的運行機制,也難以把人們引向和合的視界。
只有勇于正視現狀,才能讓散文詩理直氣壯地走上一條清明的藝術大道。那么,散文詩的發展是否迎來新契機呢?是否帶來了突破性的進展呢?是否取得了連當年的魯迅都想象不到的成就呢?這些問題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非三言兩語能夠述盡。的確,“有的作者對生命與存在的思考,有的作者在表現當代現實方面取得的進步,有的作者地域書寫方面的有益嘗試,都非常值得關注。”(黃尚恩:《散文詩的發展迎來新契機》,《文藝報》2013年4月15日)然而,我想指出的是,目前大量散文詩寫作在題材領域有趨同化的傾向,只要打開現在幾家專門性散文詩刊物就會發現,寫鄉土風情、地域山水題材的作品充斥其中,關注視點大多雷同和相近,這在無形中給散文詩帶入一種逼仄的書寫空間,即在寫作生態上出現某種欹斜。其實,散文詩書寫空間是相當廣闊的,既可以回到鄉土、回到童年、回到歷史,也可以回到都市、回到當下、回到自身,不管是往前走或往后走,還是向左望或向右望,抑或是朝上看或朝下看,都應當是精神的重塑而不是精神的消費,都應當是內在心靈性形象的展現,而不是停留于外在的實體性形象的摹寫。我們在現實(歷史)中的處境,涉及人本的種種困境,尤其是關注人的命運、生存境遇和精神家園,作為具有普遍性的主題,在散文詩寫作中盡管有或多或少的表現,卻缺乏獨特的個性內涵、闊大的境界和高遠的氣象。
如果說同質化或趨同化的傾向會給散文詩寫作帶來個性化的迷失,甚而遮蔽了個人真實聲音的發出。那么,文體意識薄弱則有可能讓散文詩自身自在本能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減色或退化。
好的散文詩與好小說、好詩歌、好散文一樣,一定要有文體意識。優秀的詩人作家在文體上有自己的覺悟和自覺。魯迅生前就相當重視文體意識,有“卓越的文體家”之譽。許多優秀的作家之傾心于文體一如十分欣賞自己最喜歡的東西。當然,不是每個作家都能成為文體家的。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據說“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漢語中也有“文體”這個詞,但這里所謂的“文體”并非我們理解中指不同體裁的“文體”。或者說,這里所言的“文體”,其內涵和外延都遠大于后者。
其實,作為外來詞的“文體”,即英文中的Style,據德國文學家威廉·威克納格(1806—1869)考證,最初應源于希臘文,后由希臘文傳入拉丁文,再傳入德文、英文和俄文。在英文中一般把Style譯為風格,俄語亦然。可以說,該詞在廣義上可用以指明包括繪畫、雕塑、音樂、建筑、文學等一切藝術的特性。把它譯為“文體”,乃專指義,用以指明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的語言特性。根據學者們大致認同的意見,文學中的“文體”具有三個層次的涵義:其一指文學體裁,這與漢語中的“文體”一詞的涵義大體相符;其二指語體,漢語中的“文體”在特定語境中也包含此層意義,在俄語中則有修辭的意義;其三指風格,這是“文體”的最高和最后的范疇(參見朱寬生:《在詩與散文之間》,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頁)。可見,文體意識和文體特點是一個作家的重要品格。換句話說,作家的創作,重要的是要寫出個性和這一文體的新品格來。
盡管文體多指作家富有強烈的個性氣質,不僅帶有作家自身強烈的風格特征,而且得力于自身駕馭文體時的自如操控力。這并非一蹴而就之功,乃取決于作家自身的辛勤磨礪和錘煉。唯有道行高深,功德圓滿者,方能成就也!其給予人的鮮明印象是,往往只言片語亦能令人為之悄焉動容,過目難忘,而且一眼便能清晰地辨認出這是出自某某作家之手筆,譬如我們讀魯迅的作品,這種感覺特別明顯。
當然,以上的說法并非要求每個散文詩作家都能成為文體家,因為體現在寫作上,這一種高難度的寫作,也是一種高標準嚴要求。然而,意識到和未意識到,或許會不一樣,無論是對于創作與批評。但愿我的這些帶有苛刻甚至尖銳的、但又是懇切的言辭,不至于讓廣大讀者反感,只要能給那些真正想用生命用心靈去投入和捍衛散文詩的耕耘者多少有所啟發,就足以欣慰一番了。
其二,當下散文詩精品力作明顯稀缺。著名散文詩作家郭風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散文詩創作本來就很難,更難出精品。魯迅的《野草》只有20多篇,但中國至今還沒有超越他的散文詩作品出現,雖然這些年出的散文詩集不少,總體上看創作水平有提高,不斷出現佳作,但還沒有哪本散文詩集達到《野草》那樣的高度。”(蕭風訪談錄,轉自嚴炎:《散文詩創作呼喚精品》,《中國散文詩》報2013年第3期)同樣的,當下散文詩界也缺少像彭燕郊《混沌初開》那樣獨特的、磅礴的、大氣的精品力作。它熔中西文化文學之精華于一爐,既探索了人的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又富有人類意識和終極關懷,庶幾達到中外散文詩史上難得的藝術高度。
為什么一些散文詩作者的文字雖然漂亮甚至也有動人之處,但最終還是從讀者心里飄忽而去?其中最大的原因顯然在于欠缺具有超越現實和穿透歷史的思想能力。究其原因,從整體上觀察,近些年的散文詩寫作缺少與讀者的對話關系,缺少與歷史(現實)的對話關系,缺少或疏于與自身的對話關系。在這種松散的狀態中,散文詩盡管不乏佳構之作,藝術有所嬗變,技巧逐漸成熟,但疲軟之態始終未有大的改觀,即:雅致佳作的多,大氣凝重的少;似曾相識的多,精品力作的少。這是整個散文詩界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對此,我贊同嚴炎先生在《散文詩創作呼喚精品》一文中說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容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創作出精品,但是愛好這個文體就要為之癡情。在這個關鍵節點,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作品說話,要堅守一種不出精品誓不罷休的精神。”可見,散文詩面臨的制約與困窘,并不因為現在有多少家專門性刊物和發表園地,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寫作隊伍有多壯大,也不在于一個人寫了多少作品,獲過多少獎,就等于沒有危機感。重要的是寫作者是否真正理解散文詩的要素,并具備散文詩的獨特品質。對于散文詩作家來說,保持作為知識分子即寫作者的思想風度和精神向度,在對現實保持警惕的前提下,其潛在的寫作立場和生命姿態不可或缺。
其三,當代散文詩批評的缺席與失語。相比較于其他文體,當代散文詩研究與批評相當薄弱,未能很好地起到推動散文詩發展的“輪之兩翼”的作用。這是散文詩面臨的最要命的一大困窘。如果說文學批評充當著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之間的橋梁,那么,散文詩批評乃是散文詩創作的延伸,是對批評對象進行藝術上的再創造,是在既定的話語中延展其審美內涵,使人們在這種再創造中領悟到散文詩作品某些更為豐富的審美信息和藝術內涵。既批判其得失,又揭示其運動規律,甚而直接影響到散文詩創作的品位格調和未來走向。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對散文詩進行“蜻蜓點水式”鑒賞與評介,這固然對散文詩創作多少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畢竟缺乏更為深入、系統、多元的透視批評,更難以進入理論性的高度闡釋、觀照和論述。加之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以及其中潛在的功利化思想泛濫,使得當代散文詩理論批評步履維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弊端。或零散寬泛,或思想僵化,或觀念滯后,或以個人好惡代替藝術審美,或缺乏深度與理性分析,或欠缺獨立思考精神和膽識勇氣,如是導致了散文詩研究與批評的嚴重缺席。可以說,散文詩批評的“失語癥”,既反映了散文詩當下批評標準的缺失與混亂,也導致了審美觀念讓位于現實利益的考量。縱觀之下,起碼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代散文界缺乏創作實踐、理論批評及學術研究皆能的“通才”;二是批評家學術素養的欠缺;三是散文詩批評原理的滯后且難有突破;四是偽散文詩批評的偏頗與乏善可陳;五是批評研究的形式化與創作難以產生互動。因此,如何推動散文詩批評回歸本質,堅守人文審美理想,是當代散文詩界理應關注的焦點。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