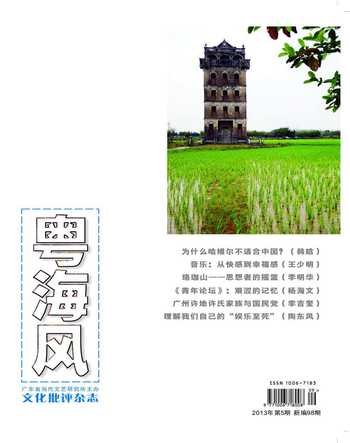辭職,民國政治舞臺的一大風景
顧土
說起中國古代的引咎辭職,我們就會記起春秋時的李離,其實李離最終的結果是引咎自裁,很是悲壯。中國古代辭職的很多,一種是實在不愿意干或者干不下去的,比如明朝的那幾位內閣首輔,幾十次、上百次的辭職,有的最后不得不掛冠而去;更多的人算是致仕,屬于告老還鄉,因為體弱多病、老態龍鐘,不能不辭職;還有一種是引咎辭職,其中常見的引咎辭職因為天災,古代的天災常常要由皇帝下詔罪己,也就是說把自然災害都算在自己頭上,而一些宰相和朝廷重臣也會因此辭職或被免職。將天災算作人禍,是我國古代的優良傳統,可惜,這一優良傳統后來恰恰沒有被承繼,還反其道而行之。
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引咎辭職也由來已久,到了近現代,更成為必須,否則,議會不答應,輿論不答應,民眾更不答應,當然,當事人也沒顏面繼續賴在那里。引咎辭職率非常高的那些國家,例如意大利、日本,貌似政局動蕩,實則是一種政治文明,這種文明一旦成為社會習慣,或者說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也就不會引發嚴重的后果,只是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必然環節,起碼憲政、社會秩序、行政機關的日常運轉都不致因此遭到破壞或癱瘓。
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下的引咎辭職,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決不會觸及最高統治者,而最高統治者很可能正是“咎”的最大責任人。
引咎辭職成為社會的習慣、政治的必須、現代文明的內容,需要有幾個先決條件。一是道德的力量巨大,面對罪過,不辭職就惴惴不安,心理壓力難以承受;二是輿論力量強大,面對悠悠眾口,面臨指責和質疑,無論是否直接負有責任,都沒臉面繼續占據著職位;三是官的利益極其有限,當不當官對個人和家庭的出路不存在決定性影響,生存、致富、出行、醫療,一切的一切,不會均系于此。假如大家的臉皮都很厚,道德的標準很低,輿論又常常無法發聲,沒有形成壓力,做官的誘惑卻極大,喪失了職務就喪失了一切,那么,主動引咎辭職就不可能成為常態,而撤職、免職和被辭職才是去職的主要形式。
一
1912年以后,中國進入了民國時代,憲政、共和的各種特點,或強或弱,幾乎都在這個時代有所顯示。辭職更是此伏彼起,常年不斷,上到總統、總理,下至部長、次長和地方大員,有幾次甚至十幾次的辭職經歷的不在少數。任職短命,成為民國歷史上的一大風景。盡管不停地辭職不利于當時中國政治的穩定,但在一個缺乏民主共和的經驗、素養和環境的社會里,也確實無法避免。
在民國政治舞臺上的各類辭職中,引咎辭職也是常事,被議會彈劾、受輿論抨擊、自認難辭其咎,都可能導致總統、總理、部長、次長這樣的高官辭職。以許世英為例,這位橫跨清朝民國兩代政治舞臺的活躍人物,可以說,遭遇過所有最難堪的政治場面。1912年,袁世凱任命許世英為大理院院長,此后歷任陸征祥內閣、趙秉鈞內閣、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盡管他也是國民黨員,但在宋教仁遇刺案的審理調查中,依然被黃興嚴詞糾彈。在津浦鐵路租車舞弊案中,他又被控受賄而辭職,并遭到京師高等檢察廳的傳訊。1923年時任安徽省長的許世英又因堅持裁撤安武軍而被迫辭任。1925年底,許世英任國務總理,在組織內閣時,未能獲得國民黨的支持,而且還遇到公務人員和國立學校教師包圍國務院索薪,只得很快辭職。不過,宦海沉浮近70載,他最后還是善終,作為“總統府資政”,以90多歲高齡病逝于臺北。
二
民國的引咎辭職習慣,體現最明顯的是政府首腦的辭職。這些辭職與近現代國家政治生活完全一樣,原因毫無二致,一是政治事件引發的危機,二是沸沸揚揚的丑聞,三是與議會、與總統的矛盾所致,權力無法施展,意圖不能實施,只得辭職了事。當然,最后一種并不都屬于引咎辭職,多數是無奈,也無所謂對錯。
五四運動和“三·一八”慘案是民國前期轟動中外的政治事件,引發的政治危機極其深遠,兩任國務總理也因此辭職。錢能訓在清朝時就官任陜西布政使,1911年又護理陜西巡撫職;袁世凱時代當過北洋政府內務次長、政事堂右丞﹐任過平政院院長兼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袁世凱之后又任內務總長,還做過代總理,1918年底任國務總理。這樣一位歷經幾朝數代的不倒翁,卻因五四運動而辭職,辭職前還特意免去國人矛頭所向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人職務。出身行伍的賈德耀始終在軍隊中任職,最后官至陸軍總長,這樣一位曾經握有兵權的軍人也難免引咎辭職的結局。1926年初,他先是代理總理,隨后又出任第39任國務總理,但在“三·一八”慘案后就不得不率全體內閣總辭職,以承擔責任。結果,從代到正式擔任,賈德耀任期前后僅僅64天。
因涉及丑聞而辭職的總理在民國歷史上也不少見。1912年8月,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9月任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雖說他是袁世凱的心腹,身為閣揆,有權有勢,但在刺殺宋教仁案中,有主謀之嫌,飽受輿論抨擊,還被上海地方檢察廳票傳,只得稱病辭職,顯示出民國初年政治舞臺的嶄新氣象。1913年11月底,《群強報》第二版報道稱:現任國務總理熊希齡在“為熱河都統時將前清行宮之古瓷器、書畫取去二百余件,現被世續查明,已請律師向京師地方廳起訴”;而《新社會日報》,則每天都有種種有關“熊希齡熱河行宮盜寶”的新聞見報,還配以“時評”;《神州》報也在頭版的顯著位置,極力渲染“熊希齡熱河行宮盜寶”事件。作為進步黨人組閣,熊希齡內閣被稱為“第一流人才內閣”,而熱河行宮盜寶的事實也并非媒體所報道的那樣,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丑聞渲染下,他也只能被迫辭職,下臺了事。
總理與總統失和,尤其是總理的施政方針常常遭到議會否決和攻訐,這是近現代政治生活的常態,雖然有弊,但更有利,最大的利就是防止獨斷專行和一言堂。所以,在民國,無論袁世凱還是其他意圖實行獨裁的統治者,其權力都是有限的,多方掣肘是民國政治的基調。“府院之爭”是民國初年的政治關鍵詞,而事實上,早在袁世凱時代,段祺瑞與袁的矛盾就已經彰顯,曾以辭職表示心意。他與黎元洪的矛盾,其實恰恰表現出總理和總統的權力都受到制約,沒有獨裁的可能。唐紹儀是首任內閣總理,只做了3個月,他敢于辭職,一走了之,正表明袁世凱這位大總統的權威也不是無限的。靳云鵬在徐世昌繼任大總統后,兩次出任總理,又兩次被迫辭職,也是因為權力實在有限。1922年7月,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顏惠慶因屢遭國會反對,不得不率內閣全體辭職;1926年5月,他再度組閣,竟然無人入閣,再次下臺。有人喜歡稱這些權力有限的人為“傀儡”,其實,民國歷史上那些握有實權的人也沒有過重的權力,段祺瑞就是典型,什么事情都有人公開反對,最后當個類似總統的“臨時執政”,連自己也近于“傀儡”,而且,“傀儡”與幕后的實力派往往還能相互制約,起到了限權的作用。
三
民國的辭職,不但是總理,還有國家元首,除了袁世凱外,民國政治生活中已經廢除了終身制。相對專制時代而言,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巨大進步。黎元洪和徐世昌各有兩次被迫去職或辭職的經歷。張勛復辟時,黎元洪棄職;曹錕賄選,黎元洪辭職。1919年6月,徐世昌向國會提出引咎辭職,后因挽留,繼續任職;可到了1922年5月,在曹錕、吳佩孚等人的逼迫下,又陷入困境。5月31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提議通告全國,宣布徐世昌誤國殃民,全體議員380多人一致通過,稱“徐世昌誤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認為他的總統屬于違法篡竊,應宣告無效。徐世昌只得在6月2日通告辭職,并發電自稱:“比年以還,勞精疲神,茹辛忍辱,調護群才,而不蒙相諒;遇事退讓,而猶以為爭;不私一財,而疑為虛偽。既已艱苦之備嘗,夫何權位之足戀。”同日離開北京,在天津當起了寓公。
民國時期,無論前后,其總理多半擁有留學背景和外交背景,內閣成員也是如此。這既說明在國庫空虛、國力微弱、百廢待興的局勢下,國際支持、國際承認的重要性,也證明了當時的對外開放程度和對現代知識的尊重程度,即便有些實權派自己出身鄉土,沒有多少現代知識,但在對外開放和對現代知識的尊重上卻十分一致。開放的背景和現代政治知識的素養,對引咎辭職習慣的養成,可以說,具有重要的培育作用。
民國的政治舞臺,之所以動不動就辭職,還在于對很多人而言,當不當高官大員,并不決定貧富,他們各有其他的職業或特長足以衣食無虞,有人能教書,有人辦教育,有人做學問,有人長于書畫,有人致力于實業,有人可以當律師,有人不妨辦報紙,比如蔡元培、章士釗、梁啟超、徐世昌、曹汝霖等等。這與今天的許多憲政國家的情形相似,做官并非各種生存方式中最具利益誘惑的一種,不做官照樣也可以出人頭地、一言九鼎、受人尊崇。
民國高官辭職習慣的形成,還在于高官備有能上能下的心理素質,即使總理也不例外。唐紹儀當過內閣總理后又任過中山縣縣長,連毛澤東都曾贊許有加。孫寶琦可以當國務總理,也可以再任審計院長、財務總長,以后再任總理,然后又任淞滬商埠督辦。錢能訓引咎辭職后又受命督辦太湖水利工程,還能應聘為外交部顧問。顏惠慶任過國務總理并攝行總統職權,而在國民政府期間,還可以先后任駐美公使、駐蘇大使等職。王寵惠辭去內閣總理后又成為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法官,1928年后歷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外交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職。汪大燮辭去國務總理后還出任過全國防災委員會委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而許世英這位國務總理,幾十年來更是上上下下,什么都可以出任。有些人盡管政府換了,旗號變了,職務降低了,但干得依然很賣勁,好像沒有丟臉的感覺。看來,那時的總理、部長、大使,其級別沒那么嚴格,在世人的眼里相距也不怎么遙遠,沒有所謂國級、部級、副部級、局級的差異,只是“崗位不同”罷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