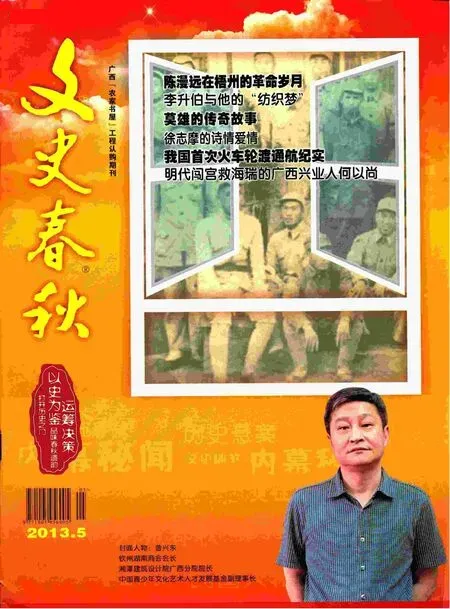李升伯與他的“紡織夢”
龔玉和
李升伯(1896—1985)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工商業界頗有聲望,為我國早期紡織實業家、教育家,新中國紡織機械制造業之父。
李升伯一生始終不渝地懷有一個夢想:渴望發展我國紡織工業,由紡織業起步,不僅使我國成為一個棉紡大國,而且成為服裝時尚的出口大國,繼巴黎、米蘭之后,將上海做成世界三大時尚中心之一。為實現此理想,李升伯身體力行,鞠躬盡瘁。
投身實業,在南通大力拓展紡織事業
李升伯189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22年留學美國,在賓夕法尼亞紡織學院攻讀紡織工程。此后,他先后到美、歐、日六國考察紡織工業,探索實業強國之途。他研究發現,歐美發展之初多由紡織工業起家,便提出培養人才、改良棉種、改進管理和自制紡織機械4項發展我國紡織事業的基礎工程。
20世紀20年代初,南通大生紗廠陷于危機。李升伯受大生紗廠張謇邀請,到南通考察了紡織業,并與張謇談起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前途,提出解決市場經營、紗廠管理及發展的想法,此想法與張謇的不謀而合。由此,張謇聘請李升伯擔任大生紗廠總經理。到任后,他憑借與錢莊的淵源,聘請了紡織管理人才,廢除工頭制,建立棉花基地,聚集了一大批紡織專才,創立了我國第一家棉產改進研究所。同時,他增加產品種類,提高棉布質量,并籌措資金,收回大生副廠,建立了發電廠,擴大了經營規模,生產成本逐步降低。經過10多年的努力,不僅挽救了大生紗廠,而且進一步拓展了張謇在南通興辦的各項事業。
李升伯特別注意搜羅人才,集聚智慧。當時,陳維稷剛好從英法學成歸國,在南通學院紡織科染化系任主任、教務兼教授,講授工業化學、染色學等課程。李升伯與陳教授一見如故,兩人對于我國紡織業的開拓與發展的見解竟然不謀而合。
抗戰時期,制定戰后紡織工業恢復規劃
抗戰初期,李升伯在上海的租界創辦了誠孚紡織專科學校(今東華大學前身)。后來,他帶領員工撤退到重慶,在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辦公地點,著手組織人員研究戰后重建規劃。
1939年春,陳維稷到安徽青陽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他受中共的指派回到重慶,擔任合作事業管理局特品供銷處協理。
不久,李升伯和陳維稷在重慶重逢,兩人都有百感交集之意。李升伯對陳維稷學非所用甚為不安,力勸陳維稷繼續回到紡織界工作。不久,陳維稷重拾專業,擔任了重慶民治毛紡織廠總工程師,并協同李升伯一起制定戰后恢復全國紡織工業的規劃。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李升伯出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副總經理、經緯紡織機械制造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有意在滬浙大展拳腳。他調集紡校師生,聘請紡織專家順利接管日本在華各紡織印染廠,迅速恢復生產,并將戰時擬定的復興建設發展紡織工業的計劃付諸實施。中紡公司聘請陳維稷先生出任上海的中國紡建公司第一印染廠廠長。李升伯到達上海后,中紡公司投入實際運作,公司即請陳維稷擔任中國紡建公司的總工程師,協助實施在重慶時制定的規劃。
重建恢復的第一要務是建立我國自己的紡織機械制造廠,李升伯等人多次帶領專家到杭州拱宸橋踏勘,決定將柳州經緯紡機制造廠之設備直接運往拱宸橋工地安裝,作為未來大型紡機制造廠的基礎設備;并招募專家負責實地籌建。
拱宸橋,地處江南水鄉,周邊地區盛產棉花、稻米,交通便捷;靠近大都會上海,原料、購銷、科技、市場信息均極為便利。土地物色洽購好后,李升伯即請著名美籍華裔建筑師作了初步設計,規劃設計未來工廠建筑之藍圖。他興奮地說:“多年抗戰,民生凋敝,百業待興,不過,等到我們的紡織母機啟動,將會生產大批價廉質優的紡機。屆時,不僅可以解決大江南北大批工人就業,民生得以改善;而且蘇北、江南,以至于華北、東北大平原,包括整個西南地區有大片棉田將為之受益。”
李升伯又道:“我看歐美諸國強盛之路,無不以發展棉紡業為始,今日之中國,經濟雖弱,然發展紡業有‘投資少、籌資易之稱,且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解決大批人員生計,此舉乃我們國家創強盛之始也,且人人要穿衣,產品無憂銷路。積累了足夠資金,就可進而發展重工業及其他產業。我們的經緯紡機制造廠生產之廉價優良織機投入市場,勢將產出更多棉布,制成輕柔之服飾,再在上海舞臺展示給世人;我國步巴黎、米蘭之后,成為全球三大服裝中心的設想,指日可待!”
從拱宸橋回來之后,李升伯等人入住西湖湖畔之新新飯店。此時,李升伯推窗外望,只見湖中之小島孤山歷歷在目,湖邊荷蓮斗艷;遠眺,湖上之白公堤,云柳擁堤沙。水上游船蕩漾,晚風拂過,送來陣陣荷香,令人心曠神怡,不由感嘆道:“吾生平發憤,多年來奔波操勞,別無所求,僅四件大事,惟獨一件,自制廉價優質之紡機乃吾心腹之憂。而今,完工之日,屈指可數。大功垂成,了卻心頭之愿,此生無求,別無他愿,足矣!”面對西湖美景,他禁不住觸景生情,感慨人生,又嘆道:“有道是‘五十而知天命,吾已五十又一,功績垂成,當全身而退。上海乃浮華之地,喧嘩塵囂,觀西湖之靜幽超脫,乃退身之階也。已令小女佩蕓在湖畔筑小屋數椽,聊以避風遮雨。西湖距吾鄉之上虞白馬湖,乘車只需個把時辰。垂暮之年,垂釣于白馬湖畔,泛舟于西子湖上,此生無求!”
此后,他一邊調集人力、資金籌建拱宸橋的經緯紡機制造廠,一邊在湖畔籌措建造一所小樓(北山路97號),委托龔文千設計圖紙、營造等,欲以此小樓作為退隱之所。經緯紡機制造廠開始緊鑼密鼓籌建之時,李升伯經常到杭督察業務,雖房子尚未完工,仍不忘前往工地察看。他一向仰慕西湖山水,念念不忘隱退后,能在杭州頤養天年。
解放在即,愿在新中國實現“紡織夢”
1948年6月后,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經濟上危機重重,已出現了全面崩潰的前兆。此時,經緯紡機制造公司在美國、瑞士訂購的大批紡織母機設備已準備就緒,整裝待發。這批機器也是戰后美國軍火工業轉為民用后的首批精良重型機械裝備。此時,陳維稷拜訪了李升伯,談及解放以后國家紡織業發展的前景。他說:“政權更換,然民生國計,百姓需要吃飯、穿衣乃生存必不可少之舉,希望李先生以及那批紡織母機能夠留在大陸。”他又說,“全國解放以后,如果有了這批紡織母機,不僅對億萬同胞的生計發生重大作用,而且,還能夠重拾當年在重慶規劃之紡織夢。”他力勸李升伯將這批母機運回祖國大陸。又說,此舉必將實現李升伯一生渴望實現的“紡織夢”。
1949年春,上海面臨解放之際,李升伯在上海寓所(茂名南路163弄1號)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是誠孚紡校的一位學生,名陳正詩。陳正詩是中共黨員,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前來會見李升伯。他向李分析形勢說:“由于時局的變化,‘中紡員工及誠孚紡校的同學們懇請先生能夠留在上海,繼續開展公司工作,并開展戰后的紡織事業復興工作。希望升伯先生能夠運用您的影響力,保護好‘中紡的工廠設備,迎接解放。”
李升伯認真聽著,思索了一下,說出自己的想法:“我明白你的意思,國民黨大勢已去,下一個步驟工作就是保護好‘中紡設備,迎接上海解放。此舉當然重要,因為‘中紡的那些設備與資產對于今后的國計民生會有直接影響。”他停了一下,繼續說,“不過,現在‘中紡各廠的紡織機器數量有限,且大多是日人留下的,難于滿足戰后和平建設時期的大規模發展需要。經緯紡機制造廠的同人以及誠孚紡校的師生都清楚,多年來我辛苦籌劃多年的紡織母機設備(制造紡織機的成套設備)已在美國訂購,這些機器能夠制造出大批紡織業急需的成套新型紡織機。如能將此套母機運回國內,國內紡織廠將更換新機,不僅老百姓的穿衣問題無須憂慮,而且,對于戰后國家的經濟復蘇,以及今后民族紡織業的開拓世界市場均頗多助益。我在杭州洽購了土地,廠房建造近期已經完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此成套機械設備在美國整裝待發。只是時局演變,時勢難料,聽說美國議院有動議,即將對華實行‘經濟封鎖。一旦此項議案通過,那套重型機械設備就可能被華府扣留凍結,前景難以預測……近日,我已急電在紐約的兩位代表,請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不惜任何代價,無論如何必須趕在兩周之內,將這批母機送上輪船,裝運回國。”
他看著陳正詩說道:“你知道,這批母機如被華府凍結,那么,不僅我為之奮斗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而且,今后國家的紡織事業也會倒退多年。因此,我必須要馬上趕往香港,指揮他們搶運母機回國……至于這里的情形,有這么多同事的努力,加上你的四處聯系,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陳正詩連連贊許。
不久,李升伯即赴香港。此時獲悉美國議會正在討論議案,即將對華實行貿易禁運的消息,他急電駐美代表,不惜一切代價,排除一切困難,趕在禁運前將在美國、瑞士訂購的紡織機械制造母機搶運到香港和菲律賓。
這些機器運抵香港后,除寄放在公共倉庫外,為防不測,他將一部分當時最尖端的巨型母機存放在永生、開源廠的廠房內。母機雖運到香港,但西方國家對華實行貿易禁運,仍不能運回國內。李升伯只得以自己的兩家廠——永生、開源廠為抵押,向銀行購買這批巨型紡織母機設備。
海外赤子,心系祖國紡織業
20世紀50年代初,紡織工業部派代表至香港與李升伯商洽這批母機,希望能運回內地,由國家將經緯紡織機械廠建成,完成他的畢生夙愿,并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李升伯聽后,一口同意,將價值連城之成套制造紡織母機設備全部無償交給國家。
那批紡織母機終于被裝運送達上海,杭州經緯紡機制造廠接到提貨單后,龔文千等人到上海提貨,以便運回杭州安裝。
根據當時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考慮,這批成套紡織母機放在沿海地區不安全,決定將它運至山西榆次,裝備新中國的第一家大規模紡織機器廠——山西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使它成為發展建國以后紡織工業的有力基礎(拱宸橋的經緯紡織機械廠上世紀50年代后更名為“浙江麻紡織廠”)。
不久,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派紡工部的孫友余到港,會見了李升伯。孫感激地說:“李先生為新中國的紡織事業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為,不知道我們能為先生做點什么?”
李升伯謙遜地說:“我現在衣食無憂,不需什么幫助。”
孫友余又說:“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國內工作,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蓄勢待發,正需要像李先生這樣的建設人才回來施展抱負。您如果回國工作的話,一定會有所作為的,回來后您的地位決不會低于原來的位置。”
李升伯想了想,說道:“現在香港正在開始發展工商業,紡織業剛起步,我的兩家廠——永生、開源廠還在籌措之中,百事紛雜,恐怕一時抽不出身來。等到這里的事務告一段落后,我一定會回來的。”他思索了一下,接著說,“不過,我有個女兒在內地工作,務請政府多多關照!”
當時李升伯的大女兒李佩貞夫婦及兩個兒子還在國外讀書,二女兒夫妻跟李升伯住在香港,內地只有三女兒李佩蕓一家,孫友余一口應承。
1952年,他的女兒李佩蕓到港探親,臨別時,似有戀戀不舍之情,李升伯一再說:“你回杭州安心工作好了,這里不用牽掛,我已經拜托過我的一位老朋友來照顧你們全家,他是共產黨員,在北京很有影響力,不會虧待你們的,你只要能常常回來看看我就行了。”
其實,李升伯為了搶救、購買及存放這批大型紡織母機設備,已欠下了巨額債務。上世紀50年代,由于此筆過于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他的永生廠與開源廠深受拖累,資金鏈斷裂,先后被迫停產倒閉。由此,李升伯攜眷移居美國,他在美國特拉華大學教書,作為一名助教,逐年用自己的有限薪水,歸還為購那批紡織母機所欠下的巨額債務,自己始終過著清貧的生活。此時,李升伯兩個正在美國大學讀書的兒子也是依靠自己勤工儉學完成學業的。此筆巨額債務直至20多年后的1972年才算最后厘清,李升伯時年已76歲高齡。而他所運回國的紡織機械設備裝備了山西榆次經緯紡織機器廠,形成了每年制造紡織機100萬錠的能力,為新中國創造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紡織工業,為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支柱產業,這批紡織母機對我國上世紀50—70年代的紡織機器制造與紡織工業及國計民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退休回國,為中國紡織業的強大出謀獻策
1978年,已82歲的李升伯先生退休后居住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寓,雖然年事已高,仍時時關心著祖國的變化。當他從電視上獲悉“四人幫”倒臺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消息,立即感受到祖國即將要進入全面的現代化經濟建設進程了。
有一次,他在電視中看到中新社的一則新聞,談及上世紀50年代初他將經緯紡機廠機器搶救回國的事情,以及那批機器后來對國家紡織業作出的貢獻,令他大感意外。
他沒有想到,事隔多年,政府仍記得他當年的所作所為,他也仿佛感受到,這則新聞報導的背后,或許有許多人對他的召喚。此時,他不由得老淚縱橫,當即寫信給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陳維稷,一方面對政府不忘舊情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談及自己因年老體弱,想念家鄉與內地的女兒,渴望回國定居,并說,后悔當初沒有聽從他的勸告回國工作。
陳維稷接到信后,立即通過中僑聯回信,歡迎李升伯回國參觀或定居。陳維稷(1902—1984),1902年10月15日生于安徽省青陽縣;1925年—1928年在英國利茲大學學習,后去德國實習;1930年回國后歷任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工專教授,南通學院教授、教務長,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紡織系主任。曾任重慶民治紡織廠工程師、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廠廠長、總工程師。20世紀30年代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主持出版《天下日報》和秘密刊物《起來》。193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從事過中共的地方組織建設工作和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1949年起至1982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20世紀50年代他主持全國紡織廠開展節約用棉運動,解決了當時國家紡織廠合理使用原料的問題。他曾領導國產棉紡織印染成套設備的研制工作和靜電紡紗等重大科研項目并取得顯著的成果。
在中央統戰部、中僑聯的安排下,1979年李升伯終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上海。
回國后,李升伯應中央政府紡織工業部、上海市政府邀請,擔任上海市紡織局技術顧問。他一方面為看到祖國紡織工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當年搶救回國的紡織母機仍在正常運轉而興奮不已;另一方面,又為國內大量紡織機械設備陳舊落后、勞動生產率低、產品原始、檔次低、質量差、附加值低與工業化發展進程極不相適應而擔憂。他向紡織工業部上書,提出發展我國紡織工業的策略。可以說,他的這些建言全部獲得中央有關部門的采納。
這些年來,在擔任紡織局顧問期間,李升伯先生盡職盡力,仔細研究分析了近代以來各國工業化發展規律,探討紡織工業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地位和作用,認為由于中國當前工業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所以,紡織工業在今后較長時期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內地人口眾多,需要紡織工業這樣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提供大量工作崗位。他除了工作、開會外,還到各紡織企業、大學視察和講學。同時,他撰文倡議國家今后應將發展服裝工業作為紡織業的主攻方向,提出要引進最新服裝制作設備、技術。他還不斷上書紡織工業部,建言在全國高等院校設立服裝專業等議題,全部得到政府高層重視與采納。
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杭州浙江絲綢工學院率先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服裝專業,之后服裝系科在全國大專院校中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他為提高紡織品的附加值作出了貢獻。
李升伯多次向有關部門及親友談起,自己從年青時就有移居西湖之想,并渴望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上虞驛亭看看。但是,鑒于當時“文革”動亂結束不久,國家百業待興,加上他事務繁忙,老弱多病,未能成行,終成憾事。1985年11月10日,李升伯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89歲。當時,中新社、《中國紡織報》、《解放日報》、《浙江日報》、香港《大公報》等媒體都作了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