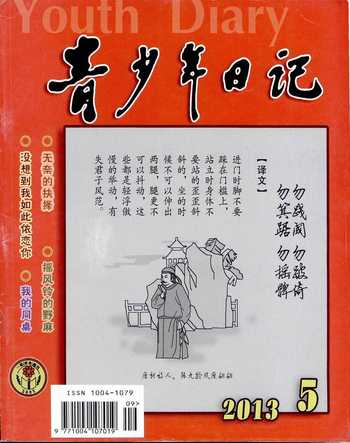記憶與超越
雪靜
2013年3月9日 晴
讀了近兩周的琦君散文,時(shí)至今日才整整看完。琦君文字平淡如水,若不是字里行間常有詩(shī)詞格律出現(xiàn),倒與小學(xué)生作文有幾分相似。文中僅是親情友情,那般樸實(shí)在如今層出不窮的出版物里已很少覓得見了。
于是想起了上周末與媽媽閑聊時(shí)她提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草木春秋》,文字也是極盡平淡,甚至讓人懷疑是故意要用大白話說故事的。
如此看來,寫作又是為了什么呢?遣詞造句固然是一種藝術(shù),把文章裝飾得頗具視覺美。唐詩(shī)宋詞善取對(duì)仗工整的格律,即便讀來似懂非懂,但看上去也是美的。
至于琦君和汪曾祺,我想這樣的寫作里記錄的成分更多一些。論文筆,這些文字或許連高中生也趕不上,但是一個(gè)作者寫得出故事,走得過春秋,經(jīng)歷本身的厚重性已經(jīng)不需要所謂的“文筆”來遮蓋了。這樣的樸實(shí)是鉛華褪盡,淡妝濃抹倒適得其反了。
自己一直較為喜愛的英倫才子王爾德便是唯美主義的忠誠(chéng)擁護(hù)者,在文字上要求極端的美感。按這標(biāo)準(zhǔn)套來,琦君這僅僅被感情潤(rùn)色的文章定是十分差勁的了。可我又為何要把兩位各具才情的作者框入同一個(gè)特定的格子中一決高下呢?寫作在于記錄,只要忠于真相,記錄是不分好壞的。
我常常想,每一個(gè)時(shí)代,或安定,或紛亂,總該是有一定個(gè)性的。寫作者是時(shí)代的撰稿人,若是背棄了時(shí)代,那這文字再好,也沒什么意義了。我們?nèi)缃褡x的,是上一個(gè)時(shí)代的記錄,上一個(gè)時(shí)代有魯迅有胡適,上一個(gè)時(shí)代再好,卻注定不是我們的。
那么我們的時(shí)代有什么呢?被無數(shù)人捧得高高在上的郭敬明,靠出版致富,我看那些文字,實(shí)在覺得只是小兒科的形容詞羅列。少男少女愛看“青春系列”——穿越古今,男男搞基,男女戀愛。文字成了讓人過癮的娛樂工具,因?yàn)榉凑@個(gè)時(shí)代本身就缺少嚴(yán)肅。
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節(jié)奏實(shí)在太快了。想要安靜地做一件事,慢慢地深入地研究,已是奢望。這樣的時(shí)代只好用夸張和娛樂來緩和眾人的緊張和急躁,你要求深刻嗎?對(duì)不起,先扔掉手機(jī)再說吧。
文字是要記錄一切的,這記錄不分優(yōu)和劣。所以,如今的文字再浮躁,也仍算得上忠誠(chéng),因?yàn)闀r(shí)代正是如此,不娛樂至死,就饑餓至死。
盡管如此,盡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并抱有半數(shù)的堅(jiān)信,總會(huì)有超越時(shí)代之上的文字。“超越”并非背棄,因?yàn)槟憧偟米屪约合嘈牛煦缰幸欢ㄓ腥吮Wo(hù)著那顆冷靜的心臟,只要理智不死,就永遠(yuǎn)跳動(dòng)不息。
山東青島市第58中學(xué)2011級(jí)(4)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