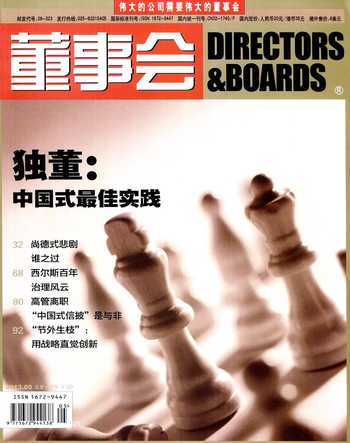央企負責人考核新規之惑
李南山

從國企改革歷程來看,國企業績考核的實踐反映了從“搞活企業”到“搞活國有經濟”再到“搞活國有資本”的改革過程。例如2013年修訂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聚焦如何增強經營者業績考核的科學性。但從歷史的維度來看,《新辦法》基本延續了原有的框架體制,仍需在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中持續推進和完善。
不同階段的國企改革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第一階段是1978-1992年,在搞活經營機制和“利改稅”改革中,政府對國企經營者采用產值、規模和利稅等指標的考核導向。第二階段是1993-2003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與之相應的財務會計制度,主要以實現利潤和凈資產收益等指標的考核導向,但政府主導考核呈現主體多元化和指標多層次性。第三階段是2003年至今,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努力探索出資人對央企發展的業績導向,2003年即訂立實施《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2006年進行了第一次修訂,2009年第二次修訂中引入了經濟增加值(EVA)指標,突出了股東價值增值在業績評價中的作用。經過兩年多實踐,2013年進行了第三次修訂,進一步完善以經濟增加值為核心的業績考核,引導央企實現生產經營穩定增長和提高發展質量。然而,圍繞國企業績考核,仍有三個方面有待進一步厘清。
考核定位:“目標管理”還是“委托代理”?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對國資國企改革的要求,經營者業績考核應放在國資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框架下,科學地設定出資人機構對所出資企業的發展導向機制。經營者考核權是股東(或出資人)的法定權利,應按照現代公司治理機構的委托代理關系,按照《公司法》的規范完善經營者業績考核制度,科學地建立國有資本經營責任的傳遞管道。《新辦法》對公司制國企從董事長一直考核到高級管理人員,沿襲了政府對國企領導干部實行目標管理的傳統方法,國資委行使了董事會的職權,實際上是擴張了自己的權限。雖然《新辦法》中也設定: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由“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業績進行考核”,但須經國資委 “授權”的規定也同樣露出了行政化舊制的痕跡。
考核分類:經濟增加值為主是否適合所有企業?經濟增加值為主導的經濟效益指標僅適應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國企分類是設定考核指標的主要依據。我國的國有企業數量大、類型多,準確分類是科學設定考核指標的前提,唯有準確分類才能建立有效的業績考核。國有企業從產業特質的分類,可區分為自然壟斷型、國防安全型、完全市場競爭型和國家發展戰略型等。《新辦法》采用經濟增加值為主的經濟效益指標,對競爭性類型的國企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確可以起到“金鞭子”的作用。但是,由于國有資本的兩重性,決定了現有相當部分的國企具有非競爭性、公益性和功能性的特點。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這些非競爭性類型的國企運行目標往往應以社會效益指標或國家利益的特定目標為主。《新辦法》中僅僅列示軍工和科研類為特殊企業,相應的業績考核指標則進行例外處理,顯然難以適應國有企業性質和運行目標的多樣性。況且,國資委管理的115家央企中的大集團,較多的兼有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產業特點,《新辦法》雖然已設定相關的例外處理規定,但過多的例外規定無疑會增大考核主體的自由裁量權和主觀隨意性,會軟化業績考核的制度約束力。同時,也會引發被考核主體諸多的“情況說明”、“補充匯報”等行為,以及以形形色色“走門路、找關系、說人情”的方式申請適用例外條款,甚至最終會導致業績考核“熱熱鬧鬧地走過場”。
考核方式:“軍令狀”還是“委托協議”?《新辦法》規定國企經營者業績效考核“實行年度考核與任期考核相結合”,年度經營業績考核和任期經營業績考核,采取“由國資委主任或者其授權代表與企業負責人簽訂經營業績責任書的方式進行”,并對責任書的主要內容予以列示;責任書中的業績考核指標以“報送——核定”的程序確定。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經營者業績考核采用簽訂責任書的方式,實際上反映了行政管理關系中下級以立“軍令狀”方式對上級表示完成既定任務的決心。而在現代企業制度中,股東(大)會與董事會、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應該是平等治理主體之間的委托協議和權利義務對等的契約關系。
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會議的精神,國資國企改革要堅持市場化的方向繼續深化。進一步完善國企經營者業績效考核,也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突破舊體制的羈絆。首先,在深化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中,出資人機構應按照《公司法》準確定位,對國企經營者的考核要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其次,在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中,要通過加強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建設,細化和優化法人治理的制度規范和運作水平;第三,要深化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制度的改革,提高國企經營者職業化、市場化的水平,真正做到“經營業績考核結果同激勵約束緊密結合”,培育大批具有市場化運行能力的優秀經營者,切實增強國有企業創新發展和持續發展的動力。
(作者系上海國有資本運營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