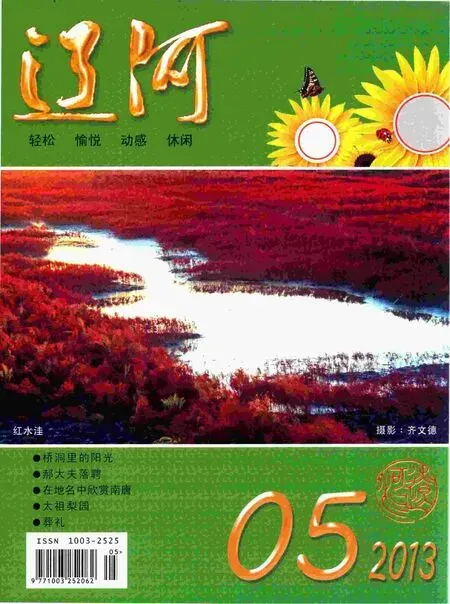村里那些樹
曲京溪
六月初十那天,我回家給母親燒三周年,卻怎么也找不到住在同村的三妹的家。原先三妹家門東的小巷里,有棵高大的槐樹,這棵槐樹就是我到三妹家的參照物,過春節時它還活得好好的。可如今小巷變成了水泥路,那棵槐樹也不見了蹤影。我們村的農房,是經統一規劃建設的,我無法找到三妹的家門,只得打電話讓三妹出門引路。三妹說:“甭說你了,一年回不來幾趟。就是王超(三妹的兒子)放假回來,沒有了那棵樹都找不著家了。”沒了一棵樹,兒子回家連家門都找不到了,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記憶中,老家的村子是被大樹掩映著的。只有在冬季,樹葉落光了的時候,才能看清農舍一排排整齊地排列著的模樣。其他時候,大樹就像母親,環抱著村子;農舍就像孩子,依偎在大樹母親的懷中。
我們村莊很大,在我小的時候,東西距離就有一華里還多,戶數近千。家家戶戶,門前栽樹,房后種樹,院子里還有樹。榆樹、槐樹植于門前,取“門前一棵槐,不是進寶就是招財”之意。如果槐、榆相抱,呈現纏繞生長的景象,那可是大富大貴的征兆,預示著戶主家不是要出達官貴人,就是出鄉賢名流,是要光宗耀祖的。房后一般栽些棗樹、香椿樹之類。院內栽的樹種,以農戶家庭的經濟條件和戶主的個人喜好而定,家庭條件好一點兒的,多栽杏樹、石榴、毛桃、蘋果等果樹,栽這些樹不但能賞花,而且在那個水果匱乏的年代,還能給老人、孩子解解饞。家庭經濟條件差一點兒的,院內一般種些白楊、梧桐什么的,長大后可當房梁、檁條蓋新房子用。梧桐板子曬干后,不易變形,還是娶媳婦、嫁閨女打家俱的好材料。記得我家門前有條排水溝,靠街的鄉親,就在自家門前的水溝邊上,栽上柳樹。村外的道路兩側,由大隊民兵和學校的學生,組織義務勞動,全部栽上了鉆天楊,高大挺拔的身軀,一直與鄰村的樹木相接。在我的記憶中,村里村外種花的極少,我小時候在村里,只見過地瓜花和光光花兩種花,覺得單調而乏味。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在那個連肚子都填不飽的年代,鄉親們哪有心思去觀花賞景呢?但樹木給人帶來的歡樂,就夠鄉親們享受一番的了。
當二月的春風,剪綠了柳樹枝條的時候,村子里便響起了孩子們的聲聲柳哨。三叔是做柳哨的高手,他通常剪下一截直而疤癤少的柳枝,捏緊枝條的一頭,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扭動樹皮,然后抽出其中的白色木條,再拿把小刀,將圓筒的兩端裁齊,削去一端的青皮,一個柳哨就做成了。圓筒粗的,吹起來聲音渾厚,細些的聲音高亢,懂些音律的,還能吹出好聽的旋律,引得女孩子羨慕不已。
夏天到了,清晨或黃昏,當炊煙升起的時候,煙靄在樹林里彌漫,根本分不清炊煙是從哪家升起的。人們下工回來,如同走進仙境一般。一場夏雨,澆開了知了尖尖的嗓門,從獨唱、重唱到大合唱,知了們唱醉了鄉村的夏季。中午,我們跟著大人去粘知了,通常是找一根向日葵桿子,上頭插一節直溜的條子,接頭處用麻繩勒緊;抓一小把黑面,加水和勻,再放嘴里嚼一嚼,就成了面筋,然后抹到條子的頂端。到樹下,小心翼翼地粘住知了如紗的薄翼,知了怎么蹦跶也甭想掙脫。掐下知了的雙翅,拿回家在咸菜甕里腌上幾個鐘頭,在大鐵鍋里焙熟,咬一口,滿嘴生香。入夜,我跟著哥哥去找知了猴,因當時我們家里還沒有手電,只能用手摸索著找,所以我們的收獲常常不多,如今想起都覺得有些遺憾。
那年月煤炭短缺,液化氣還沒有。多半農戶,一年里,總有那么幾個月缺糧少草的日子。清秋時節,風吹黃葉落,是我們拾草的好季節。天還沒明,我們就一骨碌爬起來,到溝邊灣沿,用小笤帚掃樹葉,有柳樹葉,槐樹葉,還有楊樹葉。那碗口大的白楊樹葉,是我們的最愛。因這種樹葉,不管是在樹上,還是在地面,風一吹,嘩啦嘩啦地響,我們叫它“嘩啦葉”。遇上刮大風,我們會起得更早。掃樹葉的人多了,我們就搶占地盤。掃的樹葉簍子裝不下,我們會到生產隊的場院邊上,扯幾根半干不濕的地瓜蔓子,一頭橫拴一節樹枝,一頭豎接一段細樹條,用來穿樹葉。那時候燒柴不足,我們拾的草,一年能補充一個家庭三四個月的缺口。
屋后那棵大棗樹,是我們的最愛。屋是百年老屋。棗樹就生長在老屋后面的夾道里。它枝繁葉茂,能遮擋半個屋頂。從棗樹揚花的時候,我就天天瞅著棗樹咽口水,盼望棗兒快快長大。等樹上掛滿了青果,每逢刮風下雨,我放學回家的頭一件事,就是打開后窗,爬進夾道,撿拾落在地上的青棗,也不用水洗,填進嘴里,就嘎嘣嘎嘣地吃起來,常常招來奶奶的一陣罵聲。打棗的日子,是我們孩子的節日,也是奶奶最開心的日子。秋深了,滿樹的棗葉泛了黃,那紅紅的棗兒壓彎了枝頭。清早,太陽還沒爬過屋頂,大哥就拿一根竹竿子,爬上樹杈,使勁兒敲打,棗兒就嘩嘩啦啦、噼噼啪啪,從天而降。我們小一點的孩子,就拿著瓢、搪瓷盆等物,在地上撿拾。這一棵棗樹,一年能結五六十斤,奶奶就放到天井里曬。待曬干了,奶奶拿個小一點兒的瓢,擺動著那雙小腳,給本村的親戚,左鄰右舍挨家送去,讓他們過年時蒸棗餑餑用。那棵棗樹,是奶奶一年的念想,也是她在人前能挺起腰桿的希望。
相對于人類來說,樹木的生命是卑微的,它們不能預知厄運什么時候降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建設連村路,村外的道路要拓寬,一棵棵十幾米高、兩人合抱粗的白楊樹被貼地皮鋸斷,庇護村人們幾十年的綠蔭長廊從此消失了,只留下長長的一行樹墩。我覺得一個個年輪清晰的樹墩,就像是樹們蓋在大地上的一枚枚印章,證明著它們在這個世界上有過輝煌的生命歷程。直到有一天這些樹墩腐爛了、消失了,它們的靈魂仍在大地里,萌動新的夢想。即使它們自己不能破土而出,也要托舉起新的生命。
前幾年,村里硬化主路時,那溝邊房后的樹木也一棵棵倒下了,有的倒在了推土機無情的鐵鏟下,有的倒在了鄉親們自己的手中。樹木無言,可人是有心的。
一棵樹倒下了,也許并不太可怕。可怕的倒是農村里的傳統和文化的消失。搞建筑的大外甥,聽說我回來了,找我又談起了招工的事。外甥在老家村里成立了建筑隊,專門蓋民房、廠房什么的。用的人員都是守家在地的鄉里鄉親,日工資,干大工的120元;小工90元。每當麥收、秋收時節還放農忙假。外甥為留住人員,工資是每月按時開的,逢年過節還得宴請他們吃喝。我問:“咱當地有那么多的建筑工匠,怎么非要舍近求遠招外地的呢?”他心情郁悶地說:“你說的都是以前的事兒了。如今瓦匠可成‘香餑餑了,搞建筑的爭工人爭得都快打破頭了。我的那些工人,工資全發了,還得年前登門送禮穩住心;年后再送禮拜年定下來。”“村里有那么多的年輕人,他們整天沒事兒干,怎么不學瓦匠呀?”外甥嘆了口氣:“嗨,現如今的小青年誰還樂意干這個呢!我用的70多個人,大工年齡最小的59了;最大的都72歲了。小工也沒有一個掉下60歲的來。現在都是機械化了,根本累不著人,一天90元,小青年寧可在街上閑逛,也不愿意干這個,真是沒辦法。”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想我年輕在生產隊干活的時候,要學個瓦匠那可真不容易,得生產隊長挑選優秀青年,還要安排師傅帶徒弟才行。要是真能出息把好手,不但可以吃到“百家飯”,而且娶媳婦還能挑著撿著地找。現在的年輕人這是怎么啦?眼下農村30歲以下的孩子,還有幾個會蓋屋打墻、會種莊稼的呢?要是再下去幾年工夫,農村還能有工匠嗎?恐怕連能分清小麥、玉米的年輕人也很少見了。對土地的不敬,對勞動的鄙視,就是對生活的不熱愛,這是自毀生命之根啊!
下午五點半,我們要去母親的墳上。頭上,太陽炙烤;腳下,水泥路滾燙。此時,我更加懷念村里的那些樹,就像是懷念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