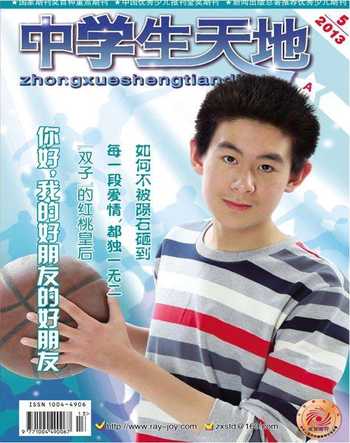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等3則
塞林 主持
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得過小兒麻痹癥,腿腳落下了殘疾。我雖然性格外向、愛笑,可下課時大多獨自坐在座位上看書、做作業(yè)。有時看到同學們在聊天、玩耍,我會突然感覺很失落。我想和他們一道開開心心地交流,但由于身體原因,只好遠遠看著他們。我該怎么加入他們呢?
孤獨玩偶
首先我對你這個名字有點小小的意見,你應該取一個更陽光一點的,為什么不呢?以“孤獨玩偶”自命會不斷給自己偏藍調(diào)的心理暗示,積極的名字會給自己帶來更正面的能量,就像你們大都喜歡的“治愈系”音樂一般。
你腿部的殘疾應該是比較輕微的,完全可以跟同學一起開心玩樂。我有一位大學同學跟你一樣得過小兒麻痹癥,腿腳略有不便,但一點不妨礙我們之間的各種交流互動,包括一起打羽毛球。他也許還是我們班上最陽光、笑容最多的同學之一。其實只要自己把心胸打開,沒有人會不樂意跟你一起玩。同學們沒有主動邀請你加入,是介意你的介意,在乎你的在乎,他們都是友善的。
我還是忍不住要引用殘疾作家史鐵生的一番話來開導你:其實每個人都是殘疾人,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缺,而任何一個人都在嘗試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大可以把自己心中有關殘疾的念頭放空,把所有顧慮都打消,以一顆赤子之心去面對世界和他人。在心理上把“殘疾”這個情結(jié)破除掉,你就是自由的,因為不再有芥蒂了,你就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人。詩人海子寫道:“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因為此心單純,因為此心澄明,因為“空故納萬境”。
同學介意你的介意,在乎你的在乎,他們只是無法判斷你是否介意和在乎。其實只要你走過去,參與進去,自然而然就是其中的一員。
讓“哀愁”變成一種“美”
我從前是個很開朗的人,現(xiàn)在依然是,但只不過是表面如此罷了。因為我喜歡的人離開了,我們不在一個學校了。現(xiàn)在我感覺沒有一個真心朋友能傾聽我的心里話,總喜歡晚上一個人躲在被窩里哭。我好像被困在一片沼澤地里,怎么都出不去……我很想回到過去……
北 北
雖然很多人喜歡嘲笑年輕的孩子“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作為也曾經(jīng)歷過那么一個階段的人,我知道青春期里那么一點未經(jīng)世事的離情、那么一點虛無縹緲的輕愁,是真實的,有時候也是頗難消受的。
記得剛上高一時的自己,每個周日傍晚離家到校后都倍感孤寂。我也描述不出那種心情,好像是傷感,又好像是空虛,總之覺得有什么東西在嚙著自己的心似的。我不像你那樣躲在被窩里哭,而是寫了許多渲染“離情別緒”的文字,跟你“很想回到過去”一樣,才十五六歲的我就自以為飽經(jīng)滄桑,就開始懷念、開始回憶了……文章因為情真意切,還屢屢得到老師的好評。那些文字當然是幼稚的、膚淺的(今天看來恐怕還是矯情的),雨過地皮濕罷了,但那樣的表達卻直抒了胸臆,消釋了塊壘。其實很快,我有了新的朋友,而功課上的事情也消耗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再多愁善感。
喜歡的同學不在一起了,新的友情未及建立,你在情感上可能會經(jīng)歷一個短暫的“頓挫期”。只要你不封閉自己,新的朋友很快就會出現(xiàn)。而如果你暫時無人可以傾訴,那就寫點什么吧,作文或者日記都行,寂寞時紙筆是很好的朋友,借助于表達你可以消除心中的惆悵。寫作的確可以升華情感。在文字所建構(gòu)的世界,情感不再會給你帶來壓力,連所謂的“哀愁”也變成了一種值得品味和珍藏的“美”。當然,你也可以讀一些格局大、志趣高的書籍,縈繞著你的小情小調(diào)會很快被驅(qū)散。
“墻角的花,你孤芳自賞時,世界便小了。”這是我中學時抄錄過的冰心的詩句,當時深以為然。你正處在準備看世界的階段,豈能把自己困于一隅,陷于“沼澤”?哪怕要有感傷,哪怕要有憂愁,也且等你把人生的風景好好領略了以后再加以細細咀嚼吧。不過,我想,置身于熱騰騰的校園的你,在讀到這封回信時,心里那點頗有形而上意味的“離騷”,恐怕早已煙消云散了。
人生的孤島上沒有成功
我有一個室友,我們很親密,經(jīng)常互相借東西。我參加學校的奧數(shù)班,她沒有。可她喜歡數(shù)學,就會跟我借卷子。每次借她的時候,我都是不情愿的。人總是有點私心的,怕她學得比我好之類的……討厭這樣的自己,很自私,可總?cè)滩蛔∵@樣……
木 吟
別太苛責自己,自私可以說是人性本身的一部分,有時候它與道德無關。有本名為《自私的基因》的書還從生物學角度來闡釋人的“自私有理”。
像你這種情況,心里有點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朋友之間有合作也有競爭。但是我希望你能把這點“不情愿”從心中滌除,畢竟它帶給你的是一種不愉快的情感體驗。你可以想,你借卷子給朋友,朋友可能會受益,你自己卻沒有受損。哪怕她學得比你好,你自己的絕對成績事實上并沒有降低一分。她因為得到你的幫助而提升了數(shù)學成績,你作為朋友應該也能從中分享到快樂。你們互幫互助,達到的是雙贏的效果。
我記得有位優(yōu)秀的班主任舉過一個例子,頗耐人尋味。班上有兩位學生發(fā)生了矛盾,一時無法勸和。她把兩位學生帶到一條窄道上,說:“一個要過來,一個要過去,怎么辦?”路實在太窄,大家側(cè)身仍無法通行。一籌莫展中她想出的辦法是:一位學生抱起另外一位學生,小心地轉(zhuǎn)身,雙方都成功通行。她說:“狹路相逢時,擁抱就是最好的辦法。”
如果你能這樣看待自己與朋友的關系,那么,借卷子給她時的“不情愿”就會渙然冰釋。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幫助她也便是幫助自己。在人生的孤島上沒有成功,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