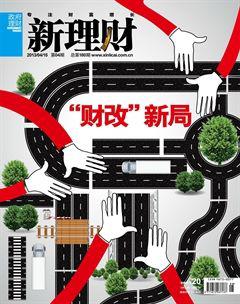變相專項
喬欣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地稅局局長王南健的真情感言,著實為如今我國分稅制改革的熱議又添了把火。
各有說辭
王南健直諫,“分稅制一定要完善。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為了完成不停加碼的任務和指標,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財政,增加收費項目,甚至是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財稅增幅指標。中央拿走的錢,用于專項轉移支付占了很大一部分,這個問題就更大了。這是‘跑部錢進的根源。而轉移多少,就看關系,關系好就多給點,不顧實際,結果造成很多浪費。”
他所說的這些,被業界普遍歸納為分稅制的若干宗“罪”。
不過有專家明確表示,在我國的分稅制中,中央并沒有多拿。“中央收入有2/3轉移支付下去了,這是有數據的。”
針對這個問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說,“對地方多征些,是為了調劑地區間的不平衡,這在理論上說是必要的,不過做法上存在待商榷之處,但這不是造成地方困難的根本原因。既然是轉移支付,就有給誰不給誰的問題,往往人為因素比較大,缺乏制度的約束和安排。現在也說盡量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減少專項,因為專項要貫徹一些具體的用途,但是各地情況非常復雜,不可能千篇一律,而且在實際的做法上,錢撥下去之后,亂挪亂用的情況非常普遍,達不到專項的目的。如果地方希望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把錢給夠,中央難以做到,那地方就進行權利尋租,而收費權和收費渠道的泛濫又導致整個分配狀況的混亂。”
記者所聯系的某地區縣級財政部門工作人員在介紹當地分稅制實施情況時說,“我們去年的財政收入上交了近2/3,這讓我們心里還是有些想法的。目前我們對下面鄉鎮進行調研后決定選取其中兩個推行分稅制,從實施情況看,他們比以前更有動力,畢竟收得多,干得多。”
專項緣何失效
圍繞引發諸多非議的轉移支付問題,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首席教授伏潤民說,“在西部很多地區,即便中央一分錢不收它們的,也依然滿足不了它們基本的支出。云南省現在已經上繳的錢沒有拿回來的多,它依然是困難的,其原因是支出膨脹,尤其是一些剛性支出、政策性支出不斷膨脹,同時財源減少、新的財源尚未形成。”
在2010年前后,伏潤民對云南全省縣級財力進行調查,“經調查地區縣級財政自由支配財政的能力不足12%,也就是說地方財政變成了一個類似計劃經濟的財政。原因在于,稅源的建設如農業稅、農特稅的取消使縣鄉財源減少,然而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去完成持續膨脹的剛性支出,例如津補貼提高、教育支出增長比例要求、行政執法的強制性高標準以及專項轉移支付的配套等等,因此,縣級預算變成了按照各種要求‘填空。我們幾次縣鄉財政困難,都是因為政策性導致,而不是分稅制導致。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發達地區上解中央財政的是多,這又涉及中央應該拿多少的問題,這取決中央財政應該掌控多大的調控能力,以及國民收入再分配要實現什么目標。”伏潤民說。
對于專項轉移支付是“跑部錢進”的根源一說。伏潤民坦誠,“專項轉移支付具有隨機性,‘跑部錢進就是講的這一塊。”
解決方法同時也是引發問題的原因。伏潤民分析,“按道理說,我國的專項轉移支付應該按照規范的程序進行,透明的公開論證、嚴格的過程監督和最后的績效評價,但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完整的監督機制和體系。
而且專項轉移支付對地方來說首先考慮的是怎么拿到這筆錢。同時專項還需地方做配套,但是如果配套要求超出了地方的基本能力,地方就不得不去借款,或者拿其他的財力充抵。”
這也是此前我們看到,縣級融資平臺遍地開花,其中超半數以上的貸款是投向公路與基礎設施建設。
伏潤民繼續說,“這筆專項的錢拿來之后沒有監督過程,尤其是如果當下沒有指定用途,或者雖然指定用途又沒有指定具體項目的話,這里面就可能出現很多問題,最終的結果就是這筆錢被補充到地方財力里去和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功能交叉而不是專款專用。既然是變相的財力性補助還不如直接拿來做財力性補助呢,讓地方政府拿這筆錢,根據他自己的需要來進行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講,提議減少專項轉移支付是對的。”
既然專項轉移支付的效用逐漸喪失,為什么依然長期存在并且一度呈現增長態勢?“因為專項分布在不同的部門,交通、農業、水利等等部門都需要專款,等于說各路諸侯都在向中央要錢,不分不行。可是給它們之后接下來進一步怎么分,都是各自按自己的思路。比如,衛生部門對鄉一級衛生機構進行補助來提升它們的水平,但是平均下來每一個鄉級衛生機構拿到的專款只有1000多元錢,客觀地自問,這筆錢能改善什么?農業、水利等等其他部門的專款也是這樣。除了大型項目固定之外,很多項目成了‘撒胡椒面,而且內部功能交叉、重復分散、沒有效力。因此,部門利益分割、準入條件、監督機制和績效評價沒有建立或者沒有嚴格執行造成專項轉移支付的種種問題,而造成專款失效的根源是事權劃分不清晰。”
財政部門也有著它的思量。某市財政局工作人員認為,“一般性的專項指標問題較多,應當少一些一般性的專項,多一些財力性的專項,或者多一些‘定向但不定項的指標,比如切塊給下級農村教育補助指標500萬元,由地方政府或者地方財政和教育部門共同安排用于農村教育方面的補助。”
構建地方稅體系
采訪中記者注意到,一位市級財政局工作人員介紹當地分稅制情況時,說到這樣的話,“由于我們省還是屬于增量上繳分成的體制,所以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他的話印證了此前有業內人士提出的“省以下實際上沒有形成真正的分稅制”。
省以下分稅制改革難在何處?浙江省財稅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余麗生分析,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級次多、缺乏主體稅種并且缺乏稅權。
他說,“省以下也推行了分稅制改革,但做法是各有千秋、參差不齊,有的地方實行的是將共享稅的地方部分再在省和市縣劃分的分稅制;有的地方實行的是總額分成的分稅制,等等。”
“十八大”提出了構建地方稅體系,“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孫鋼說,“怎么構建新型地方稅體系?稅種就這么多,那么就是怎么分的問題。我建議分享制能不能改成分征制,拿增值稅來說,變成中央增值稅和地方增值稅,比如中央征13%。地方征4%-5%,這樣一來,中央這13愿意減也好不減也好,那是中央的事。地方4也好5也好,收多少,對誰收,這是地方自己做主的事情。這樣有幾個稅種建立起來,能夠撐起一個地方稅體系,要不然就剩下些都是特別少的稅怎么稱它是體系?
按照這個思路,就需要中央和地方做到各征各的、各管各的,這樣就是比較徹底的分稅制了。如果中央在滿足自身支出時大大富余了,還要拿出一塊做轉移支付,從富裕地區調劑到欠發達地區。現在我們改說,理順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不講財權和事權,也就是這錢不一定是你征收上來的,上面給的也算。”
不過,伏潤民認為,“分享改分征解決不了徹底問題,徹底問題是在事權劃分的基礎上,把財權讓出去,地方稅體系才能真正建立。這就涉及到行政體制和財政體制的匹配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稅收體系。”
“縣級財政不同于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中央財政出現困難可以增稅或者發行國債,省級財政困難也可以向中央財政要求增加補助或向縣級財政要求提高上繳,而縣級財政困難是真正的困難,緩解困難的辦法和手段幾乎沒有回旋的余地。”余麗生說。對于如何構建地方稅體系,他建議提高共享稅的地方分成比例,也可以從地方稅中培養變為地方稅主體稅種。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小稅種的征收管理潛力是比較大的,如車船稅,隨著我國汽車從高消費品變為出行的工具,進入普通家庭,車船稅收入增長迅速,對地方財政的貢獻越來越大。又如土地使用稅,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土地使用稅收入的增長將越來越大,對地方財政的貢獻也越來越大。
還可以從費改稅中轉換為地方稅主體稅種。除了稅收之外,政府憑借行政權力向企業和個人收取有關費,包括政府性基金。政府的費收入由于缺乏法律約束,征收的難度大,而不少費收入是政府不可或缺的收入,有些地方政府費的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規模幾乎是相當的。對有一些收費改成收稅,即費改稅這是方向。如將社保基金改成社保稅,將排污費改成環境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