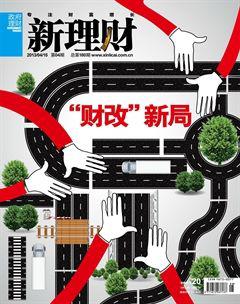癥結與解藥
馮興元
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仍然處于失衡狀態。總體上中央政府有著出臺收入劃分新方案的主導權,而地方政府窮于應付。隨著近年來收入管理技術和制度的日益完善(比如引入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土地出讓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等),富裕地區地方政府的博弈空間日益減少,較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獲得巨額的轉移支付,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當前中國的財政體制主要存在六大問題。一是稅費立法權高度集權。我國稅收的立法權高度集中在中央,收費的立法權高度集中在中央、省和一些較大的市,而且最終需要中央點頭,不能充分調動地方涵養稅源的積極性。而且稅收的立法權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決定”、“通知”、“條例”來制定和執行,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后兩者目前本身的人員結構也有問題。《預算法》甚至把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權一次性下放給了國務院,相當于一個公司的財權,從董事會移交給總經理。
二是我國在法律上并非分權國家,中央和地方迄今為止的所有財政安排和事權調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談判妥協的結果。中央政府由于擁有政治和行政上的權威地位,往往對事權和財權劃分方案有主要的動議權和決定權,因此事權和財權劃分缺乏內在的穩定性和法律保障。事實上,上級政府能夠比較隨心所欲地調整事權和財權分配,從而可將事權層層下放,財權逐步上收。地方政府則是通過討價還價、叫苦、申請項目、收取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土地出讓以及負債等形式來部分維護財權。
三是現行地方稅制體系不完善,地方稅制結構不合理,缺乏地方主體稅種。單個地方稅種的收入規模占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較小,導致地方自己的財源小且不穩,對預算外和制度外資金、土地財政和負債依賴程度較高。 實際上,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收入劃分方案中,共享稅部分規模過大。單單國內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證券交易印花稅合計占稅收收入總額的份額就達41%。共享稅占比越大,“分稅制”就越是名不副實。
四是在財政支出上,效率還很低。各級政府總體上重視收入,而忽視支出效率,還沒有建立透明的、有規則約束的公共財政預算體制,導致納稅人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之外作為第四權力部門的媒體不能有效監督政府的財政支出,納稅人交的稅也與其享受的公共服務不相匹配。
五是征稅管理成本過高。我國分國稅和地稅兩套征稅班子。這不僅增加了征收成本,也影響到納稅人的遵從成本,因為后者要面對兩套班子,而不是一套班子,而且這兩套班子之間還經常爭奪稅源。
六是專項轉移支付名目過多,不透明。轉移支出有個好處是可以控制地方政府,壞處是效率容易走低。轉移支付分兩種,一種是一般性轉移支付,另一種是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往往是比較透明,根據公式計算的,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資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據人頭標準就很容易算出。專項轉移支付是與許多中央部門掌握的專項資金相聯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的“跑部錢進”的影響。而我國恰恰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比較少,大量都是專項轉移支付。最近有了較多的調整,如果均不計稅收返還,2009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轉移支付(去除稅收返還額后為23678億元)的比重已達47.8%,專項轉移支付達52.2%。這里專項轉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規范性和隨意性,所以這么多年來存在上述一直被詬病的“跑部錢進”現象。在專項轉移支付里,現在的操作往往是成問題的。如果是2000萬的項目,地方政府一般要上報成5000萬或者更多,這是因為現在很多項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的,一些偏遠地方政府就很麻煩,沒有多少財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資金。考慮到中央會基于地方的討價還價,砍掉一部分預算,再加上要考慮打點費,也就是“尋租成本”,便在事先翻倍地報。
上述錯綜復雜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表明,我國需要加快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這里需要回答的問題首先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究竟如何真正明確劃分財權和事權。
在成熟的競爭性較強的聯邦制國家,比如美國,首先界分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然后按照輔助性原則來界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再按照各級政府自己的事權,來確定支出責任和支出需要,最終由此決定收入需要。而收入權的來源就是事權、支出權、支出需要,所有這些權力都是轄區內的公民賦予的,是在憲政框架內安排的。所謂輔助性原則指的是,凡是個人和市場能夠處置的事務,留由其自身去處置;政府的事權留由最低必要層次的政府去履行,上級政府提供輔助性的支持。而且,上級政府接手或者插手之前,還要考慮自身是否確實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實際上,各級轄區都是在法治框架內以自治管理方式提供本級公共產品與服務。本級轄區財力不足或者公共產品與服務本身有著一些外溢性等因素時,上級政府才有可能插手或者接手,包括轉移支付。但是,轉移支付額是有限度的,不能扭曲各地方轄區的治理積極性,損害一些發達轄區的稅收努力。
在稅制結構本身的改革上,地方政府必須要有自己穩定的財源,有著地方自己的主體稅種。比如依美國的經驗,三級政府財源支柱的概況是:個人所得稅和工薪稅(類似社會保障稅)歸聯邦(中央);銷售稅和公司所得稅歸州(相當于我國省級);財產稅主要歸地方(基層政府)。那么,我國在稅權歸屬上該如何劃分呢?我國是世界上政府層級最多的國家之一,有五個政府層級,包括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如果按照各級政府在法治框架內以轄區自治管理方式提供本級公共產品與服務,那么政府級次是幾級這一問題無關緊要,而各級政府有其征稅權至關重要。比如中央政府通過立法只確定中央一級自身收入的增值稅稅率,同時確定各級地方政府可加征的地方增值稅稅率范圍,各地具體加征的地方增值稅稅率(所謂加征率)由各地自行確定,這樣既允許一定范圍的轄區間稅收競爭,又保持總體稅制框架的完整性,各級地方政府均有法律上規定的獨立稅源,即便名稱都叫增值稅。其他共享稅種的改造也是一樣的。此外,財產稅即物業稅的引入也是必要的,它屬于地方稅,可以成為地方的主體稅種之一。但是財產稅的加征,必須以減少財產環節的其他征稅和收費以及其他環節的征稅收費為條件。因為我國的宏觀稅收負擔率非常高,各種政府財政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達到41.7%,2009年則膨脹至52.9%。這里的政府財政性收入包括政府的一般預算收入,基金收入、預算外收入、社保收入、土地出讓金收入、制度外收入、新增債務收入余額,還包括通貨膨脹率,它屬于通貨膨脹稅入的稅率。我國正在試點財產稅。財產稅也是讓地方納稅人增強納稅人意識、落實納稅人權利和義務的重要手段,它應該首先體現納稅人支付的稅價,以換取政府的公共產品與服務。但是它不應該首先是政府進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
我國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是需要行政體制改革的配套的。按照現有的較為嚴格的收入管理技術和制度,國稅和地稅兩套稅收征管班子完全可以合二為一地負責稅收征管。此外,根據上述的分析,各級地方政府應擁有法定征稅權,在法治框架內通過轄區自治管理的方式自主提供本級公共產品與服務,而上級政府仍然提供輔助性的支持作用。這種治道變革實際上不僅意味著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而且也是政府體制的變革。這也有助于我國構建一套轄制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穩定的規則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