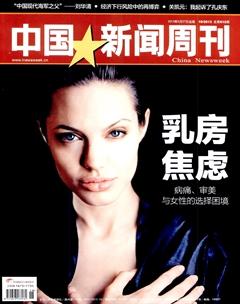扭曲的悲傷
克里斯托弗·利恩
(作者供職于美國西北大學,著有《害羞:正常行為如何變成一種疾病》一書)
人們需要多長時間去哀悼去世的親人?這個問題有點古怪甚至令人反感。從喪親遭遇中恢復,是個獨一無二的個人經歷過程。盡管有時需要幾個月才能走出悲傷,但形式各異,程度不同的悲痛,仍然是人們對失去親人的一種自然反應。
然而,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組織編寫的第五版《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對喪親之痛的理解,不認為喪親之痛是一種高度個人化、不可預見的經歷。新版《手冊》給精神病學專家和全科醫生提議,兩周時間的悲痛是比較合適的,此后,可能會被認為是抑郁癥。
換言之,14天后,大多數人還認為只是處于喪親之痛的初始階段時,醫生就應該能夠辨別出這種反應是正常反應,還是出現了精神紊亂的抑郁癥狀。有種說法是哀悼期應該迅速短暫且高效,這種說法既令人困擾,又實無必要。
此外,由于誤診可能性很高,定義“可接受的”痛苦,可能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嚴重后果。負責舊版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的艾倫·法蘭,在這一領域有著40年的經驗,他說自己難以區分正常的悲痛和兩周時間的輕度抑郁——而且“任何人都難以做到”。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初診醫生的反應。80%的抗抑郁藥物都中由他們開出來的,這會涉及很多病人。修改后的《手冊》將導致處方數量增加,因為診斷病人中,那些只是經歷短暫抑郁期但也有悲痛特點的人,其處方也將被囊括在內。
第五版《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的影響范圍遠遠超出美國,所以這個手冊一出來就在國際上引起了熱議。例如,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認為這個手冊有“過分簡化的危險”,充滿“瑕疵”,同時警示誤診事件會隨之大量發生。
更為復雜的是,該手冊的作用并不只是局限在健康醫療體系內。學校、法庭和監獄都會用到這份手冊,目的是確認精神病治療是否必要,而且能否報銷。
早期版本的《手冊》很謹慎,沒有把悲痛列為抑郁癥診斷的范圍內,因為悲痛和抑郁都能引起失眠,沒有胃口,精神萎靡不振以及心緒緊張——兩者極易混淆。而且,如紐約大學的杰羅姆·韋克菲爾德教授所言,當人們處于“婚姻破裂,愛情背叛,失業,財務困境,自然災難以及可怕的醫療診斷”事件中時,“類似的悲傷之情”也會出現。
對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宣稱新版手冊是基于科學依據的說法,韋克菲爾德表示強烈懷疑。他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邁克爾·B.福斯特教授都指出,“新的《手冊》應縮小臨床抑郁的分類,而不是相反。”
盡管反對聲很高,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仍然堅持對抑郁癥標準的修改,他們只是在手冊中添加了一個補充說明,授予主治醫師在兩周之后進行抑郁癥診斷的選擇權。顯然,精神病學協會認為誤診率是極小的。第五版《手冊》修訂小組主席大衛·庫普弗說,精確的診斷是基于“扎實準確的臨床判斷”。
然而,這已經不是精神病學協會阻礙診斷的第一個案例了。1994年發行的第四版《手冊》中,社交恐懼癥的判定標準被極大的降低,導致該組織不得不警告執業醫師不要將其與正常的害羞混淆。
盡管如此,之前少見的“悲傷”成了經濟被提及的話題。就連“預期恐懼”也成了診斷標準。所謂“預期恐懼”,是指人們可能會做一些丟臉和尷尬的事。新版《手冊》稱新增的“兒童悲傷”癥狀包括一些常見的兒童期行為,如“粘人”“怕冷”“畏縮”,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紊亂癥患病率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無論是協會還是其支持者都沒從中吸取教訓。即使已經做出讓步,稱“14天的時間來進行確診有點太短”,但《精神病學時報》前任編輯羅納德W.皮斯仍然堅持“在忽略抑郁癥狀發生的‘背景下,這是對的”。
這些影響巨大且難以逆轉的類似的決定,導致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宣布減少對新版手冊的支持,這個研究所曾經注入大量資金支持精神病學協會。研究所主任托馬斯R.英索爾援引《手冊》第五版中的話“缺乏有效性”,認為其“診斷依據的是一大堆臨床癥狀的一致性,而非客觀實驗的測量”。
今天,這種一致性在消失(其是否真實存在也值得懷疑)。在未來,人們也許有可能不再依據“生物指標”來判定抑郁癥,但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卻在增加籌碼,這給處于喪親之痛的人們增加了暗示——兩周后,悲痛就會變質。最終,哀痛也可演變成一種疾病。
譯/儀修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