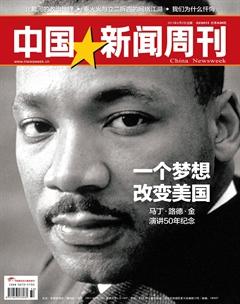解決地方債危機應硬化預算約束
馬駿
最近,國務院展開了新一輪地方債的大規模審計。
地方債問題的討論中,許多人最大擔心就是地方政府面臨的是軟預算約束,認為這種軟預算約束在目前的體制下是無法改變的。實際上,通過允許若干違約事件、建立用腳投票機制、立法、加強地方人大監督、建立預警體系等手段,是可以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
在美國,聯邦政府曾經多次接手州政府的債務,但是在19世紀30年代末大批州政府再次陷入債務償付危機的時候,聯邦政府選擇了不予救助。此舉使得那些財政困難的州政府不得不勒緊腰帶,但是最終都逐步擺脫困境并重新得到市場的認可。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后直到今日,聯邦政府再也沒有需要出手為任何一個州的債務違約而買單,地方政府債務也沒有再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系統性風險的來源。
即使在中國,也有硬化軟預算約束的成功案例。比如1998年的廣國投的違約案。廣國投事件之前,所有人(包括外資投資者)都假設政府不會讓其違約,當時對是否政府應該出手援救廣國投也確實有極大爭議,但最后下了決心,宣布廣國投破產。此后,其他信托公司的融資金成本飆升,高風險的信托公司和業務逐步萎縮,避免了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金融市場機制幫助硬化預算約束的另外一個例子是國有企業上市后的改變。20年前,非上市的國有企業普遍面臨著嚴重的軟預算約束。但是,上市后的國有企業,引入了新的股東,并根據上市法規必須定期向公眾披露詳細的財務報表。與20年以前相比,這些上市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得到了明顯的硬化(雖然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在這個改革的過程中,資本市場用腳投票(拋售不負責任的企業的股票)、媒體的壓力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與此類似,如果引入市政債,則債券市場用腳投票、要求披露地方財政數據的壓力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機制。
過去十年,全國人大對中央財政預算的約束力有所增強,中央財政透明度有所提高,表明通過提高地方人大的監督能力來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并非天方夜譚。由于全國人大的作用,中央財政明顯感覺到無法隨意擴大赤字,近年來中央財政預算的公開和詳細程度也有較大提高。另外,包括網絡媒體在內的媒體人、學者通過輿論對財政的監督也開始產生作用。這些機制完全可能在地方層面建立一定程度的對地方政府的約束。
通過立法(規定市政債的余額的上限和用途,要求地方政府公布資產負債表等、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等)、強化信息披露(通過加強評級公司的作用)、建立預警體系(如省級政府提前對下級政府發出風險警示)、加強審計等手段,也能從不同的方面加強對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
因此,由財政部對地方政府的風險指標進行詳細分析,選擇一批(開始選十幾個,五年內逐步擴大到近百個城市)償債能力達到標準的城市,允許發行市政債。市政債可以包括由財政收入支持的債券,和由項目收益支持的債券兩種。
立法規定地方政府債務的上限,比如債務占當地GDP的比例不得超過50%,利息支出不得超過經常性收入的一定比例。規定地方政府發債所籌得的資金必須用于資本性項目,不得用于經常性支出。地方政府的經常性預算必須平衡。
然后通過立法,明確宣示中央政府對市政債的償還不承擔責任。在實際運行中(比如五年內),應該允許若干基本沒有系統性風險的中小規模的市政債違約事件發生,以建立中央承諾不擔保的可信度,從而打消債券市場對“隱形擔保”的預期,使得地方債市場的定價(利率)能準確地反映這些地方的債務風險。
對部分有系統性風險的大城市違約案例,應該采用在中央或省級政府支持下的債務重組方式(如中央或省級政府給予部分救助,但絕對不能全盤接收債務,以免加大道德風險),降低違約對投資者的損失和風險在金融市場上的傳導范圍。但是,涉事官員必須承擔最大責任。地方首長免職、市政府重新組閣、地方政府開支大量削減必須成為上級政府幫助重組債務的條件。
省級政府可以考慮借鑒美國俄亥俄州的經驗建立對下級地方政府違約的預警體系。這個預警體系可用來對已經發行市政債的地方政府的信用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如果超出一定風險底限,省級政府就給予警告,通過警告來影響這個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和融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