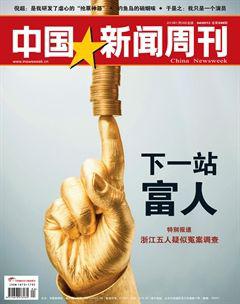《萬箭穿心》:口碑電影 票房炮灰
萬佳歡 劉炎迅

“恨不得七條路八條路都從你屋里樓下扎過去,各個方向都有。風水上這叫萬箭穿心!”聽完閨蜜這一番話,剛死了丈夫的李寶莉把眼一瞪,“我就不信這個邪我越是要說這是萬丈光芒,我不得叫我家散了。”
電影《萬箭穿心》的英文名是“Fengshui(風水)”,但其中講述的悲劇故事實際上跟風水沒多大關系。
女主角李寶莉出身底層,潑辣、霸道,與家里人無法溝通,在丈夫出軌時采取的極端做法逼得丈夫跳江自殺。此后,她挑了十年“扁擔”供養兒子和婆婆試圖“還債”,最終卻仍然無法獲得兒子的諒解。
這樣一個全武漢方言、改編自湖北作家方方同名小說的電影獲得了極好口碑。豆瓣給出了8.5分的評價,僅次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萬箭穿心》進入院線的時間僅為兩周,每日只有寥寥幾場,最后在《少年派》和《一九四二》的熱烈討論中悄然下線,在《泰》豪取12億的同時,拿走了可憐巴巴的300萬,成為又一個好口碑的票房“炮灰”電影。
“現實主義血脈”
即便發行方事先叮囑主創不要提及影片的“文藝”和“低成本”,觀眾還是能嗅出《萬箭穿心》里的文藝味兒:沒有大明星,情節反高潮,除去幾個高樓俯拍鏡頭,影片幾乎全部使用肩扛攝影。那些搖搖晃晃、看似隨意的運動鏡頭將故事里的市井氣一遍遍強調。“從生活來”“接地氣”正是影片監制、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謝飛最早對小說的印象。
在謝飛看來,中國電影最優秀的傳統就是現實主義,它是一種需要延續的“血脈”。從上世紀初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到1980年代的《老井》《本命年》,許多國產好電影都做到了既貼近現實,又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
而最近十幾年來,主流國產電影越來越娛樂化、鬧劇化,“這真把中國電影整個毀掉了,”謝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這兩年,他開始有意識地尋找一些現實題材小說,將它們改編成低成本電影。《萬箭穿心》就是個成果。
2010年,《萬箭穿心》的電影創作啟動,第一稿劇本并不盡如人意,項目暫時擱置。第二年年初,謝飛找到當時的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副主任王競,希望他出任導演。
王競曾執導過表現“人肉搜索”的《無形殺》和關注假藥的《我是植物人》等電影,一直沒跟現實題材斷過聯系。
在重新創作劇本時,王競與編劇吳楠一致認為,第一稿劇本對小說“吃得不是特別深”,且“有點偏商業”。
“不管是題材還是演員、投資,都注定了《萬箭穿心》不太可能做成傳統意義上的商業片,”王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的做法是,把故事的聚焦點回歸到人物身上,讓情節跟著人物走,這得到了一致認同。
影片最后采用了跟原小說幾乎一致的時間順敘方式,更重要的是去掉了原小說對女主角苦情奉獻的憐憫和“宿命感”渲染,努力在她性格里尋找造成悲劇的原因。
“文化砸車”
現實題材影片市場難做,審查難過。王競覺得《萬箭穿心》的審查還算順利,“只改了一兩處小地方”。比如女主角李寶莉向襪子店老板告假,老板說,又請假?都像你這樣,天下還不亂套了?李寶莉原本回答:“我要是能把天下搞亂,早就不在你這里混飯了,800年前我就進中央了!”王競覺得最后一句話的思維邏輯“特別李寶莉”,但審查后,做了修改。
但走向市場的時候,這部電影還是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動靜。2012年10月,剛剛接手《萬箭穿心》發行的董文潔以郵件形式要求影片退出東京國際電影節,原因是“日本政府右翼分子發動釣魚島挑釁事件”。
此事立即遭到了監制謝飛的反對。他發表聲明,表示這“完全是為了商業炒作”,是個“文化砸車”式的過激行動,“于理于法都不可取”。雙方發生了極大的沖突。
“東京退賽引發的沖突和當時大家對市場的判斷與不同觀念有關系,” 王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家的出發點其實都是希望影片的市場更好。” 謝飛認為,《萬箭穿心》就是個文藝片,怎么折騰也就幾百萬票房,而發行方覺得“要沖一沖、拼一拼”。
退賽舉動博得了民族主義者的眼球,但引發了一些文藝片受眾的反感,一些網友甚至還沒看過影片就因此打出低分。
風波后,發行方決定提前上映影片,2012年11月16日《萬箭穿心》匆匆上映,除了電影頻道舉辦的一個首映典禮外,幾乎再無宣傳活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片名有些“尖銳”,上映期間不太方便發硬廣告。
事實上,從第一稿劇本的論證會開始,就有人提出,片名“一定一定要改”。但想了其他一些片名,都覺得不夠犀利也不合適。
與《萬箭穿心》同檔期的影片包括香港動作片《寒戰》、美國動畫片《無敵破壞王》《守護者聯盟》及伊朗影片《一次別離》,后又遭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一九四二》。票房結果可想而知。兩周后,《萬箭穿心》悄然下線。在它下檔很長時間后,王競竟然還能在公交車身上看到影片的廣告。
“這種片子就是這種命運”
與發行方不同,謝飛把《萬箭穿心》的市場前景想得很清楚。他的目標是爭取做到“小盈利”。作為監制,謝飛嚴格地把影片成本控制在400萬以下,“能進影院就進,不進影院也可以。”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為此,《萬箭穿心》在劇本創作初期就開始與電影頻道合作。最后電影頻道對該片電視和網絡播出的回收費用達到200萬,成為《萬箭穿心》的第一出品方,片方也借此收回了一半以上的投資。
王競承認,謝飛對市場的判斷還是對的。《萬箭穿心》最后的票房與同期上映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次別離》差不多,“《一次別離》這么好的片子也是這樣,這種片子就是這種命運,”王競說,“觀眾都是特定的,不太可能產生隨機的觀眾。”
他認為,只有當特定的觀影渠道、特定的觀眾群形成,文藝片才算擁有真正的生存市場。而這二者有賴于電影市場的整體成熟。“中國目前已有13000多塊熒幕,再增加影院就會飽和,那時會產生一個拐點,影院必然會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拓展分眾市場。”王競說。
王競回憶起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舉過的一個例子:電影學院一個學生移民香港,發現樓下有個15座的電影廳,便把它包下來,又從日本買來電影《情書》,就這一部片子在那里放了整整一年,掙了18萬港幣。
有了這樣的影院,就會培育起固定的觀眾群。電影市場相對成熟的韓國就有很細的市場人群:上午10點或下午2點,一批家庭婦女收拾完屋子,會相約去社區影院看電影。她們絕不會看一個類似“007”的大片,更多地會挑一個家庭倫理片,有時候看完還能相互聊聊。
“這樣的市場發展可能真的得靠時間,”王競說,“《萬箭穿心》的發行方就是想這么去試一次,有操作、技術上的問題,有時機的問題,但確實市場也有這個勢,目前這個趨勢還是改變不了。”
在這樣的趨勢下,出品方電影頻道的投資似乎成為了一根救命稻草。然而問題還是無法徹底解決。經過影院里默默無聞的短暫上映,1月17日《萬箭穿心》終于在電影頻道播出,可當天播出的影片比電影版短了十幾分鐘,而且改成了普通話版本,因為“方言會影響收視率”。
影片結尾也有所區別:電影版里女主角的兒子更“絕情”,而電視版中,兒子在最后對母親產生了一絲悔意。王競很慶幸自己在拍攝時多拍了兒子悔過的鏡頭作為“備手”,因為電影頻道在劇本階段就對此十分堅持。“他們(電影頻道)大概是覺得進入家庭的東西還是要多一些溫暖和希望。”王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