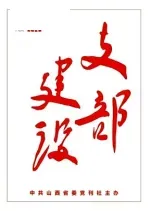石碾和石磨
■王寶亮
曾經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石碾和石磨,被遺忘在村莊的角落已塵封多年了。想起故鄉過去的一些人和事,總有許多與石碾石磨相連相扯的情節,歡樂掩蓋著苦澀。我走過它們運轉的圓圈道,刻進心里的是一幅有強烈動感的生命之畫!
當年的石碾是村民共有的碾米工具。村里每個生產隊都有碾房,石碾在我眼里仿佛就是一尊碾神,碾房則像一座神圣的殿堂。碾房的門不上鎖,誰家想碾米了,就牽上隊里的一頭驢或騾子,套在碾桿上,人、畜、石碾共唱一段碾米曲。我家碾米是隔幾個月碾一次,母親是碾米師,我當助手。記憶中的碾磙子很大很重,碾米效率很高,碾出的米金黃金黃,米粒完整無損。碾磙子上方懸著大木漏斗,我每次都是站在碾磙邊踮著腳很費力地將谷投進高高的大木斗。母親拉開木斗的漏口,谷便往下漏。漏口的大小由一塊橫插的小木板控制,母親根據碾磙子的轉速,定好谷的流量。騾子拉碾走得快,漏口須拉得稍大些。拉碾的牲畜戴著眼罩和捂嘴套,拉碾子很少偷懶。母親手里拿一把笤帚,跟在拉碾的牲畜后邊,將碾出碾盤的谷往里掃著,并觀察著出米的程度。米既要徹底去皮,又不能碾得過度,碾至米粒光亮為好。碾過幾次米后,我記熟了母親的動作,后來在碾道里走的,就多是我和牲畜了。最后母親用簸箕簸去谷糠,碾米曲緩緩而止。
還有一種石碾人們叫小碾,碾磙子略小,無漏斗,安在較寬敞的土窯口,也有露天的。人們碾少量的米,就在小碾子上人拉著碾桿轉,僅圖方便而已。
石磨也分大磨、小磨兩種,屬農家私有財物。很早以前,村里人買不起大石磨,一般人家只有小石磨,全家人吃的面都在小石磨上解決。男人在外勞作,家中磨面的活由女人承擔。母親當年磨面多在做完其他家務活后,利用晚上的時間,抓著小石磨的朝天木柄搖著轉著,左手困了倒右手,一搖就是多半夜,且日日如此。后來有了大石磨,我和母親合力推,磨面效率提高了,母親的負擔減輕了。大石磨的上扇側面有相對的兩孔,安著短木柄,套上繩套用木棍就可推著石磨轉。上世紀70年代初,村里有大石磨的戶增多了,而我家還沒有,磨面時就在鄰居家借用大石磨。磨轉著,我們不停地用力推著走著。我看著玉米粒紛紛從磨眼進了石磨的肚子里,它們被粉碎后變成面從兩扇石磨的合縫中像下雪一樣落在磨盤上,而我的腳已把磨道踩得光溜溜黑亮黑亮。小時候吃慣了石磨磨出的面做的窩頭,總是那么香甜可口。后來我明白石磨不破損糧食營養成分,特別是頭羅面,因含糧食籽粒的胚芽營養,質量最佳。
石碾和石磨見證了一個村莊的百年歷史,見證了山村百姓的艱辛和堅強。——想起當年石碾碾出的米、石磨磨出的面,心中一股溫暖流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