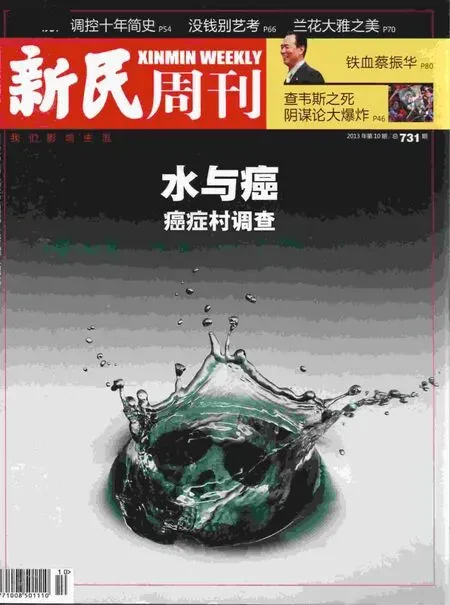歐洲治水史
樂悠

不管是興起工業革命的歐洲大陸,還是產業發展蓬勃的美國,都曾經歷過“母親河”瀕死的陣痛,或嘗過地下水污染帶來的澀果。也往往是在苦過之后,才有了更加迫切的心,要恢復那一片清冽甘甜。
瀕死的泰晤士河
英國19世紀的政治家約翰·伯恩斯曾說:“泰晤士河是一部流動的歷史。”中世紀起,泰晤士河就是著名的鮭魚產地,因此,皇室貴族、國王王后,或是具有相當權力象征的大主教,都在泰晤士河兩岸興建官邸、皇宮、行宮、大型修道院、僧院,就連許多中下層人民也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園。
這條英國的母親河,千百年來默默流淌,承載著倫敦的落寞與繁華。然而,恰恰是伯恩斯贊美泰晤士河富有人文歷史底蘊的那段年代,這條河流卻日益失去生機。
泰晤士河的“病”早有征兆。公元17世紀,倫敦市的供、排水系統就已經跟不上城市發展的速度,這一問題到了18 世紀工業革命時期顯得更為突出。隨著城市人口激增——1805年,倫敦常住居民達到100萬——泰晤士河一方面繼續向倫敦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也成了傾泄糞便和生活垃圾的場所,許多居民的生活垃圾直接沖進排水明溝,未經處理就進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漸漸變臭,天氣越熱,味道越大。
有資料記載,1800年,漁民還能從泰晤士河捕到龍螯蝦和鮭魚,倫敦魚市上仍能見到產自泰晤士河的鮭魚。但在后半個世紀里,河兩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工廠林立,污水橫流,越來越骯臟的泰晤士河終于引發了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這條河里停止繁殖生命,反而開始孕育霍亂。19世紀,泰晤士河流域發生了五次霍亂大流行,在1849年疫情高峰期 ,平均每周有2000名倫敦人被奪去生命。此時,倫敦城的醫生幡然省悟:原來傳播霍亂的元兇并非他們所以為的“空中飄浮著的臭烘烘的蒸汽”,而是身邊這條從1833年開始就見不到鮭魚的泰晤士河。
英國首次吹響治理泰晤士河的號角是在1852年,議會通過的《都市水務管理法案》規定,取自泰晤士河的飲用水必須經過沙濾處理;為保證飲用水不受污染,所有取水口必須建在遠離污水排放口的泰丁頓河閘以上。
1854年,負責泰晤士河排污管理的機構“都市工程委員會”設計出一套“中途攔截”的排污系統。具體想法是:修建一套巨大的污水采集系統,把全倫敦的污水引到城市東部,在那里集中儲存9個小時,再趁泰晤士河退潮統一排放入海。
1858年6 月,倫敦大街小巷彌漫著泰晤士河散發出的陣陣惡臭,熏得英國議會無法正常辦公,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不得不通過增加稅收的手段加快實施這套計劃。1874年,該計劃全部完成,倫敦修建了城市排水系統與泵站,但沒有從根本上清理泰晤士河的污濁。
又見鮭魚
20世紀初,英國人開始反思治理不力的關鍵:技術沒問題,但是管理方法有誤。泰晤士河沿岸大小供、排水公司百多家,多為私人所有,管理分散,如果對水資源的凈化處理系統進行有機整合,統一管理,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政府首先把水處理的權力收歸國家,其次通過立法對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作了嚴格的規定,且明確各級水務管理的管轄范圍和權限。有關當局還重建和延長了倫敦下水道,1932年—1938年修建了活性污泥法污水處理廠,1936年—1955年修建了190余座污水處理廠,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污水處理系統。
1974年,政府將泰晤士河流域的200多個管水單位合并成一個新水務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務管理局,再把全河劃分成10個區域,每家分局明確管轄一段河道,全面負責該流域內供水、防洪、治污以及廢水處理。這項大膽的體制改革和科學管理,被歐洲稱為“水工業管理體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從上世紀70年代起,泰晤士河開始重新找回清白:鱸魚、鰈魚等絕跡多年的魚類回來了,就連對水質非常挑剔的鮭魚也重新出現。1976年以后,100余種魚類重返泰晤士河。
1983年8月31日,一個名叫拉塞爾·多伊格的釣魚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報》的版面:他手里舉著一條重達6 磅的鮭魚,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英國泰晤士河水管理局特此給他頒發了一只銀杯和一張190英鎊的支票。英國媒體紛紛報道說,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復生了。
民間組織治理萊茵河
在歐洲大陸,還有一本值得稱道的“治河經”——國際河流萊茵河。
萊茵河全長1300多公里,流經瑞士、德國、法國、盧森堡、荷蘭等9個歐洲國家,是以上幾個國家的重要飲用水源,流經之處,也是歐洲著名的工農業走廊,城市分布密集。
上世紀50年代,由于工業、農業和生活污水長期不受限制地排到河里,萊茵河的水質幾乎讓人絕望:魚蝦基本絕跡,鷗鳥不見蹤影,沿岸放牧的牲口出現怪病,土豆里被檢測出含砷。沿岸國家意識到,必須打破之前各行其事、各自開發的做法,成立國家間常設性決策機構,形成合力治理萊茵河。
1950年6月,“萊茵河國際保護委員會”(ICPR)應運而生。1963年,萊茵河流域各國與歐共體代表,在ICPR范圍內簽訂了合作公約,奠定了共同治理萊茵河的合作基礎。
為減少萊茵河的淤泥污染,ICPR嚴格控制工業、農業、生活固體污染物排入萊茵河,違者罰款,罰金50萬歐元以上。保護委員會還實行“責任到戶”,如委員會下面設置若干個專門工作組,分別負責水質監測、恢復重建萊茵河流域生態系統以及監控污染源等工作,如:拆除不合理的航行、灌溉及防洪工程,拆掉水泥護坡,以草木綠化河岸,對部分改彎取直的人工河段重新恢復其自然河道等。
1986年11月,瑞士的桑多茲化工廠發生火災,消防隊員的高壓水槍把工廠儲存的大量農藥和殺蟲劑沖進萊茵河。這場生態災難讓沿岸國家意識到,僅僅控制住污水排放還不夠,應該對沿岸工廠布局采取更為嚴厲的限制。1987年,ICPR通過《萊茵河行動計劃》,決定以1995年為限,將兩岸化工廠等 重污染企業數量縮減一半。
正是這樣一個工作人員僅12人、既沒有行政管轄權也沒有強制權的民間組織,卻讓萊茵河重煥青春。上世紀90年代在萊茵河里中又出現了標志性魚類——大馬哈魚的蹤影。2002年年底調查表明,萊茵河已經恢復到二戰前的生物多樣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