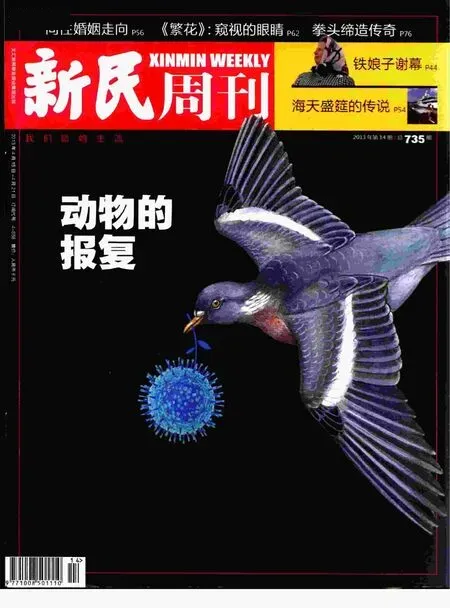心念唐音
王悅陽

王心心有著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zhì),然而,她又是很具有可塑性的。
當(dāng)“潯陽江頭夜送客”的絲弦響起,懷抱琵琶的她是白居易的江畔知音,而隨著陣陣胡笳悲鳴,她則又成了和番出塞的王昭君……
更多的時候,她身著繡花袍子,珍珠白、藕色粉、青瓷綠、湖水藍(lán)……襯著消瘦的臉龐,眉眼間善良、慈悲,不善言辭,總是用手撫摸著她心愛的琵琶、弦管。若說她像民國女子,到底還是俗了。她的美,很難形容。
王心心出生在福建農(nóng)村一個很普通的家庭,在她的記憶里,小時候是點著油燈、借著月光唱南管。還曾經(jīng)跟著宣傳大篷車,用南管演唱,宣傳計劃生育好。在讀書時,文科不好,常因背不出書而苦惱的她,卻因?qū)⒈痴b的內(nèi)容串聯(lián)成南音演唱,而第一次考到了滿分。學(xué)過女紅,考過大學(xué),最終,王心心宿命般地從事起了南音藝術(shù)。
南音演唱演奏,技巧高難。然而真正優(yōu)秀的南音藝術(shù)家,僅需一人一檀板,輕敲慢打,伴著弦樂聲聲,就令人感到真如聆仙樂一般,余音繞梁,綿綿不絕。從小熱愛南管的王心心,出道伊始就贏得了“坐遍五張金交椅”的美譽——指的是琵琶、三弦、二弦、洞簫與演唱全能。
而觀眾們認(rèn)識她、熟悉她、喜歡她,可能是從她去了臺灣之后。在那段歲月里,先是參與“漢唐樂府”,后來又組建了屬于自己的“心心南管樂坊”,從以南管吟唱的唐詩《靜夜思》開始,到對傳統(tǒng)曲目諸如《昭君出塞》、《陳三五娘》等的精心演繹,以及多年來嘗試的跨界合作——民樂、交響樂、昆曲、現(xiàn)代舞、布袋戲……王心心把古老滄桑的南音,帶到很多領(lǐng)域,走得很遠(yuǎn)很遠(yuǎn),她給了擁有近八百年歷史的南音藝術(shù)全新的生命力。
早春時節(jié),作為東方藝術(shù)中心“2013名家名劇月”的參演作品,王心心帶著屬于她一個人的作品《琵琶行》,來到上海。林懷民先生曾說,閱讀了古詩詞那么久,直到聽到王心心演唱的《琵琶行》,才第一次真正了解《琵琶行》。而事實上,《琵琶行》的誕生,其實就和云門舞集的創(chuàng)始人林懷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當(dāng)年,林懷民給王心心出了個題——讓她一個人在臺上彈唱《琵琶行》。王心心對整整45分鐘一個人彈唱感到?jīng)]有自信,可林懷民當(dāng)時就安慰她:“你的每一次彈撥就是舞蹈,你的每一個眼神都充滿了戲劇。”而最終的結(jié)果,并沒有讓林懷民失望,反而贏得了如此的評價:“她尚未出場,我們靜默等候;她一開口,我們便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有趣的是,盡管用南音演唱白居易的《琵琶行》,似乎是最為貼切與自然的,然而事實上,《琵琶行》中有很多描寫琵琶演奏技巧的詩句,諸如“輕攏慢捻抹復(fù)挑”、“鐵騎突出刀槍鳴”、“四弦一聲如裂帛”等,并不能用南音演奏的琵琶加以表現(xiàn)。為此,王心心去年特地前往日本,學(xué)習(xí)用唐代流傳至今的薩摩琵琶進(jìn)行演奏,希望能“還原”《琵琶行》詩句中最原本的音色,從而一窺唐代至今綿延不絕的一抹舊時韻味。
演出當(dāng)天,數(shù)百人的音樂廳幾乎滿座,久未露面的著名作曲家瞿小松,以“粉絲”的身份,趕來上海捧場。而他對南音的喜愛、癡迷與研究,絕不亞于專業(yè)演奏人士。音樂會結(jié)束后的慶祝宴上,《新民周刊》記者得以與王心心、瞿小松二位展開一次有趣的跨文化對話。
平凡的從容
《新民周刊》:瞿小松老師這次是專程從北京飛到上海來聆聽王心心老師的演出的。多年來您一直立足于傳統(tǒng)古典樂、原生態(tài)歌曲與當(dāng)代音樂的交融,是否心心老師的南音也打動了您?給您啟發(fā)?
瞿小松:我寫過一個歌劇《試妻》,里面有一段昆曲。這幾年我在為敦煌藝術(shù)研究院的多媒體展示廳寫配樂,接觸了許多中國傳統(tǒng)音樂,包括戲曲、原生態(tài)民歌等等。我知道王心心這個名字,是梨園戲的藝術(shù)家曾靜萍的介紹。而第一次聽到心心老師的演唱,是她去臺灣時出版的碟,很簡陋,沒有曲目名,沒有時間長度,什么都沒有。但是一聽就放不下了,我知道,這就是我所要的音樂。我覺得南音是一種平凡的從容。心心老師的南音很安靜,是屬于非常平靜的東西,在南音里,喜怒哀樂是平等的,又是那么沉得住氣。在我看來,洗盡鉛華。
王心心:是的,南音里無論是喜悅還是憂傷,都要求表現(xiàn)得舒緩,甚至有一點點壓抑。在南音里,沒有十分歡快的曲子,哪怕唱詞是很歡樂的。
瞿小松:就好像我說的,我總希望把我不想做的事情變成我想做的事情。這個跨越是一點一點積累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鼓勵自己完成不想做的事情。像郎朗,我問他:“你爸打你嗎?”他說:“當(dāng)然打。”后來,他就成就了。世界上的事都是有邏輯聯(lián)系的。在南音里面,喜怒哀樂都應(yīng)該是平等的。所以我認(rèn)為,不能對沒有才華的學(xué)生抱有歧視。
《新民周刊》:小松老師似乎對南音的琵琶也特別欣賞。雖然簡單,沒有繁瑣的技巧,卻能動人心魄,很純粹。
王心心:其實南音的琵琶是后期發(fā)展的。四條琴弦就是四條線,看著譜子直接可以摸琴彈。不是邊彈邊唱的,先彈一段,在唱的時候就聽的。最多就給一個基準(zhǔn)音,剩下的就是唱。
瞿小松:中國的琵琶很多變化,為什么你們不能變化?就好比“梅派”最牛的地方就是大音希聲,沒有拍,動作都很小。南音也是這樣。昆曲的雅是有體系的,有系統(tǒng)支撐的,是程式化的,但沒有人真正去總結(jié)。因為總結(jié)出來很難。提煉的是一種想法,不是技巧。戲曲大量依靠口傳心授,但不要過分強調(diào)。而南音只給骨架,怎么演靠自己。
不妄自菲薄
《新民周刊》:以前是什么樣的演員造就什么樣的觀眾,從梅蘭芳開始,就是什么樣的觀眾造就什么樣的演員。
瞿小松:這個是相互的,是互動的。這是跟人有關(guān)的。有一次我去了泉州師范做講座。學(xué)生里學(xué)南音的抬不起頭,我問他為什么抬不起頭?他們說學(xué)西方音樂的同學(xué)說他們土。我就覺得奇怪,第一,中國跟西方音樂為什么要跟得這么緊?第二,一定要學(xué)了西方音樂才能成為現(xiàn)在的藝術(shù)家嗎?
王心心:我覺得高人都是通的,誰也沒必要妄自菲薄。
瞿小松:不是一定要經(jīng)歷西方才能成就。比如說每一個文化的傳統(tǒng)呈現(xiàn)出來的東西,佛教和佛教藝術(shù)不是中國的,可張大千的畫里就有敦煌壁畫的影子。再比如昆曲,它不像京劇,不是一味地在唱。要用丹田氣,慢慢把氣輸出來,昆曲是需要技術(shù)支撐的,這和西方美聲唱法是異曲同工的。
《新民周刊》:這也正是您多年來致力傳統(tǒng)民族音樂推廣的原因所在吧?
瞿小松:有時候適當(dāng)?shù)囊龑?dǎo)會有想不到的作用。每年我去音樂學(xué)院演出,我只做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去年一個藏族歌手,只唱佛曲,這種佛曲和漢傳佛曲不一樣的。如果去靈隱寺,會聽到的是漢傳佛曲。但他是第一個離開藏區(qū)的歌手,唱的佛經(jīng)。用我們漢人的感覺,他就看起來傻傻的,站在臺上不知道怎么辦。可是一開口,驚為天人!我想就是要這樣。希望大家不要放棄你的期待,好比無意中走到一個寺廟,聽到佛曲,或者無意中走過一個村落,聽到人家在對歌。
大家愿意走就走,愿意留下來的就留下來。最后,我做的演出持續(xù)了一個多小時。很多觀眾來聽時,心是打開的。我找民歌,要去海拔數(shù)千米以上的地方,為什么?因為只有那里還沒完全通電,藏民們依舊保持著傳統(tǒng)的娛樂方式。南音也是如此,由于泉州沒有過度商業(yè)化開發(fā),使得那里成為一方傳統(tǒng)文化的凈土。
《新民周刊》:您認(rèn)為南音保存八百多年至今的價值何在?
瞿小松:你要知道,一個人真正呈現(xiàn)他所體會的所有音樂的時候,他的魅力是自然呈現(xiàn)的。一個人如果能真正開放,那么就是有智慧的人,否則就是匠人。我想,南音給我最大的啟發(fā),就是不要以一個標(biāo)準(zhǔn)來提供所有標(biāo)準(zhǔn)。我們?nèi)绻艞壩乃噺?fù)興以來一直被灌輸?shù)臉?biāo)準(zhǔn),就能找到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從科學(xué)角度來講,音樂是可以總結(jié)的,是與人體、心理、生理有關(guān)聯(lián)的,這有可能解開中國藝術(shù)或是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彼此是可以打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