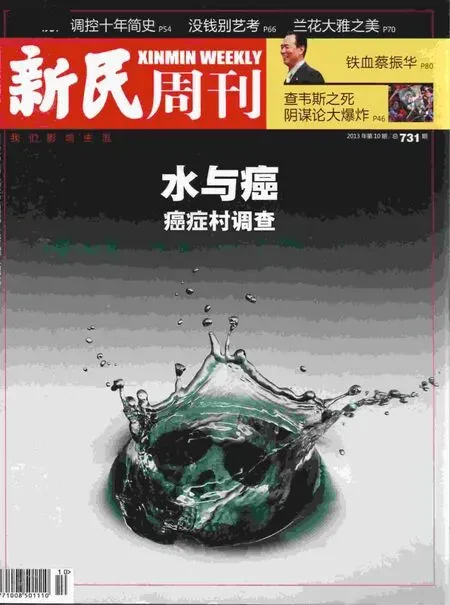年輕人要求更多權利

喬健副教授是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他是《中國勞動關系報告》一書作者,研究領域為工會。
在朱镕基擔任總理的年代里,中國放棄了在勞動關系的問題上糾纏于意識形態之爭。朱镕基主導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破產、重組,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重新學習在市場化的環境中生存。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涌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這個混亂的過程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但也遺留下很多痛苦的后遺癥。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10月,上任不足一年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三峽庫區云陽縣考察時,遇見當地農民熊德明。熊德明向溫家寶反映,在外打工的丈夫有2000多塊錢的工資長期被拖欠,影響孩子交學費。溫家寶親自為熊德明家討要這筆工資,一時傳為佳話。
在溫家寶擔任總理的10年里,中國的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利用加入WTO的契機,延續了一條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推動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勞動關系的市場化改革對繼續對發揮了關鍵的支撐作用。
溫家寶討薪的故事反映出中國政府在勞資關系中扮演的強勢角色,也反映出中國正在經歷的巨大的歷史轉型。這個轉型涉及中國的意識形態、經濟戰略、中國的人口狀況,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解決一些復雜而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溫家寶的壓力下,各地從2003年開始清理積欠的農民工工資。盡管2009年之后,拖欠農民工工資情況再次反彈,但規模遠不及2003年。這可能是過去10年中,溫家寶政府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從討薪到立法
為應對國企改制和民營企業發展所帶來的勞工問題,中國加強了針對勞動關系的立法活動。過去十年里頒行的涉及勞動關系的法律是歷史上最多的。2007年,中國頒布了《勞動合同法》。這是個特別重要的法律,它禁止企業在沒有合同保護的情況下用工,也限制企業任意解聘員工。長期以來,這正是中國企業所做的事情。2012年,這部法律又進行了修改,專門針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勞務派遣作了修訂。
盡管工會在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2001年頒布的《工會法》修正案和2007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還是保障了工會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以維護職工權益的權力。這為未來工人通過組織來保障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到2011年末,全國共簽訂有效集體合同96.2萬份,覆蓋職工1.22億人。
為推動執法監察工作,2004年國務院頒布了《勞動保障監察條例》。2011年發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提出要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針對近年來勞動爭議頻繁激增和這項制度存在的缺陷,2007年又頒行了《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該法創新和完善了勞動爭議的處理機制。
在勞動標準方面,2004年修訂《最低工資規定》,建立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兩檔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除經濟危機的2009年,每年都有20多個省調整標準。目前,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的15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的14元。
在過去10年里,我國還頒行了《社會保險法》(2010)、《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2011)及《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2013)等勞動保障重要法律政策。
正是在這十年,中國適應市場經濟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初步形成。
法外之地仍然存在
勞動合同已經成為中國人最熟悉的事物。“單位”意識淡化,通過勞動合同來建立市場化勞動關系并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進一步強化了我國勞動關系的契約化。據統計,2011年末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86.4%。
但在實際經濟中,中國發展出了復雜而高度彈性的用工機制。國企中的勞務派遣、家政業的非全日制用工及微型企業幫工等非正規的勞動關系有明顯增加。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普遍實行“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勞務派遣大行其道,新員工不再和老員工享受同等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目前通過勞務派遣形式的在崗人員已經達到6000萬人。在部分央企,甚至有超過2/3的員工都屬于勞務派遣,儼然成為企業的主流用工方式。
到今天,仍有部分群體未簽訂用工合同,如事業單位改革中的大量工勤人員,50多萬農電工人、330萬保險經銷員、200多萬出租車司機,用工荒背景下愈加增多的學生工甚至童工,家政用工,生產線外包工,軍隊用工,社會導游,職業運動員,以及國際投資中的勞務外派人員等,都亟需出臺立法或政策以保障其權益,規范其勞動關系。
在過去的十年里,特別是后期,一種新的不平等日益體制化。那些控制經濟發展命脈的國有壟斷企業,通過其行政壟斷地位、政府財政補貼和少繳利稅,其正式員工的薪酬和非貨幣收入普遍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行業間收入差異巨大,在企業內部,大量使用的勞務派遣工與正式員工相比,也存在明顯的同工不同酬現象。
年輕工人要求更多權利
在過去10年里,勞資沖突的加劇是中國最值得重視的問題之一。這極有可能會影響到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走向。
中國已經有2.6億農民工,他們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團結意識顯然在不斷增長,在年輕一代中尤其如此。學術界把那些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稱作新生代農民工。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專項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為8487萬,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已經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
同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多數人不再“亦工亦農”,而是純粹從事二、三產業;就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工作勤奮。
這些年輕工人在進入工廠之前,已經在學校中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他們廣泛使用互聯網、工余時間與同伴好友不時聚會,進入各種娛樂場所消費,這決定了他們的發展預期。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其維權態度更為積極。據統計,新生代工人當權益受到侵害而采取投訴行為時,以集體投訴方式進行的占45.5%。在訴求內容上,勞動者已產生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要求,從基本權利訴求轉向利益訴求。
10年來,中國的勞動爭議激增,且重點正在從個別爭議轉向集體爭議。尤以2008年下半年以來,那些保護勞動者的法律開始顯示威力。由于經濟危機加劇,企業裁員破產、勞動爭議顯著增加。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制造企業富士康連續出現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這些都加深了中國社會對工人權益的關注。同一年,廣東南海本田公司發生了罷工事件,并推動了各地以提高工資為目標的罷工停工行動。
總的說來,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中國的工人正在尋求“體面勞動”。但要實現這個目標,他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實際上,勞動者權益受侵害的情況在中國仍很普遍。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已進入職業病高發期。全國30多個行業和2億勞動者不同程度遭受職業病危害,600萬塵肺病患者掙扎在死亡線上。
另一個牽動人心的問題是,中國的收入分配呈兩極分化的趨勢。據全國總工會的資料,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連續22年下降,致使勞動者不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為了讓占中國就業人口多數的工人感到滿意,由此保證社會穩定,中國政府還需要解決很多重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