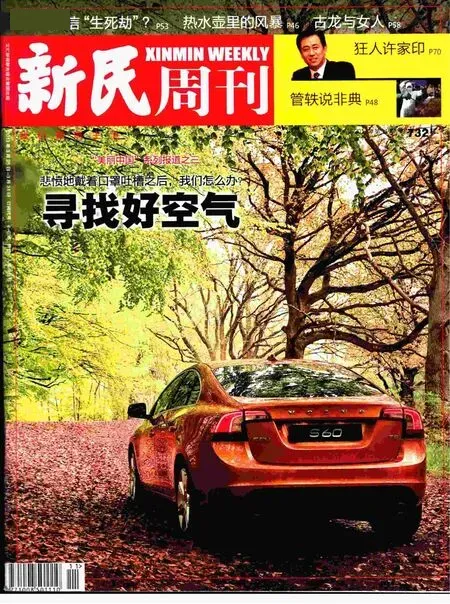有一種敬畏如此陌生
洪流
3月4日,一名兩個月大的嬰兒的生死,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當天上午7時許,長春市一對粗心的父母將剛出生兩個月的嬰兒放在汽車后座上短暫離開,車輛被人乘隙偷走。為此全市數千警察和熱心市民都加入了搜尋的行列,然而到了3月5日,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還是發生了:犯罪嫌疑人周喜軍在盜車途中將嬰兒掐死埋于雪中……
以一個尚在襁褓的無辜生命的死亡來作為本文的開篇,對于孩子,對于孩子的父母,對于也有孩子的筆者來說,都是殘酷的。事實上,筆者只是想在哀痛和憤怒的對周喜軍的喊殺聲中,提出一個問題:
當我們要以合法的方式剝奪罪犯的生命的時候,我們對于生命的敬畏,到底以何為底線?
2000年4月1日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4個失業青年在南京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及其妻兒。普方先生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老人作出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德國沒有死刑。我們會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同年11月,居住南京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自此致力于改變江蘇貧困地區兒童的生活狀況。協會用善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希望他們能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為他們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創造機會。這一舉動默默延續了9年,已有超過500名的中國貧困學生因此圓了求學夢。
2007年4月16日,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了一起韓國留學生趙承熙槍擊案。趙承熙在開槍打死32個人之后,也開槍殺死了自己。在之后舉行的守夜祈禱會上,人們點亮了33根蠟燭,而不是32根。也就是說,他們既要為那32個受害者祈禱,也要為那一個加害者祈禱。學校在廣場上安放的悼念碑也是33塊,而不是32塊。33塊悼念碑旁都有鮮花和蠟燭。在趙承熙的悼念碑下,有個紙條這樣寫著:“趙,你大大低估了我們的力量、勇氣與關愛。你已傷了我們的心,但你并未傷了我們的靈魂。我們變得比從前更堅強更驕傲……愛,是永遠流傳的……”
2011年7月22日,挪威的布雷維克在奧斯陸市中心制造爆炸案,隨后在奧斯陸以西的于特島開槍行兇,共致死77人、傷80多人。2012年8月24日,挪威首都奧斯陸一家法院判處布雷維克21年監禁。挪威不設死刑,最高刑期21年。
都是惡性殺人案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被害人心態、民眾呼聲和法院判決,這當中的區別在哪里?難道普方的母親、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學生和已經廢除死刑的挪威民眾,他們心中沒有悲傷和憤怒嗎?
人之所以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案件的結果其實是多方面的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共同造成的。貧困、貪婪、憤怒、恐懼等,即一些宗教教義中的“惡”或“罪”,都可能成為犯罪的原因。如果死刑不能有效阻止貧困,不能阻止貪婪,不能阻止憤怒,不能阻止恐懼,那么我們為什么一定要用死刑?如果用其他刑罰可以阻止犯罪的人重新犯罪,我們為什么要用死刑?
在刑法中,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是最嚴重的犯罪,因為生命是神圣而無價的,我們之所以反對殺人,是因為我們敬畏生命,這種敬畏應該是一種普世性的。但如果他人在“罪”或“惡”的驅使下殺人,我們是否也要敬畏這些“罪人”或“惡人”的生命?殺人如果有了法律的依據,我們可以不需承擔法律責任,但是,我們心中對于生命的敬畏,是否就要劃定一個范圍?
這些天電影院線在放映周星馳的《西游降魔篇》,在片中,所有的惡魔都是心中有孽障的,要真正地降魔,靠殺是沒用的,因為真正的“魔”,在于妖怪的心中,也在于我們對于敬畏生命的不完全的釋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