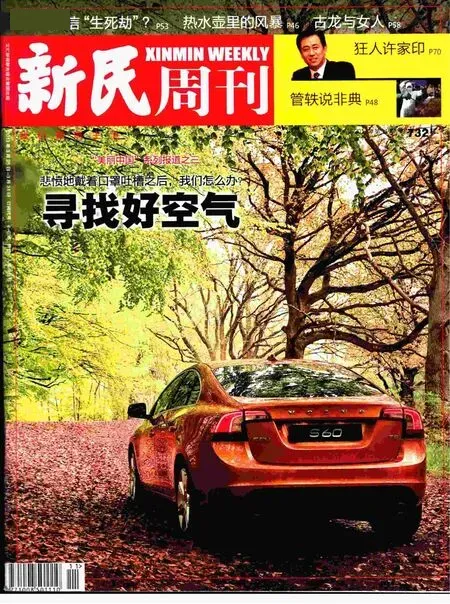關于夏商,關于東岸
紫鷹
在他逐漸被低調占據的不惑之年,棱角悄悄退去,但我仍然可以嗅到他隱藏在更深處的野心,應該會把他的“雙面人生”推向極致,進行到底!
上世紀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浦東變遷的歷史片段,引發了夏商去完成《東岸紀事》。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歷時六年,觸動他思考一些人生值得懷疑的問題:
“通過地域的轉換,人物發生變化,物質上可能有些人滿足了, 但是這種變遷可能讓有些人失去了自留地,萌生了鄉愁。現代化的轉變過程究竟使人更有幸福感還是正在失去幸福感?”
他曾是這段歷史的一分子,理所當然成了歷史變遷的目擊者。他用一個老浦東人的眼光來洞悉那段歷史,并且在最容易被忽視的邊緣標上了自己的注釋。
他出生在上海川沙縣的一個自然村,破舊的宅子坐落于城鄉接合地帶,因為時代的變遷又不得不與純粹的城市聯系起來。從六里橋、南碼頭、塘橋、爛泥渡(陸家嘴)的生活進行曲中,聽到的是鄉村、城鎮、城市衍變的旋律。
這是他唯一一次準備了寫作提綱的創作,在寫作之前,他故地重游,用照相機尋找往昔的氛圍和記憶。百多張照片不僅成為了有力的寫作工具,而且成為了浦東變遷過程中遺失原生態的佐證。雖然當時已經無從獲取三十年前的影像,他卻在竭力選擇相似處;雖然六年的時間近在咫尺,可當年的一切還是在繼續消失。
《東岸紀事》其實是在完成還原歷史的真相,作為地方志的一部分也不過分。地名、故事、時間、事件都在逼近真實,唯有人物是虛構,但不排除有他和他周圍人的蹤影。
夏商反對把《東岸紀事》冠以“半自傳體小說”的稱呼,而要用“懷疑小說”的名頭來面世。正如有人曾描繪的土著人,被嶄新的文化、經濟甚至是闖入他們生活的移民所干擾,突然某一天土著人發現這個地方并不屬于他們,作家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扎根土地的人物命運所發生的變化……
正如更多的小說家開始遠離閉門造車的虛構,貼近和關注歷史,小說有著記錄歷史的責任,而這樣的小說往往會被歷史遺留下來。夏商作為浦東三十年變遷的親歷者,他自信而毫不夸張地說:“關于這一時期的浦東平民史,不會有人比我寫得更扎實。”
自信一直是夏商給人的第一印象,并且具有無從提防的“強制性”植入特性,《東岸紀事》在幾經周折之后終于面世了。帶著些許吊詭,帶著些許頑強,帶著些許杰出,沖破了與創作同等艱辛的重重世俗阻礙,像一羽涅槃之鳥越過樊籠,脫穎而出。
《東岸紀事》寫作的順逆之道并不影響夏商的生活和信仰,除了小說之外,畢竟還有他創辦的“普茶客”品牌,普洱茶一遍又一遍經過沸騰的水過濾,還是醇香怡人呈現著琥珀色。人跟茶沒什么兩樣,無論你曾經用任何一種形態出現,最終總要回歸到一種顏色。
在我認識夏商似乎只是彈指一瞬的二十年里,記憶給我的提示,就如他自己定義的“雙面人生”一般,他對自己歸納的準確,可能就是他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把握恰到好處。他在時間的流淌過程中一直在實踐自我,不是將“雙面人生”演變成人格背離,而是一種接近完美的統一。
這二十年里,夏商以兩種身份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很容易被陌生人把他分割成兩半。而事實上,他也是在人生的舞臺上扮演著兩個不容易聯系起來的角色。從模糊走向清晰,甚至越來越不容易混淆,又刻意將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拿捏到一起,并且大聲告訴世人絕對唯一,而非孿生。
現在,人們可以從眾多非此即彼的標識中馬上辨認出夏商的“雙面人生”,這種和諧應歸功于他找到了一個契合點,一個與他性情、嗜好、生活狀態唯美吻合的支點。充滿離奇,但又不乏真實存在。在他逐漸被低調占據的不惑之年,棱角悄悄退去,但我仍然可以嗅到他隱藏在更深處的野心,應該會把他的“雙面人生”推向極致,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