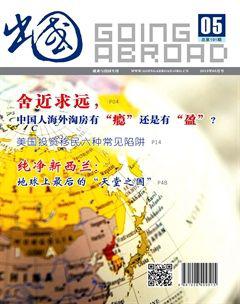火線觀光突尼斯文
郭瑩(英國)
對于北非突尼斯最初的印象是1980年代看過一部英國電影,名字忘記了,不是什么大片。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少年站在突尼斯城的露天市場,他身邊有一個紙箱子上印著中英文:中國制造。
2月8日,英國BBC新聞報道如下:
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成千上萬人參加了遇刺身亡的反對派領袖貝萊德的葬禮,警察與抗議者發生沖突。警方向在墓地前打砸汽車的年輕人發射了催淚彈。據報,南方城市嘎夫薩也發生沖突,反政府抗議者向警察總部投擲石塊。工會舉行35年來首次大罷工,突尼斯全國許多商店都關了門。
又一場阿拉伯之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
英國政府沒有發出前往突尼斯的旅游警告,故旅行社不給退票,我只得硬著頭皮孤身前往首都突尼斯城以南200公里處的度假圣地Sousse,來一趟“火線觀光”。
來到Sousse城的次日清早,拉我去民俗市場的的士司機,一邊收聽首都民眾大規模示威抗議及聯合政府辭職的新聞播報,一邊回答我的提問。司機表示除了阿拉伯母語之外,他還會說法語、英語和德語,都是在學校學的。司機并說,突尼斯人民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我忍不住對司機開玩笑說:“這么好的福利,你們干嘛還上街?”此話的緣由是,我腦子里突然涌現1980年代初期,央視國際新聞老報道歐美國家街頭的游行抗議活動,那時我家沒有電視機得去鄰居家看,聽周圍人議論:看!老外們個個都戴著手表,都有錢戴上手表了還游什么行呀?那時中國民眾買手表得憑票,電視機、自行車、縫紉機還有手表是訂婚彩禮的幾大件。以往我在希臘、摩洛哥旅行時整天與的士司機斗,絕不其樂無窮。Sousse侯在酒店門外的的士,好像定有攻守同盟的“外賓價”,去市中心要4個第納爾。抵達Sousse的次日上午在碼頭民俗市場,我詢問兩位突尼斯女孩哪里有當地人購物的商場,以往的異國旅行經驗是為游客服務的所謂民俗商品集市,價格都是“外賓價”,同樣的商品在當地人消費的超市則是“內賓價”。兩個女孩自告奮勇陪我前往,我們打了一輛的士,我信心十足這次有當地人保駕護航,司機再不能宰老外。的士七拐八拐5、6分鐘后就到了,司機要求8塊第納爾,我的零錢不夠,身旁的突尼斯女孩掏出錢包要湊上一份,司機見狀急得一通嚷嚷。這次我“聽懂了”阿拉伯語,那就是:“你沒事吃飽了撐的自掏腰包!讓老外付錢。”于是,身旁的女孩立馬手又縮了回去。下車走進購物中心,我發現就是下榻酒店馬路對面的商場,只不過司機繞道將車停在了后街,多宰了我4塊錢。購物中心沒有超市,我向4位逛街的女孩打聽,4個女孩一臺戲,她們熱烈地討論應該引介哪個超市給老外,嘰嘰喳喳了15分鐘,常常是3位女孩交頭接耳時總有第4位用不甚流利的英語建議我應該去哪一家,一番議會辯論后女孩們終于達成一致,她們為我叫了一輛的士。
這次我吸取教訓一上車就要求司機打表,車子又在夾雜著咖啡館、理發店、雜貨鋪及飄逸著阿拉伯香料的老街上兜圈子,繞過了N個咖啡館之后街道越發地破敗起來,我心疑了怎么還不到呀?不就是一個超市嗎?難道這位司機師傅要把我拉到村里當他的第四房太太不成?這般“亡命飛車”看來這漢子還真是著急討四房。當司機又拐了幾條一千零一夜的老街后,當我差點就喊停車我不去超市了的當口,車子終于停下來,果然是家大超市。司機要1,700第納爾,由于我頭天晚上9點下飛機直接去了酒店,還沒轉過彎來當地的貨幣單位,早上的兩趟來回司機要4塊及8塊錢車資我沒太在意,現在猛聽到上千位的數字立刻就把我嚇暈了。司機見我手里有一把硬幣就揀出一塊錢和七個銅幣,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上午的4塊及8塊錢都是“外賓價”,這位誠實的打表司機則是“內賓價”,實際上他要的才不到兩塊錢,路程可謂遠得快到阿里巴巴村子了。為了鼓勵他的誠實,我付了3塊錢。原來,突尼斯的貨幣單位是:1000才是一塊第納爾,比如,我換了20英鎊,銀行水單上印著
酒店里的英國游客告誡我別獨自外出,這里可是穆斯林國家。兩位英國婦女向我抱怨她們遭遇了當地男人的騷擾,所謂騷擾,就是傍晚路邊的小伙子盯著她們“虎視眈眈”,還上前搭訕要她們一起去喝一杯,并且尾隨了她們一段路。其實,這是西方游客與當地男人之間得到的信息各不相同,我有在土耳其、希臘、埃及和摩洛哥的旅行經驗,當地男人都曾提到一些中年西北歐的師奶跑到地中海來是為了尋春,的確,在地中海國家的旅游區我曾見識過,西方容顏已逝的半老徐娘傍著位當地青年男人,在SOUSSE幾天也有見識。因此,一些當地男人主動搭訕西北歐婦女,是出于盛傳西方婦女熱衷享受浪漫假期的“口碑”。另一方面,地中海男人喜歡在街上“虎視眈眈”盯著美眉是一項街頭風俗,而地中海美眉們,面對滿大街老少爺們的注目禮和口哨調戲,她們皆能表現出久經考驗般地大義凜然。比如,練過童子功的意大利靚女們,喜歡架著太陽眼鏡,以超然的傲慢昂首闊步穿越男人們的眼球儀仗隊。與地中海姐妹們的從容不迫相比,來此度假的西北歐女同胞們,由于先天“培訓不足”只能干“吃虧”。因為,西北歐國家里在街頭盯著婦女瞧稀奇,那是很不紳士的行為,西北歐男士們若想要欣賞街頭美眉,也只能裝作“視而不見”地偷窺。于是,當西北歐婦女們來到“高視社會風俗”的地中海國家,當遭遇地中海帥哥火辣辣的調情時,她們常常會不知所措、愣愣地回視對方,這一舉動顯然愚蠢,等于在鼓勵對方的“干勁”。
我下榻的酒店餐廳服務生,有兩晚為我上甜品的時候,詢問我一起去喝一杯怎么樣。我都拒絕了。英國女人聽了我的“遭遇”后,大驚小怪地奉勸我:“趕快弄個戒指戴在無名指上,你手指上沒有結婚戒指,光憑你三寸不爛之舌說有老公,他們不會相信。”英國女士還現身說法指著她自己的無名指說:“看,雖然我離婚了,但我為了這趟旅行特別弄了個戒指戴上。”我忍不住撲哧笑出聲來,覺得英國女士過于緊張了。
我打算前往Monastir城參觀清真寺,咨詢前臺值班的小伙子,他是學法語的大學生目前在酒店實習沒有工資,他父親是位司機但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母親是家庭婦女,他下面還有3個弟弟。由于大學教育免費,他這樣的底層孩子也有機會享受高等教育,他夏天大學畢業后準備繼續讀碩士。對此,我忍不住又感嘆了一句:“這么好的福利,你們還上街游行。”突尼斯作為前法屬殖民地,當地人告訴我這里的小學是阿拉伯語教育,中學和大學教學語言全是法語。前臺小伙說他周三輪休時可以陪我一同去Monastir,我趕忙問那要付你多少導游費?他說不收錢。我表示周三要回英國,決定獨自前往。我又詢問,一個外國女子獨自旅行是否安全?小伙子一口咬定安全。我說:“恐怕是對你安全,對我未必吧?”小伙子一臉認真地表示:“我們尊重婦女。”好!吃了定心丸。
原以為路上至少會遇到北歐或者荷蘭、德國的自由行客,因為這些國家的背包客堪稱“世界公民”,通常世界的每個角落皆能輕易地“偶遇”他們。大概由于最近的突尼斯局勢,加上前不久的阿爾及利亞人質危機,路上居然沒遇見一個外國人,火車車廂里也全是當地人。我舉著車票詢問對坐的一位小姐,她不會說英語,隔座一位包頭巾小姐過來坐到我身邊用不流利的英語攀談。她表示特別喜歡中國,向往有朝一日游覽長城,她居然雙手合十吐出標準的漢語:“你好”。我詢問她從哪里學來的,她說看電視風光片聽來的。我好奇地問她關于穆斯林婦女包頭巾的風俗,比如她裹著包頭巾,而對坐的女孩不但蓬松長發披肩,腿上還套著黑色緊身褲豐乳肥臀畢露,街上的大多數婦女也都不裹頭巾。女孩說包不包頭全是個人選擇,她的頭巾是她的保護是她的神。女孩為了解釋包頭巾對她的人生重要意義,窮盡她能找到的有限英語詞匯,這時斜對坐的一位小伙子過來充當語言支援,他拿出手機試圖用谷歌翻譯將阿語譯成中文,可惜,他說的阿語譯成中文是“胡子”,雞同鴨講。周圍姑娘和小伙子們都是大學生,我不愿意透露自己是英國公民來自英國,因為前不久剛發生阿爾及利亞人質危機,死了40個外國人質其中包括6名英人。當年青人好奇我從中國飛來突尼斯要多久的航程,詢問在哪里轉機時,我脫口說在英國轉機,話一出口立馬后悔,顯然,我應該編造從迪拜或從巴黎轉機才合邏輯。幾位聽說我在英國轉機愣了一下,幸好姑娘急于咨詢中國的社會宗教,年青人沒在意我的謊言不能自圓其說。我解釋中國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還有穆斯林……女孩追問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沒有宗教信仰。”她立馬詫異、同情地看著我:“沒有宗教信仰?”顯然女孩驚訝的臉上寫著:那你如何生存?
接下來幾位年輕人要求上“速成漢語”課,要我教他們說:你好,謝謝,再見。還有:歡迎你來突尼斯。我十分驚異他們的語言模仿能力,幾位的發音居然都很標準,大概他們自小接受阿拉伯語、法語及英語教育,外語的語感都很好。小伙子詢問我對突尼斯的印象,我自然是熱情洋溢地夸贊有加。于是,小伙子追了一句:“那你不要回中國就留在突尼斯好了,我們歡迎你。”這可真是不同,因為通常中國人在西方國家留學、旅行與西方人攀談時,西方人有時常會問:“你來了多久?何時回國?”甚至有西方人會問:“你不會不回去吧。”出Monastir車站時見到一位倒在地上的乞丐,他是我幾天來唯一看到的街頭乞丐,看著這位乞丐的傷腿,這里的免費醫療體制得到了印證,我注意到乞丐腿上的傷口是今天新包扎的,我特別駐足觀察了一下,紗布很清潔包扎得也很專業。待我2小時后返回車站時,乞丐已經無影無蹤。
從Monastir城清真寺返回火車站前,我在集市上截了一輛的士,司機掐著手指形容火車站其實就在街拐角處。到了火車站前,我詢問司機車資,畢竟是小鎮子人,司機沒見過“大世面”,還沒學會宰老外長肥膘,他居然不好意思要錢,一再說路太近了。我遞給他300第納爾銅幣,司機說:“好,算你送我一杯咖啡。”
突尼斯一周,天真藍;陽光真燦;空氣真清;人民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