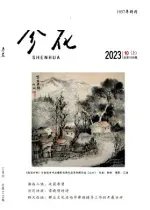沒有墓碑的墳塋
王天亮
在長白山三道松江河岸邊的樹叢里,曾經有一座長滿野草的墳塋。據老輩人講,墳塋里掩埋著三具抗聯烈士的忠骨。
記憶里,在墳塋的周邊有幾株高大的柳樹,其中有一顆還是“合歡樹”。粗壯樹徑5米左右的上方,自然分開兩個樹杈,她們相互交織相互依偎著擁吻藍天。再往岸上100多米遠,有幾棟破敗不堪的民房,那里就是我兒時的三味書屋——前川林場子弟學校了。
依稀記得,37年前的那個清明時節,天空飄著初春的暖雪,已經開始融雪的地面上露出斑斑土痕。因為這一天,我們要參加學校組織的為革命先烈掃墓活動。
一大早,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高舉鮮艷的紅旗,裹著初春的薄寒,來到了距校址100多米遠的英雄墓冢,舉起我們稚嫩的小手,跟著老師宣誓。那時我才知道,長眠于墓穴里的抗聯英雄是兩男一女,他們的平均年齡才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本應是人生最美的花季,而他(她)們卻用年輕的生命,為了民族的解放和獨立,用一腔熱血,把自己深深地融入到了長白山的山脈之中。成為了捍衛華夏國門的門神。
遺憾的是,因為我們是學生的緣故,此后竟再也沒有機會參加過類似的祭奠活動,以至于,我竟忘記了她們的名字。
忘記是哪一年了,一天下午我剛放學回家,父親站在我們自家的院子里,手里拎著鐮刀和鐵鍬,讓我放下書包跟他走。兒時的記憶里,父親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因為父親是一名軍人,是一名有著十余年戰爭經歷的軍人,說句不敬的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多年的軍旅生涯,造就了他威嚴剛毅的性格。踏著細碎的斜陽,沿著河邊的土道,父親領著我來到了烈士的埋骨處。我不知道父親領我到這里的意圖。只見他拿起鐮刀,圍著墳塋開始軋樹棵子,不到一個鐘頭,整個墳塋轉圈收拾得利利索索。隨后我們爺倆開始四周取土,往墳塋上培。從沒見過父親流淚的我,哪天竟看見父親的眼里閃動著晶瑩的淚光,臨走時,父親還在墳包上壓了一塊很大的土坯。
那一天,父親跟我說了很多話,他說;“這些人,是打江山的英雄,人們不應該忘記他們,等你長大了,別忘了給他們軋軋棵子填鍬土。”
直到真正地長大后,我才理解了父親內心深處那股厚重的軍人情結,他不僅是在祭奠長眠于河畔的幾位英烈,更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在緬懷那些曾經和他一起為了新中國浴血奮戰而犧牲的戰友。
多年后,我在查閱一些史料時獲悉,長眠于岸邊的幾位英烈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的戰士,軍長叫王德泰,政治部主任叫李學忠。朝鮮領袖金日成當時還只是下面的一個師級政委。1936年8月9日,李學忠所在的撫松縣東崗鎮大堿廠密營(兵工廠、后方醫院)突然被日本走狗李道善的自衛團百余人包圍,正在醫院治療腿傷的李學忠立即組織密營全體人員奮勇抵抗。但是,由于我方多為傷病人員和非戰斗部隊,又是倉促應戰,造成重大傷亡。年僅26歲的李學忠也在激戰中英勇犧牲。而在激戰中突圍至此的三位抗聯戰士,與埋伏于此的小股敵人奮力搏殺后,終因寡不敵眾英勇就義。第二天,她們被幾位好心的獵戶草草掩埋,因為怕遭到李道善的報復,幾位獵戶沒有給烈士們立碑。
1985年撫松縣人民政府為抗日名將李學忠舉行了隆重的墓碑揭奠式,據說堿廠村村委會也曾給三位烈士立過一次碑,但由于是木碑,沒過幾年便在風雨的侵蝕中不見了蹤影。伴隨他們的只有墳頭那叢生的野草和幾株細瘦的柳樹。
多少個春秋過去了,花謝花開草長鶯飛,昔日那幾株細瘦的河柳,如今早已長成了參天大樹,而烈士們的墳塋和那幾具曾支撐河山的傲骨,早已伴著長白山大開發的腳步,化作忠實守護這片沃土的山魂,護衛著祖國的東部邊陲。
令人遺憾的是1998年那場罕見的特大洪水,硬是把整條河道沖寬了20余米,烈士的忠骨和那高高隆起的土包早已不見了蹤影,連同那棵“合歡樹”也被肆虐的洪水連根拔起沖走了。幾位上了歲數的老人感嘆地說:“英雄們真的萬古流芳了。”
先烈們是為信仰而戰為理想而死的,雖然洪水沖走了他(她)們安歇棲身的墓冢,但卻永遠沖不走那一段血與火的歷史,抹不去人們心中無盡的懷念與敬仰!清明對于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淚飛化雨的季節,斜風細雨打濕的不應只是回憶的夢境,更多的還是那阻不斷的血脈情緣。或許我們的夢和你們的夢,只是一雨之隔,但你們用鮮血孕育出的太平夢境,早已伴隨著1949年的那一聲巨人的吶喊,抑若春霆發響,一雷驚蟄。
雖然你們的身軀早已化作了一捧溫潤的泥土,但沿河兩岸的青松翠柏和掩映在樹叢中的綠樹村莊,卻植根于你的泥土中正散發出盎然的春意。毋庸置疑,那桃紅柳綠太平的盛景,一定是經受了無數先烈鮮血的滋潤,才使得這片被戰火燒焦的土地變得如此厚重秀美。一個世紀快過去了,自然萬物在一如既往地繁衍生息,冰凌花開了一茬又一茬,大森林的年輪轉了一圈又一圈。倘若烈士們泉下有知,看到這安定祥和充滿希望的世界,他們肯定會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有一縷風曾在這片森林中走過,雖然她沒有裁剪出花團錦簇的三月陽春,但她走過的地方,花草樹木都化成了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