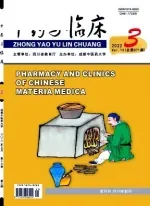非處方藥品說明書【用法用量】項的警示缺陷及責任主體分析
王欣,宋民憲
近年來,隨著《侵權責任法》的建立,公眾越來越關注藥品侵權責任相關問題的研究,由產品責任制度中產品缺陷結合藥品特性得出的藥品缺陷應運而生。據統計,我國約有4億兒童,其中患病兒童的比例約占患病人口總數的20%[1],表明兒童用藥需求量巨大。近年來兒童用藥安全越來越受到重視,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指出,全球的患者有1/3是死于不合理用藥,而不是疾病本身[2]。目前,對于兒科的研究僅著眼于現狀的探討、處方點評、說明書分析等方式,而對于藥品說明書存在問題的研究少之甚少,而兒童非處方藥品說明書存在較多的不合理之處,“用法用量”就是其中較為嚴重的問題之一。因此,筆者在此僅針對非處方藥藥品說明書【用法用量】項下的部分問題進行簡單分析研究。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6年頒布的《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指出,藥品說明書是指藥品生產企業印制并提供的,包含藥理學、毒理學、藥效學、醫學等藥品安全性、有效性的重要科學數據、結論和信息,用以指導臨床正確使用藥品的技術性資料。藥品說明書是醫師在選擇用藥時重要的參考依據,是指導藥師審方發藥的參考依據,是患者使用藥品的依據。《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非處方藥”(簡稱OTC)是指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公布的,不需要憑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處方,消費者可以自行判斷、購買和使用的藥品。而《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也有規定,“消費者有權自主選購非處方藥,并須按非處方藥標簽和說明書所示內容使用”。非處方藥雖然是經過醫藥學專家的嚴格遴選,并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較為安全的藥品,但它們仍然是藥品,安全也是相對而言的,其作用對象大多不具備專業醫學知識,因此,正確撰寫非處方藥品說明書對公眾健康和指導正確合理用藥具有重要意義。
“用法”就是指藥物的給藥方式或方法,如口服、直腸給藥、滴鼻等。“用量”就是指藥物的給藥劑量,或用藥的多少。兒科非處方藥品說明書中的【用法用量】就是指導患兒用藥的方法和劑量,是決定藥品安全、合理、有效使用的關鍵之一。
1 數據分析
筆者利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網站數據查詢欄下搜索出的兒科非處方藥藥品說明書333個(169個化學藥和164個中成藥)中存在的不合理之處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
1.1 用法
1.1.1 頓服 阿苯達唑相關劑型的藥品說明書中【用法用量】項下均標注了“頓服”這一服藥頻率詞,就專業醫藥學人員而言,尚且理解“頓服”的含義,那對于沒有醫藥專業常識的消費者,是否清楚?
調查研究發現,有的消費者認為“頓服”就是“吃飯的時候服用,這樣藥效果好,容易和飯一起消化。”還有的消費者認為“只要吃飯了,就要吃藥,一天三頓每頓都要吃。”也有認為是“一頓服用量”,絕大多數的消費者對其含義一知半解。
“頓服”一詞來源于中醫,語出漢?張仲景《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簡明中醫辭典》謂“頓服”是“指一次較快地將藥物服完。”而在西醫中所說的頓服則是指將一天的藥量一次服下,以達到最佳的效果。通常只有突發疾患,病情危急的情況下,需要集中藥力,速挽殘局來遏制病情的蔓延與發展時,才采用頓服藥物的方式,但此舉只能起到急挫病勢的作用,如若要治愈此病,用藥后應依據病情追加藥力并酌情減量。兒童生理特點主要表現為臟腑嬌嫩、形氣未充、生機蓬勃、發育迅速,病理特點為易發病、易變化、易康復,就是說,兒科治療與成人相比,更要強調及時、正確和謹慎。兒童對藥物劑量差異反應靈敏,用藥時必須根據兒童個體體質和疾病輕重區別對待,且中病即止。阿苯達唑作為非處方藥,患兒在首次服藥后的用藥情況仍主要是由其監護人決定,而其監護人在該藥藥品說明書的指導下極有可能連續兩次或兩次以上服用同等劑量,就此是否會因用藥過猛對患兒產生不良反應或副作用不得而知。
1.1.2 服藥方式 在333個藥品中,除開33個外用制劑,僅有79個藥品(占口服制劑26.33%)的用法描述為“咀嚼后服用或用溫水溶解后服用”、“服藥時可倒出藥粉加入少量溫開水或奶液服用”、“將軟囊滴嘴開口后,內容物滴入嬰兒口中;有吞服能力的兒童、孕婦及乳母可直接吞服”、“嬰幼兒可直接嚼服,或碾碎后溶于溫熱牛奶中沖服”、“用刻度吸管吸取后滴入口中,或放入溫開水、牛奶、果汁等飲料中搖勻后服用”、“用40℃以下溫開水或牛奶沖服,也可直接服用。”等語言,而其余73.67%的口服制劑均簡單描述為“口服”。試問,“口服”是直接將藥干咽服下,還是用涼開水、溫水、開水送服。對于沒有吞咽能力的兒童,諸如片劑、膠囊劑型,兒童的服藥順應性極差,通常監護人都會將其碾碎、咀嚼后服下,或將膠囊內容物取出服下,除此之外,對于藥味稍重的藥,監護人會讓兒童將藥用牛奶、果汁、汽水等飲料送服,其服藥方式亦是口服,但其藥的吸收作用部位、代謝途徑、藥品成分與飲料間的相互作用等因素是否會影響藥效,甚至是發生不良反應就不得而知。
衛生部辦公廳2011年8月《關于加強孕產婦及兒童臨床用藥管理的通知》中規定兒童藥物治療藥嚴格掌握適應證,除成人用藥原則外,必須嚴格掌握兒童用藥的藥物選擇、給藥方法、劑量計算、藥物不良反應及禁忌證等,避免或減少不良反應和藥源性損害。
1.2 用量
1.2.1 生長期 小兒維生素咀嚼片的藥品說明書中【用法用量】為:“生長期兒童一日1片,咀嚼后咽下。”何為“生長期”?
中醫兒科學中,將整個小兒時期劃分為7個階段,分別是胎兒期(男女生殖之精相合而受孕,直至分娩斷臍)、新生兒期(出生后臍帶結扎開始至生后滿28天)、嬰兒期(出生28天后至1周歲)、幼兒期(1周歲后至3周歲)、學齡前期(3周歲到7周歲,也稱幼童期)、學齡期(女為7周歲到12歲,男為7周歲到13歲)、青春期(女12歲到18歲,男13歲到18歲)。《WHO兒童標準處方集》規定新生兒為0~28天,嬰兒為1~12個月,兒童為1~12歲;《兒童藥代動力學研究基本要點》規定新生兒為0~1個月,嬰兒為1個月~2歲,兒童為2~12歲。
然而,無論基于何種劃分標準,均無從得知“生長期”這一詞所概述的具體年齡段,詞典里解釋“生長期”為作物可能生長的時期或作物從播種到成熟的時期。那對于人而言,“生長期”就應該是指受精卵生長到兒童成熟時期或小兒出生后到成熟時期。傳統兒科服務的對象限于14歲以下的兒童。2002年在北京召開的第23屆國際兒科大會,明確將兒科服務的對象認定為18歲以下的兒童,明確兒科學的研究對象為自胎兒到青春期的兒童。那是否可以就此認定“生長期”即是指胎兒到青春期的兒童。
以上對于兒童年齡段的劃分均是專業知識限定,當藥品說明書的對象為非醫藥專業患者或患兒監護人時,怎能使其準確掌握用藥劑量。通常兒童藥品說明書上是用“1~3歲、4~6歲、7~9歲、10~12歲”這一簡單明了的表述來區分年齡段,方便患者或患兒監護人針對不同年齡兒童用藥劑量的理解。
1.2.2 服藥量劃分依據 在樣本333個藥品中,占68.47%的藥品(其中化學藥品占64.50%,中成藥占72.56%)是依據年齡段結合體重來劃分用藥劑量,如“1~3歲,10~15 kg;4~6歲,16~21 kg;7~9歲,22~27 kg;10~12歲,28~32 kg”,將年齡和體重并放一起,是為了更好的規范用藥劑量,但當患者或患兒監護人面對病人的實際情況與年齡分段的體重不符合時,應該遵循何者?
而根據兒科教材及相關用藥指導得知,兒童用藥劑量的確定方法主要是四種:根據體重、年齡、體表面積或者由成人劑量折算計算。但根據體重計算劑量,對于體重過重兒,劑量會偏大;根據年齡計算的方法計算過程太過復雜,很少被采用;按照體表面積計算方式不適宜大于30公斤以上的小兒,因為對于10歲以上的兒童,每增加體重5公斤,增加體表面積0.1 m2,如30公斤=1.15 m2,35公斤=1.25 m2,50公斤=1.55 m2,70公斤=1.73 m2,如此算來,體重超過50公斤時,則每增加體重10公斤,增加體表面積0.1 m2;而按成人劑量表(表1)折算可能劑量會偏小,但相對較安全,可供參考。

表1 成人劑量折算表
1.2.3 療程 在收集的333個非處方藥品中,僅健兒糖漿、兒脾醒顆粒、兒瀉康貼膜、兒瀉停顆粒、小兒厭食口服液、小兒秘通口服液、小兒健脾口服液、小兒宣肺止咳顆粒、兒康寧糖漿(2)共10個藥品品種有敘述服用療程。
對于其余非處方藥品,在久服不愈后,應當采取換藥服用還是及時就醫?對于含有特殊毒性藥味的藥品,久服是否會產生蓄積性毒性,損害患者機體健康。
我國藥品說明書相關規定指出,應當詳細列出該藥品的用藥方法,準確列出用藥的劑量、計量方法、用藥次數以及療程期限,并應當特別注意與規格的關系。
2 藥品缺陷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4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及第122條的規定,產品責任屬于法律有規定的需要承擔無過錯責任的特殊情況之一,即產品生產者應對產品缺陷對他人造成的損害承擔無過錯責任。藥品作為一種特殊的產品,在其生產過程及銷售和使用過程中都必須確保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藥品缺陷責任同樣是一種無過錯責任。
警示缺陷是指藥品生產者、銷售者未對藥品的危險性和正確使用作出適當警告和說明,導致藥品使用中存在不合理危險[3],是藥品缺陷的類型之一。藥品的警示具有兩方面的基本作用:一是指示用途,即通過說明藥品的基本情況,包括成分、適應癥、用法用量等,指導患者合理用藥;二是警告用途,即告知藥品存在的危險、不當使用時可能招致的損害以及危險的防免。警示事項不全或有誤,均屬警示缺陷[3]。而【用法用量】項下內容與指示用途相關。
兒科OTC藥品說明書的作用對象除了是醫師、藥師及醫藥相關人員外,還有患者或患兒監護人等,而“頓服”、“生長期”等詞專業性較強或意思模糊,讓公眾如何正確理解其含義并合理用藥。我國《新藥審批辦法》和《藥品管理法》對藥品說明書的撰寫都有相關規定,但均不曾提到專業性較強、詞義模糊的詞語不能用,因此,上述用語并不違反相關使用規定。但《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及《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中均有規定,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的文字表述應當科學、規范、準確,非處方藥說明書還應當使用容易理解的文字表述,以便患者自行判斷、選擇和使用。在美國Suter v.San Angelo Foundry & Mach.Co.案中,法院認為,“一個產品會由于指示不充分而成為不安全產品”。“制造者對其所銷售的產品負有一些說明的義務。只有一件產品附帶有適當的能夠使得消費者在使用該產品時具有合理的安全性的信息‘軟件’,才能認為該產品是‘合理’安全(或非‘缺陷’)的。”兒科OTC藥是為大眾所消費、使用的,由于沒有專業中間人士的指導,對其標簽和說明書的要求相對于處方藥來說,應該更加嚴格,其說明書中的警示內容應為社會上不具專業知識的一般人所能引起注意、知曉、理解。因此,上述“頓服”“生長期”等專業用語模糊不清是相關藥品說明書存在警示缺陷的不合理危險。
3 警示缺陷相關責任主體
3.1 藥品生產企業
2006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新修訂的《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開始施行,要求藥品生產企業要對說明書的正確性與準確性負責,為因安全性、有效性導致的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依據《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九條規定,因藥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藥品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0條至第42條,明確規定了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造成消費者人身傷害、死亡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藥品生產者位居藥品產銷流程的首位,是藥品說明書用法用量制定控制源,況且,藥品生產者在藥品經營過程中有獲得利益,應當承擔該藥品造成的損害責任,因此,只要藥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除了法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責任事由外,藥品生產者都應當為該藥品侵權的主要責任主體。然而藥品監管部門批準的藥品說明書內容,只是為藥品生產者設定一個最低強制披露義務的下限,出于保護公眾健康和指導正確合理用藥的目的,藥品生產者可以主動提出在藥品說明書加注監管機構批準內容之外的警示語。美國非那根案例中,最高院根據FDA的“有效改變規則”(簡稱CBE規則)——“允許藥品制造商在得到FDA預先的批準前改變其產品標簽以增加或加強產品的警示,只要其事后提交修改的警示以供審查或批準”——判定惠氏公司獲得FDA批準的藥品標簽違反了藥品的警示義務,存在過失,不得對抗原告的訴請。MacDonald v.Ortho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案中,馬薩諸塞高等法院在上訴審中判決原告勝訴的理由之一,認為Ortho制藥公司雖然依照FDA法規對其藥品作出了警示,但其警示語中缺少通俗易懂的“中風”一詞,而是使用“腦細胞組織受到非正常血液凝結損害”的說法,無疑會減輕對使用者的警覺力度,也會讓普通消費者無法清楚了解危險的性質[4]。藥品說明書的印制內容獲得藥品監管部門的批準,并不能作為訴訟中不構成警示缺陷的抗辯事由。依照《侵權責任法》按照產品責任承擔侵權責任,符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藥品生產監管規定的只能免除行政責任。如【用法用量】項警示內容的用語本應在藥品生產者的能力范圍內被控制的缺陷,造成受害人損害事實的,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
3.2 藥品銷售者
藥品銷售者(指藥品生產者以外的其他藥品銷售者)屬于制造與行銷完整事業體系的組成部分,具有盈利行為,其藥師對處方的審核、銷售者對非處方藥的銷售含有對藥品用法用量的掌控或囑咐行為。《藥品管理法》第十九條指出,“藥品經營企業銷售藥品必須準確無誤,并正確說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項。”因此,消費者通過藥房(店)購買藥品時,店員(或駐店藥師)有責任主動向消費者解釋該藥品說明書上的專業術語并告之準確的用法用量,否則,受害人因此造成損害,可以向藥品經營企業要求賠償。司法實踐“亮菌甲素注射液受害人訴齊齊哈爾第二制藥有限公司、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廣東醫藥保健品有限公司、廣州金蘅源醫藥貿易有限公司損害賠償案”、“王小華訴翁牛特旗醫藥支公司龍膽瀉肝丸致害案”中,法院均判決藥品銷售者對受害人承擔無過錯責任[3]。我國《產品質量法》與《侵權責任法》第43條均有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受害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者要求賠償。屬于產品的生產者的責任,產品的銷售者賠償的,產品的銷售者有權向產品的生產者追償。屬于產品的銷售者的責任,產品的生產者賠償的,產品的生產者有權向產品的銷售者追償。因此,藥品經營者對受害人承擔無過錯責任,而藥品生產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不真正連帶責任。此法條增強了經營者維護消費者用藥安全的意識;使受害人能夠及時、有效的獲得賠償;同時也保障了生產者與經營者中,無責任方的權益。
3.3 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在藥品的流動過程中,扮演了同時包含有銷售者和使用者的重要角色。《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規定》指出,醫療機構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嚴格按照《藥品管理法》、《處方管理辦法》等法律規章制度審核、調劑處方,并告知患者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項。醫療機構除了向患者提供藥品(包括處方藥和非處方藥),也指導藥品的使用,其中就包括非處方藥用法用量的解釋與指導。《藥品管理法》93條將醫療機構與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一并列入藥品致害的賠償責任主體;《侵權責任法》59條亦明確規定了醫療機構對于藥品致害的賠償責任,因藥品缺陷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后,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追償。在醫療機構與藥品相關的業務多、可能存在用藥醫療事故因素的影響下,醫療機構不同性質的侵權行為所承擔的賠償責任不同。但筆者認為,醫療機構對患者承擔的義務應比銷售者對消費者承擔的義務更重。因為,在消費者選擇購買非處方藥的過程中,消費者的主要行為是收款供貨,而在醫療活動中,由于醫學知識的缺乏,患者在選擇使用醫療產品時,是無法行使其選擇權的,而是有醫療機構代為行使的,醫療機構憑借其專業知識、職業道德和臨床經驗為患者選取使用醫療產品,醫療機構應有義務保障患者在使用其選擇的醫療產品后不會出現生命健康的損害。而法律尚且對銷售者追究無過錯責任,對醫療機構則更應追求其無過錯責任。
《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及《中成藥非處方藥說明書規范細則》中明確規定,藥品說明書是經過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審批核準的,藥品說明書的具體格式、內容和書寫要求由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并發布。若藥品說明書中的警示內容存在缺陷,國家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應在其職責范圍內予以糾正或禁止。然而,該行政部門制定的藥品說明書內容不合理,長時間未發現、糾正缺陷,導致依此標準制定的藥品存在不合理危險,而該藥品對受害人造成損害事實時,應承擔行政不作為責任(行政不作為就是指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有積極實施行政行為的職責和義務,應當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職責的狀態)。藥品相關監管部門怠于行使職權使得缺陷藥品流通與市場并導致社會個體利益損害的,根據《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民法通則》等法律的規定,受害人有權主張賠償。外國在這方面已經產生了一些判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亞急性脊椎視覺神經癥系列案判決。9個地方法院對此案的判決結果都承認了國家的相關責任[5],如金澤地方法院的依據:1)醫藥品本質具有危險性,厚生省與藥品和準時,須對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進行審核,而本案中,厚生大臣在批準藥品制造后,懈怠對Chinoform進行安全確認[6];2)藥品收載后,國家的安全確保義務,并不因此而削減,該案中,厚生省對該藥物安全存有疑問,但未立即為藥局方之變更,從而應承擔不作為責任。目前,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就產品侵權案件對藥品監管部門的失職或違法行駛職權的行為,只規定了相關的刑事、行政責任,而沒有明確國家賠償責任。國外的成功案例即可成為今后相關案件判決的有力依據。
4 結語
我國對藥品實行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制度,處方藥的使用尚有醫生、藥師的特別指導,而非處方用藥的普及,使得患兒監護人給患兒自用藥物的現象比較普遍,而患兒監護人的醫藥專業知識有限,以及現有兒科藥物劑型的缺乏或規格不合理,加之患兒監護人治病心切,盲目加大劑量或延長療程,往往導致用藥不當,對患兒造成損害。因此,與藥品相關的部門或企業均應在各自職責范圍內依法嚴格履行義務,減少或避免患兒用藥損害的發生。
藥品生產者,作為藥品專家,履行警示行為應該充分、持續和及時。警示缺陷的存在,不僅僅可能危害到患者,也可能給藥品生產者自己帶來不可預計的財產和名譽損失。藥品生產者科學、正確的撰寫藥品說明書,盡可能的保障了患者的用藥安全,同時,合理規避了相關侵權責任。
然而對于非處方藥品的使用,患者本人或患兒監護人的主觀意識也是安全用藥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我國首例因服用藥物致人窒息死亡案例——成都市溫江區一女子因服用“桂枝茯苓丸”致咽喉部堵塞引起窒息死亡案中,法院認為受害人李秋華服用被告楊文水制藥公司生產的“坤舒”牌“桂枝茯苓丸”時已滿34周歲,屬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直徑約為1.6 厘米,外形呈軟性狀的大蜜丸進行服用時,應當預見到服用藥丸方法不當可能存在的危險,并且這種危險是其自身可以輕易克服和排除的,受害人李秋華對藥丸服食方法的不當是導致藥品存在的潛在的不合理危險轉化為窒息死亡損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據此,受害人李秋華存在主要過錯,應當自行承擔主要民事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不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的規定,綜合全案的具體情況,成都市溫江區人民法院認定本案因人身損害產生的損失,由原告自行承擔 80% 的責任,被告楊文水制藥公司承擔 20%的賠償責任。此案例充分說明了患者或患兒監護人對于無醫生指導的非處方藥品的使用應隨時具備安全用藥意識,否則也會對造成的損害負相應的責任。
關于對用法用量的規定是中成藥與化學藥相比,中成藥藥品標準增加的內容之一。藥品說明書標準是基于臨床試驗或長期經驗歸納得出的,而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能在新技術、新方法的指導下發現藥物新作用或新不良反應而使得藥品說明書具有滯后性;不良反應相關監測部門的不良反應報告上報的不及時又使得藥品說明書具有信息有限性,建議對【用法用量】項的內容不作限制性規定,依藥品生產者根據研發藥物當時的實際科學技術研究所得信息為準,促進藥物研究人員對藥物的不斷研發和改進,為患者提供更安全、可靠、有效的藥品。
藥品監管部門行政人員切實履行職責義務,增強責任心和為人民服務意識,完善藥品法律體系中尚不健全的條款,使我國的醫藥事業穩定、健康發展。
[1] 馮紅云,劉翠麗,侯永芳.淺析我國兒童藥品不良反應/事件現狀[J].中國藥物警戒,2011,(8):483.
[2] 魏令敏.兒科合理用藥的探討[J].中外醫療,2011,(22):186.
[3] 陳璐.藥品侵權責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152.
[4] MacDona v.Ortho Pharmaceutical Corp.394Mass.131 ,475N.E.2d65,cert,denied, 4744U.S.920,106S.ct.250,88L.E.Ed.2d 258(1985).
[5] 植木折[日].醫療法律學[M].冷羅生,陶蕓,江濤,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 于敏.日本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