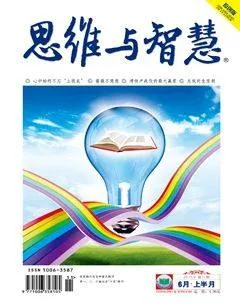薔薇不愿意
涼月滿天
“佩帶花環的阿波羅,向亞伯拉罕的聾耳邊吟唱,我心里有猛虎在細嗅著薔薇。”
好詩。
可是一只猛虎嗅薔薇,你曉得人家薔薇樂意不樂意。
好比我們賞花,撅著屁股,湊得近近的,鼻子都要杵進花心里了,眼睫毛都要把嬌嫩的花瓣扎出一排洞眼。
又或者伸出柔荑,輕輕掐下一朵花來——
對人來說,這叫風雅。
對花來說,這是個什么玩意!這么怪,大腳板把地板跺得咚咚響,嚇破了偶們的小心臟;鼻子長得像白毛象,還伸進來亂嗅亂拱,鼻毛都能數得清,嘔——
眼睛上還長一排鐵刷子,喂,別湊這么近!
啊!一朵好姐妹被這只怪物用長滿體毛的爪子把脖子擰斷啦,把尸體還給戴到它自己的頭上,嗚哇哇——
瞧。
我們眼里的螞蟻,多么微乎其微,對于一朵花也是一只扛著大鍘刀的惡狼,它們鉆進它的花芯,噬咬它的花瓣,或者不顧它是疼還是癢,徑自排著隊浩浩蕩蕩爬過它的身體。它也不能動,所以只能既恐懼又惡心。
一頭猛虎細嗅薔薇,從老虎的角度,也許它的心里有朦朦朧朧的一點什么感覺,但是不耐細追尋,一追尋就消失了;從人的角度,這是詩意的,值得贊嘆和銘記,帶著禪味。而從一朵薔薇的角度呢?這家伙那么大的嘴巴,會不會吃了它?這家伙整天吃肉,口氣好臭,要熏得它背過氣去。我們眼中所見的無比違和又無比和諧的一幕,宇宙間漂亮的一景,如果從薔薇的眼中看出去,是可怕的滅頂之災。
還有,你知道一棵樹拔出來,再重新栽回土里去,為什么會葉片發蔫,好長時間恢復不了元氣?
不是因為損傷了根脈。據說,把樹從土里拔出來,露出根,那是和人類的被剝光了衣服裸奔一個等級的行為,把你扒得光溜溜的,讓人看個飽,然后再給你解開,穿上衣裳,讓你繼續生活,不羞死才怪。
當然,當春風拂面,百花擠擠挨挨,香氣縈繞,天頂一片湛藍,太陽發著金光,或是細雨淅瀝而下,這些花啊樹啊是多么地愜意。好像一切都圍著它起舞,一切都為它謀篇布局,陽光是為它照耀,青草是為它生長,蜂蝶是為它營營繞繞,流水潺潺,其實是為它奏響的愛的鳴琴……
對一朵花來說,這一切都是圍繞著它發生,我們是它生命中的惡棍,它的生命中還有那么多、那么多專為它存在的喜悅。它才是世界的中心。
每朵花都是世界的中心。
每只貓、每只狗、每只蚊、每只蠅。
一塊石頭也是世界的中心。
誰說石頭沒有生命的?你問問量子物理學家,它在和它的周圍的環境,質換著怎樣的粒子,而它的內里,是又有著多么活躍的粒子的運動。對于它來說,即使是風燭殘年的老人,舉動也像是在快放電影,就那樣滑稽地飛速地前進、倒退、說話,嘴巴動起來快得無與倫比,一切都滑稽得不行。而它們睡一覺醒來,我們早已經成了灰塵。
我們就算站在它的旁邊,一動不動幾十年、上百年,對于它們來說,也不過就是我們的身邊,有一只螞蟻偶爾停留了片刻。至于片刻之后,螞蟻是生是死,我們不關心,而我們的生與死,石頭也不會關心。
所以,你的眼里看出去的,不是世界的中心,那只不過是你的世界。我們看一個瘋子傻呵呵地滿街亂跑,可是對于這個快樂的瘋子來說,我們才是表情木然、心思呆滯的瘋子。
我們不認識這個世界。
我們也不認識自己。
當年八國聯軍進逼北京,慈禧西逃,隨身兩個丫頭一邊吃苦受罪伏侍主子,一邊說閑話,說到當初看戲看到的陳圓圓的故事,城破被俘,六宮的人被趕著迎接新主子,“九殿咚咚鳴戰鼓,萬朵花迎一只虎”。
老虎是開心了,那一萬朵花開不開心?
當然這話跟老虎說不通,因為老虎不識字,人形的老虎也是莽夫、粗漢。可是我們識字。所以我們不要搞這種讓花惡心的事。
當你想要褻玩一朵花的時候,也要先想想它開心不開心。
所以還是不要一廂情愿地去歌詠一頭猛虎細嗅薔薇,因為薔薇不愿意。
(編輯 慕容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