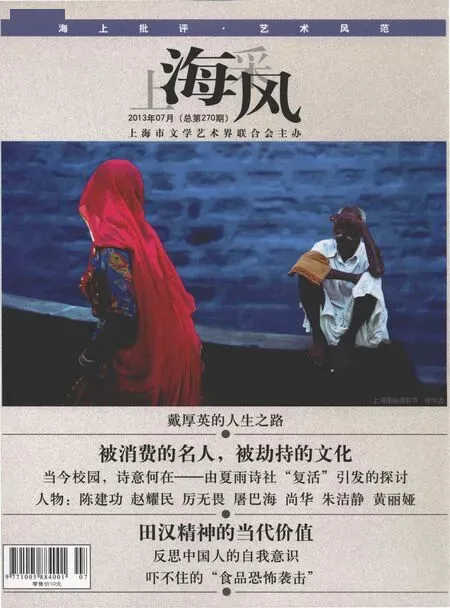陳建功:“平民主席”的自由談與兼容論
文/本刊記者 胡凌虹

文學界,盛傳陳建功是“平民主席”,這點在我第一次發短信聯系他時就見識了。五一節前,受邀去北京參加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第二屆施耐庵文學獎新聞發布會,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參會并做主題發言,于是我便提前跟他約專訪,他爽快地答應了,并在短信尾處特地加上“不勞再復”。之后聯系的短信中,“不用復”也是必有的“手頭禪”, 讓人不由感嘆他的善解人意。
北京的早晨,風很大,有些涼意,原本約了在館長室采訪,在路上我收到短信,告知因有事采訪地換到多功能廳。走進文學館時,忽然被門衛叫住:你是胡記者嗎?當我有些發懵地點頭時,門衛禮貌地說道:“陳館長剛進去,特地關照我告訴您,他去多功能廳了。”小細節處盡顯陳建功的考慮周到悉心,讓人感到一陣暖意。
離活動舉行還有一個多小時,會場空空蕩蕩,便在這里開始了采訪。陳建功很善談,如同鄰家大叔般和藹親切、毫不造作,而且說話坦率,一點也不打官場的“太極”。只是半個多小時過后,有外地專家到場,他們與陳建功打起了招呼,我心中不禁泛起咕嚕:糟糕,朋友間總要寒暄一下,加上之后陸續到場的作家、評論家,估計采訪只有不斷被打擾的份兒了。不料,三言兩語過后,陳建功便向他的朋友介紹:“這是來自《上海采風》雜志的記者,正在采訪我。”然后溫和地對我說:“我們換個地方吧”。隨即帶我來到一旁安靜的小型會議室,讓我感受到他對于采訪的認真與尊重。
陳建功衣著樸實,笑容可掬,像個待人謙和的“老同志”,倒不像個身居“要職”的官員,采訪中,我越來越感受到這點,而這方面其實早已聽到過不少坊間的傳說:
有一次,陳建功去見一位未曾謀面的外地作者,不料對方直沖著更顯得儀表堂堂的司機伸出了熱情的雙手,喊著“建功主席”,嚇得秘書、司機趕忙往后退。陳建功卻一點也不尷尬,反而笑著自嘲:“有人說我們長得有點像哎”。
有一年,《文藝報》請領導為報社寫新年寄語,當陳建功的“手書”傳真過來時,編輯們都傻眼了,因為上面寫的是:“我的手機號是1360×××××××,有事打電話。”“文化圈里,大家寫新年賀詞,可以理解,但我對這種形式不感興趣,還是來點實在的,倒也出新了。”提起這事時,陳建功爽朗又憨厚地笑著。多年來,陳建功的手機號一直沒換過,凡事找他無不回復。我有些疑惑地問他:“你已經夠忙了,不怕被人打擾,更添負擔嗎?”他坦言:“小事一般不會找我,找我的肯定是他有大事、急事,這個時候,肯定要幫忙啊。”還真有不少人打電話,比如有些并不熟的作家打電話來讓他幫忙聯系北京的名醫,陳建功立馬牽線搭橋,還親自送他們去醫院。
隨著采訪的深入,我發現陳建功不僅沒有官腔,甚至連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都沒有,而且這種姿態不是裝出來的,是他由衷地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這也跟他的經歷息息相關。
陳建功生于1949年,8歲時被父母親從廣西北海家鄉接到北京。1966年“文革”開始,這一年的陳建功是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的學生。當時,高考取消了,陳建功去了京西一個叫木城澗的煤礦當了一名巖石掘進工,一呆就是10年。井下生活非常艱辛,陳建功還不慎受了傷,腰被撞折。但是出身書香門第的他一邊挖煤,一邊還堅持偷偷讀書。一天,下夜班時陳建功不由得背起曹禺《日出》里陳白露的一句臺詞:“太陽出來了,黑夜即將過去,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結果正巧被治保委員聽到,陳建功被打成“攻擊‘紅太陽’”的“反革命嫌疑犯”。
經歷了一段惶惶不可終日的被批判的時光,一天,礦區的領導忽然找上門來,問陳建功能不能給寫一段詩,原來北京要搞一個勞模賽詩會。于是陳建功趕寫了一首詩,隨后,這首詩由礦上的勞動模范在人民大會堂朗讀。第二天,陳建功的“處女作”登在《北京日報》上,不過署的卻是那位勞模的名字。之后,陳建功繼續寫作,又發表了幾篇作品,想的是扎根礦山,走“工農兵創作道路”,當一名“工人作家”。1977年10月,各大媒體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在母親的堅持下,陳建功被“逼”著乘上了高考恢復后的首班車。1978年年初,陳建功考入了北大,豐富的學習生活使他對文學的理解日漸深刻,并開始自我批判。“在北大時,我寫了一篇反省文章,回想起礦上,我雖被調去寫作,稍舒適了些,但是處于很尷尬的境地,那時候的我,一方面受社會擠壓,一方面又拿起筆歌頌那個擠壓你的時代;一方面對“四人幫”推行的文藝路線產生深深懷疑,一方面又要尋找理論來證實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被社會潮流打得暈頭轉向,一方面又想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這么一種心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兩重性。”陳建功說道。待人溫和的他對自己批判起來卻是毫不留情。
在北大學習的第一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看中了陳建功與林洪桐合作編寫的一個電影劇本,還準備把這劇本列為向建國30周年獻禮的項目,但需要做一些修改。陳建功請假到了上海,一日在街頭買了張《文匯報》,看到了發表在上面的盧新華的《傷痕》,看完后,陳建功很激動,他意識到新的時代到來了,文學敢于直面現實的時代到來了,文學不應該再成為簡單的獻媚邀寵的工具。回去后陳建功就跟劇組說不改了。“他們很驚訝,不能理解,已經作為獻禮片了,改一稿就有稿費了。我說不行,電影劇本說的都是粉飾太平的話,我不能再容忍這種文藝觀。”
和許多新時期作家們一樣,他最先敏銳地感覺到,時代與文學,都面臨著陵谷之變。回到北大后的陳建功開始直抒心聲,后來就有了《蓋棺》《前科》《丹鳳眼》《轆轤把胡同9號》《鬈毛》《放生》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曾多次獲全國文學獎,并被譯成英、法、日、捷、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小說人物的原型都是陳建功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他以深邃的思考,用樸素生動的語言,帶著悲憫、自嘲的眼光,展開了一幅幅市井小民的生活圖景。在陳建功的眼里,“‘卑賤者更聰明’或許不無道理”!“一些人一旦成了‘肉食者’,很難逃脫‘肉食者鄙’的境遇!他就停滯在那兒,永遠對別人耳提面命。其實真正值得敬畏的,倒很可能是引車賣漿者流,是那些永遠在創造和思考的人。”
1995年3月,陳建功調中國作協工作。之后,先后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長、創作研究部主任、書記處書記和黨組成員,但在一些作家眼里,他這個“官”,依然保持著平民的底色。在出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后,他也一直在拉近文學館與廣大作家、普通百姓的距離。例如,他曾倡辦“此物最堪思”為主題的“作家友情展”,號召作家把含有親情友情故事的、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捐贈或暫借給文學館。于是,繡著“丁玲不死”的錦旗,世界短跑名將劉易斯贈給北京作家史鐵生的一雙跑鞋,王安憶夫婦送給宗璞的圍巾和CD等等,紛紛與廣大觀眾見面。
“我本來就是工人,即便是現在我到底層,也能混成一片,跟他們一起‘大碗篩酒大塊吃肉’。當然到了高層,我也能‘道貌岸然’。”他哈哈大笑著,坦率、爽朗,又有一種自嘲的幽默。在工作、生活中,陳建功信奉的是 “無累”,不為“官位”所累、不為聲名所累、不為金錢所累;在創作方面,他又是斤斤計較、愛“折騰”的,一直保持著獨立的內心和寫作姿態。1995年后他寫了兩個電視劇本、一些回憶性的小文章,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說,已經許久不見蹤跡。“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都不能成為作品不出來的借口,我還要再努力。”事實上,陳建功透露,已經寫好了一個中篇,正在寫一兩個長篇,只是未到拿出來的時候,對于寫作,他依然保持著深刻的自省力,充滿了激情與自信。
記者:
剛才你說到,在煤礦時寫作如同抓一根救命稻草,那么之后寫作對于你的意義有了怎樣的變化呢?陳建功:
后來成為我表達社會良知,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對弱者的同情、對人性復雜性的理解的一個重要途徑。我認為,世道人心的責任感是中國知識分子骨子里與生俱來的,因為中國文人有感時憂國的傳統,完全脫離政治是不現實的,所以現在“緊密切合現實”的說法不夠準確,其實都是貼近實際的,只是有些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有些人則是趨炎附勢,關注現實中的功利,是“使命感”遮掩下的瞞和騙!記者:
在你看來,一個寫作者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陳建功:
最重要的是人格的獨立,就是巴老所說的講真話,這也是很多作家所痛切呼吁的。“我手寫我口”,這些話一直在說,但是不是人人皆可口對著心?不少作家遭遇過文革中的狀態,被侮辱,被損害,其實是一種人格尊嚴的喪失。因此才有了毅然拋棄了外在的東西,進入了新的文學境界、人生境界。但是現在很多人沒有銘心刻骨的遭遇,他們不知道講真話、不做違心之論,對一個搞文化、搞學術的人是多么重要。我也不少接觸到一些青年,金錢、權勢又開始成為他們所信奉追求的東西,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由地思想,尊嚴地生活,真實地訴說,實際上比其他更加珍貴。記者:
直言心聲在你看來是最重要的,不過當你出任某個領導職務后,這方面是否會有沖突?為考慮方方面面,發言、寫評論以及創作時,是否會有所顧忌,無法像以前那樣自由表達?陳建功:
這個問題很好!國內有人出來針對一些現象振臂一呼,我對他們充滿敬意,但是我特殊的位置在這里,有時也許說的是對的,但是對整個局面未必有利。比如文學界在四次作代會以后,因為作家間政治的、藝術的歧見甚多,很有一些混亂。1986年開的第四次作代會,一直到1996年才開五代會。文學界有各種觀點,包括不同的立場、角度和藝術主張,怎么找到共識把大家團結在一起,推動文學的發展,這個事情不僅需要勇氣,而且也需要策略。我有自己的觀點主張,如果是一位普通作家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甚至不怕激怒不同觀點的人,但是作為負責人之一,你的“毫無顧忌”則將可能成為作家間戰火重燃的導火索。更何況所謂“不同的立場、角度和藝術主張”,其實并沒有那么嚴重。實踐證明,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共同目標下,大家還是坐到了一起。第二方面呢,1978年上大學以后,為人為文的觀念上有了根本轉變,記得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先生曾對我們說:第一,要有自己的觀點、見解,秉持獨立思考的精神;第二,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也許別人跟你的觀點不同,要維護別人講話的權利,還要看是否有道理,是否可汲取。總之,既要講獨立之精神,又要講兼容之精神,這才是比較好的為人為文的態度。記者:
那么具體到創作方面,你以前寫的很多的是底層人,處境的變化是否也會對寫作帶來一些影響?

陳建功:
處境的變化確實對舊有的立場是有一定影響的,從煤礦工人變成作家,這倒也罷了,后來又變成某一方面的領導。盡管我覺得自己還是自己,但是最近寫完一個中篇以后,我就發現,過去曾有的嬉笑怒罵,曾有的底層老百姓的口吻,如譏諷、自嘲,以及其他深層次的東西,失去了很多,這也是我為什么遲遲不把它拿出來的原因。我需要在風格問題上再想一想、改一改,至少要找回那種悲喜劇的感覺。記者:
有人說,陳建功當“官”了,中國作協多了個好領導,中國文壇失去了個好作家。對此,你怎么看?陳建功:
從1982年到1995年,我當了十幾年的專業作家,出任一個職務對我來說,是換種生活方式。1995年以前,我的接觸面主要是知識分子以及引車賣漿者流;1995年以后,我接觸到了文化部門某個領導層和組織者的生活,所積累的素材非常多,所領會的東西也很重要,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這些對于我來說都是生活的擴展。不過,另一方面呢,我的時間確實被大量占用。為今天的講話,昨晚我就寫到了11點鐘,實在太困就想去躺躺再寫。今天早上5點一醒,發現我的電腦還開著呢,趕緊爬起來去把講搞寫完。以前這樣的狀態經常出現,幾乎天天如此,因為不斷有研討會工作會,這種狼狽的狀態擠壓了大量的時間。是否是個“好領導”我不管,但是確實沒有拿出作品來。退休以后,我會把積累了的故事、人物,特別是某些所謂“官場”人物的微妙心態都寫出來。記者:
不擔心對號入座嗎?陳建功:
對號入座當然是不對的,因為小說畢竟是小說,但是真正好的小說,你把人物寫準確了,對號入座是沒有關系的,因為真正好的作家對所有的角色應該都是充滿同情的,都應該是設身處地去理解的,哪怕理解歪曲了,因為有這“同情”,大概就不會遭到誤解。這也是我的一個文學觀念。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里有句話,他說有些作家之所以膚淺,是因為他們把同情只放到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身上,他們不知道,即使是那些“剝削人壓迫人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當然夏先生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看,他們也都是迷途的羔羊啊。但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看,也未必說不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絕不那么單一,馬克思也從基督教中吸取了很多精華,包括解放全人類的思想,不能不說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傳承,或者說是與傳承同步的發展和創新。過去我們就犯過“肉體消滅”的錯誤,打倒地主,就要拿石頭把人家砸死,但是實際上打倒的應該是那種生產關系,剝削者所賴以剝削的制度,對個體,對“人”,是要充滿同情的,這樣才不會斗地主時走“肉體消滅”的極端,也不會發生這樣的疑問:我爺爺是地主,不像你們說的那么壞啊。在革命時代,或者說在狂飆突起的、你死我活的時代,過激的想法或者偏激的行動幾難避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把人,個體的人,他們和整個階級的關系,和無法避免的社會存在的關系鬧明白,不能簡單地把具體的人涂上“階級”的或“好人壞人”的臉譜。我們中國的文學,當然也有很多長處和特色,比如“感時憂國”的傳統,社會擔當的自覺,等等,但是比起西方文學來,在對人的認識方面還有很多膚淺的、臉譜化的東西。我們需要在這方面進一步突破。記者:
目前寫好的,以及正在寫的小說是關于什么方面的呢?陳建功:
沒拿出來的中篇是關于北京底層人群生活的,也是以前風格的延續,只不過比以前荒誕了些。我正在寫的長篇說的是改革開放以后一代青年人的生活道路。上個世紀80年代到今天,像我這一代人漸漸變老,這幾十年,我們的生活道路是很繽紛地展開的:有些人成為“民主斗士”,有的人則權柄赫赫,有的人變得沉潛而求實,有的人則激情不減。而這一切,又被市場經濟和商業時代的現實沖擊得亂七八糟,我認為這個過程很有趣。記者:
大家都對你的小說充滿期待,是否會有壓力?創作時是否會有年齡方面、靈感方面的擔憂?陳建功:
我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也承認自己所面臨的考驗。其實早就發現了,也承認了。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詩人,他們進入小說界,帶來很多語言的新意和直覺的快感,這已對我們這代小說家構成了威脅,形成了壓力。隨后發覺新人輩出,能人崛起,涌現的大作家太多了,但契訶夫說嘛,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權利。何況我輩也未必沒有我輩的優勢,就是對人生經驗的把握。閱歷帶來的對人生和人性的感悟,是不可替代的。靈感是不是消失了?也不見得,我現在一直在接觸底層老百姓,生活還是充滿新鮮感的,還能情趣盎然地描寫身邊的那些人、那些事,我還有這個自信。當然,能不能找回當初的藝術感覺,能不能對過去有所突破,能不能讓大家滿意,我不知道。但我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