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魔術(shù)的獨特魅力與發(fā)展之道
采編/紅 菱

舒 巧

周良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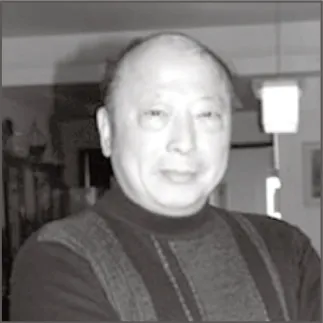
傅騰龍

陸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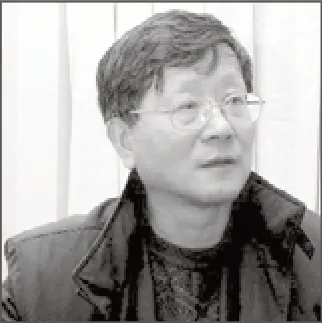
藍 凡

劉明亞
上海是名副其實的“魔術(shù)重鎮(zhèn)”,并以“海派魔術(shù)”聞名國內(nèi)外。海派魔術(shù)誕生于中國近代的上海,后因影響力大,又擴展到長三角一帶及更遠的地方。海派魔術(shù)對上海乃至中國的現(xiàn)代魔術(shù)發(fā)展有很大的影響,不僅把中國的魔術(shù)帶進了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舞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開創(chuàng)了魔術(shù)的新紀元。然而,新世紀以來,隨著北京、廣東魔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浙江、安徽省的快速趕超,海派魔術(shù)的發(fā)展相對滯后,面臨著不小的困境。
近日,上海雜協(xié)和文學院以《一壺魔術(shù)半世功·周良鐵》新書首發(fā)式為契機,舉辦了“海派魔術(shù)的傳承與發(fā)展”理論研討會,與會專家在肯定新書的同時,紛紛就海派魔術(shù)的形成、特點,海派魔術(shù)的理論建設(shè)以及未來發(fā)展走向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海派魔術(shù)”的形成與發(fā)展
周良鐵(上海雜協(xié)副主席、著名魔術(shù)師):海派雜技的概念應(yīng)該產(chǎn)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第二屆金獅獎在上海舉辦期間,以老團長王峰為首的領(lǐng)導(dǎo)班子正式定下來的。當時在南派、北派的爭議中,王峰提出了海派的觀念,其意義是重大的,也是非常睿智的。從此,與上海有關(guān)的雜技、魔術(shù),紛紛舉起海派的旗幟,用作品詮釋著內(nèi)涵與外延。我自認為是海派藝術(shù)的踐行者,2010年,被授予上海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海派魔術(shù)代表性傳承人”稱號。其實,我的實踐都是在上海雜技團前輩的影響下進行的。從1980年—1987年,在魔術(shù)上我是學習階段、舞臺實踐階段。1987年—1999年,是我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期,在領(lǐng)導(dǎo)、同仁等的幫助支持下,創(chuàng)作了《魔術(shù)師的約會》《變臉》《百鳥朝鳳》三個主要節(jié)目。之后,我把重心轉(zhuǎn)到培養(yǎng)學生、舉辦魔術(shù)大會上,使我比較全面地繼承海派魔術(shù)、探索中國魔術(shù)的改革。
傅騰龍(著名魔術(shù)師):
魔術(shù)藝術(shù)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特點,就是視覺藝術(shù),不靠語言。因此,每當社會發(fā)生變革時,也就是中外交流比較頻繁的時候,雜技、魔術(shù)總是當先。漢武帝時期,張騫帶回兩個外國魔術(shù)師;到了隋唐、兩宋,是魔術(shù)頻繁交流的時期。到了清朝末年,大體分為南北兩派。海派魔術(shù)的特點、風格,決定于地域性。但要說明的是,海派魔術(shù)不僅指上海,應(yīng)該包括長三角地區(qū)。海派魔術(shù)產(chǎn)生的原因在于:第一,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通商口岸打開,上海成了水陸交匯的大碼頭,各地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好的班子集中在上海。第二,一般來說,練把式的比較窮,搞魔術(shù)的比較富。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容易支撐魔術(shù),容易有人玩魔術(shù)。上海水陸碼頭,集中了很多非常優(yōu)秀的魔術(shù)師。滿清末年中國藝人出國表演,同時外國魔術(shù)團體來到中國,一般首先到上海。我認為“海派魔術(shù)”的形成和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76年—1949年。1876年,英國魔術(shù)師瓦納在上海圓明園路表演,這是清朝來的第一位魔術(shù)師。過去我們賣戲法是在街頭巷尾進行表演,這些外國魔術(shù)團帶來的是一個舞臺鏡框式的表演,里面形成了一種非常嚴格的模式,這種表演在當時整個上海是轟動甚至是瘋狂的。瓦納到中國表演之后引起了對魔術(shù)的觀賞熱潮。1894年,唐蕓洲出版《鵝幻匯編》,書里面記載了很多外國的魔術(shù),說明中國的魔術(shù)藝人已經(jīng)掌握了這些節(jié)目。應(yīng)該說,這是海派的開始。這個過程,持續(xù)了70年,一直到1949年。這當中,中外交流頻繁,上海地區(qū)魔術(shù)大家涌現(xiàn)非常多,其中有三大家值得我們研究,即莫悟奇先生,張慧沖先生,吳恩奇先生。
第二個階段:1949年—1979年,這個時期屬于大浪淘沙時期,以前在上海有多如牛毛的班子,經(jīng)過整頓后梳理了不少。那時候的魔術(shù)師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模仿外來的節(jié)目,而是改造外來節(jié)目并融合自己的創(chuàng)造和特點。這時候魔術(shù)創(chuàng)作受到一定導(dǎo)向性的影響,首先剔除了封建迷信、刺激感官這類的節(jié)目,產(chǎn)生了很多專題魔術(shù),擺脫了以前魔術(shù)一個節(jié)目連著一個沒有變化的演出形式,不管這些主題表現(xiàn)如何,有的是標簽式的,有的比較生硬,但朝著這個方向走,為中國魔術(shù)開辟了非常廣闊的道路。
第三個階段:1979年至今。1979年馬克·威爾遜到中國來演出,全國興起了魔術(shù)熱。又適逢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海派魔術(shù)迎來了機遇和挑戰(zhàn)并存的時期,海派魔術(shù)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這三十年來整個文化界的思路也非常的活躍,海派魔術(shù)再次繁榮,創(chuàng)作出了很多具有清新氣息、藝術(shù)和技術(shù)相結(jié)合的優(yōu)秀節(jié)目。
海派魔術(shù)的特有魅力
陸林森(傳記作者):
我是一個喜歡魔術(shù)的看客,魔術(shù)帶給我的不僅是感官上的刺激,也不僅是心靈上的愉悅和精神上的享受,而且更多的是新奇,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撲朔迷離感。正因為如此,魔術(shù)顯示了迷人之處,似乎是有一只無形的手,牽引著我和廣大魔術(shù)觀眾,共同探尋一個新奇的、充滿奇趣的世界。這個世界,真是太變幻莫測了。因為寫作《一壺魔術(shù)半世功·周良鐵》,使我有機會走近海上著名魔術(shù)師周良鐵老師,走近海派魔術(shù),并對海派魔術(shù)更多了些認識:一、海派魔術(shù)具有濃郁的上海本土特色,無論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張慧沖還是他的兒子張小沖,作為海派魔術(shù)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表演帶有濃郁的上海特點、上海風格和上海痕跡。表演大氣、華麗、典雅,給人感官上的強烈沖擊和視覺享受。海派魔術(shù)是中國魔術(shù)的一脈,與北方魔術(shù)相比,海派魔術(shù)的舞臺空間更大,演出更華麗。
二、海派魔術(shù)的平民化走向。海派魔術(shù)不是小眾藝術(shù),而是大眾藝術(shù)。上世紀,除了舞臺表演,大量魔術(shù)集中在工礦、企業(yè)和工人俱樂部,無論男女、不分老幼,百姓都喜歡觀賞,說明海派魔術(shù)走的是一條本土化的平民路線。
三、海派魔術(shù)海納百川、兼容并蓄,乃至中西貫通的特性,不僅體現(xiàn)了海派文化的藝術(shù)胸襟,也反映了海派文化的精氣神。當年的《炮打真人》,就體現(xiàn)了海派魔術(shù)地不分南北、藝不分中西,兼容并蓄的特征。以周良鐵為例,在20多年魔術(shù)表演中,他拜師學藝的名家大師、各地民間魔術(shù)藝人有六七十人,采各家之長,拓展了海派魔術(shù)的藝術(shù)觸角。
四、海派魔術(shù)的傳承關(guān)系和創(chuàng)新精神。海派魔術(shù),雖然相比火紅年代冷清了些,但并沒有沒落。事實上也不可能沒落。相反,既有傳承,也有創(chuàng)新。比如周良鐵的《變臉》《魔術(shù)師的約會》等,堪稱海派魔術(shù)創(chuàng)新之作。這一創(chuàng)新成果,證實海派魔術(shù)沒有從民眾的視野當中淡出,而是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發(fā)展。
傅騰龍:
海派魔術(shù)有以下這些特點:第一,具有海納百川的精神、風格常新。這和海派魔術(shù)的環(huán)境是分不開的。周良鐵師徒是海派魔術(shù)的主力軍,他說別人是十年打十口井,我是十年打一口井。說明他在海派魔術(shù)中求新求變的一個過程。第二、海派魔術(shù)豐滿厚重。如南派魔術(shù)的手法和北派不同,它是要與情感融合在一起的,像莫非仙的風格看似普通,但引人入勝。像鄧鳳鳴的《束指自由》道具雖然一般,但她有滿場飛的美譽,很會表演。還有像張慧沖的即興演出,華特生的閃電魔術(shù),鄧文慶平易之中見精神的魔術(shù)等,都反映了海派魔術(shù)的富厚。第三,海派魔術(shù)注重藝術(shù)包裝,如張慧沖的節(jié)目服裝美輪美奐,在國內(nèi)外取得很大的成功。海派魔術(shù)注重音樂、舞美并且道具制作非常精良,在很早之前就有編導(dǎo)了,在全國也是非常領(lǐng)先的。第四,基礎(chǔ)扎實,業(yè)余隊伍非常強大。為什么上海的群眾基礎(chǔ)非常好?上海注重文化,注重經(jīng)驗的總結(jié),重視理論,上海出版了不少魔術(shù)書,單我們傅家,我統(tǒng)計了一下,我們家有15個人參與過魔術(shù)的寫作,到現(xiàn)在出版了75本魔術(shù)雜技方面的著作,比較重要的一本是《中國雜技史》,這是中國第一本雜技史書。藍凡(上海雜協(xié)理事,文藝評論家):
魔術(shù)是一個外來詞,我們翻譯成魔術(shù),在國外有幾種含義,《哈利波特》中叫魔法。但是魔術(shù)作為一種藝術(shù),翻譯進來之后,在整個藝術(shù)當中是最為特殊的一種。有的時候,它作為游戲出現(xiàn)、作為娛樂出現(xiàn),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參照的對象來研究,這是非常大的悖論。魔術(shù)非常普及,但理論關(guān)注度非常低。在所有藝術(shù)樣式里面,只有魔術(shù)的理論是不成系統(tǒng)的。但實踐和理論應(yīng)是兩手抓的,因為越平民化越容易誤導(dǎo)。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魔術(shù)又是一個地區(q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象征。魔術(shù)越來越成為人類交際的手段,容易拉近關(guān)系。我認為,魔術(shù)最基本的屬性是表演藝術(shù)。作為一種表演藝術(shù),魔術(shù)有自己的特點。戲曲的假戲真做是表演給你看的,雜技,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但魔術(shù)就是告訴你,假的就是假的。我們只有知道了魔術(shù)自身的特性之后,才知道海派魔術(shù)的“海”字在什么地方。
和其他的表演藝術(shù)相比,魔術(shù)有四大特點:一是喜劇的形態(tài)。戲劇里有喜劇和悲劇,但魔術(shù)不可能有悲劇,就是喜劇形式。第二,魔術(shù)是依靠道具和人體相結(jié)合產(chǎn)生效果。第三,隨意性。不管是舞臺演出還是廣場演出,它的表演場所可大可小,可內(nèi)可外。第四,就是奇觀效果。《哈利波特》《阿凡達》等,那是大場面,高科技數(shù)字化形成的,所以現(xiàn)在的奇觀性、道具性也給魔術(shù)帶來不一樣的感覺。國外有靠高技術(shù)進行魔術(shù)表演的。
海派魔術(shù)要成為地域性的流派,要成為一種表演學派,一定是在這四個方面形成自己的特性,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海納百川、兼容并蓄。改革開放以后,只要是沿海城市都具備了這些特點。具體來說,第一,喜劇性,西方魔術(shù)喜劇性表現(xiàn)在幽默上,但是中國的魔術(shù),更多是滑稽。解放前,海派魔術(shù)的喜劇性更多表現(xiàn)在噱頭上。這種噱頭、滑稽和幽默是不一樣的分寸,不一樣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第二是道具的技藝,作為海派來說,借助于科學、經(jīng)濟文化的深厚基礎(chǔ),應(yīng)該比其他的地方更多地吸收高科技。當然,也不能作假,像臺灣魔術(shù)中人頭落下來,是靠電影的剪輯。第三,表演場所隨意性,也就是更平民。平民性深刻表現(xiàn)為海派藝術(shù)的特征。第四,奇觀性,某種意義上表現(xiàn)為多種藝術(shù)的雜交,學習電影、電視等藝術(shù)。有了這四條,我們對海派魔術(shù)的界定會更加有理論性。
劉明亞(上海雜技團著名魔術(shù)師):
有些人會認為魔術(shù)可能都是一些嘴上的噱頭或者什么,其實魔術(shù)里面可以分很多種類。比如像劉謙表演的,大部分是近景的魔術(shù),有一些賣口的,包括北派魔術(shù),也是賣口比較多一些。那么,海派魔術(shù),賣口是其中一個,最主要還是舞臺上的表演。還有一種是魔術(shù)里面的手法、技巧,這在行內(nèi)來說是比較認可的。作為魔術(shù)師沒有很過人的技巧,在行內(nèi)有一些人是不會太尊重你的。魔術(shù)不能落后于雜技
舒巧(著名舞蹈家):
其實我是雜技、魔術(shù)的忠實觀眾。像我這么大年紀,不管多煩惱,一看魔術(shù)就像小孩子一樣,就會想十萬個為什么。魔術(shù)使一個人進入非常純真的境界。這十年來,舞蹈界很多的舞劇就是學雜技,柔術(shù),綢吊都用了進去。沒有搞清楚雜技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學了,就是四流的雜技在臺上擺弄,很慚愧。這也是雜技的魅力。原來我覺得,雜技和魔術(shù)是“一鍋煮”的。分開之后,我覺得上海的發(fā)展,魔術(shù)不如雜技。現(xiàn)在魔術(shù)的節(jié)目沒有雜技節(jié)目那么豐富、過癮。雜技有一個晚會的總體結(jié)構(gòu),把小的節(jié)目弄得非常好,而且里面也有吸收舞蹈的部分,結(jié)構(gòu)是完整的,音、舞、美結(jié)合得很好,節(jié)目豐富。我去美國時看過太陽馬戲團的表演,覺得不如《時光之旅》好。希望魔術(shù)界能夠再有新節(jié)目趕上雜技界。雜技是對人的身體技能的極限挑戰(zhàn),魔術(shù)是對想象力的極限挑戰(zhàn)。我們有很多神話傳說,《山海經(jīng)》等等,比如女媧補天怎么補?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中汲取營養(yǎng),開拓我們的想象力。傅騰龍:
海派魔術(shù),過去為人詬病的一個是硬功夫不夠,第二個就是賣口比較差。但是這個“不夠”現(xiàn)在已經(jīng)趕上去了。像劉明亞的京韻手彩達到了最高境界。王小燕的手彩也達到很高境界,獲得了金牌。劉謙的脫口秀大家非常喜歡,我告誡兒子傅琰東,不要學劉謙,而是自己要有定位。他也說話,沒有劉謙流利,但是很謙和,人家也很喜歡。我感覺海派魔術(shù)是來自四方的,但是海派魔術(shù)也是隨著交流、發(fā)展撒向四方。海派,是海納百川之后再釋放出去。我是60歲之后到北京去支援我兒子傅琰東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說我脫離海派。傅琰東在臺上,大家也感覺他是上海的小孩。我們闖北京,也是經(jīng)過了艱苦的磨煉。我從1995年開始上中央電視臺的春晚,后來一直與中央電視臺結(jié)下了又愛又恨的關(guān)系,連傅琰東這次,我們是第八次上春晚。過去上春晚和現(xiàn)在不同,過去魔術(shù)作為一個品種讓你演一演,現(xiàn)在把魔術(shù)當了重點。至于海派魔術(shù)未來的走向,我認為,只有“上海的”才能獨特。要棋高一著,要堅持自己的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