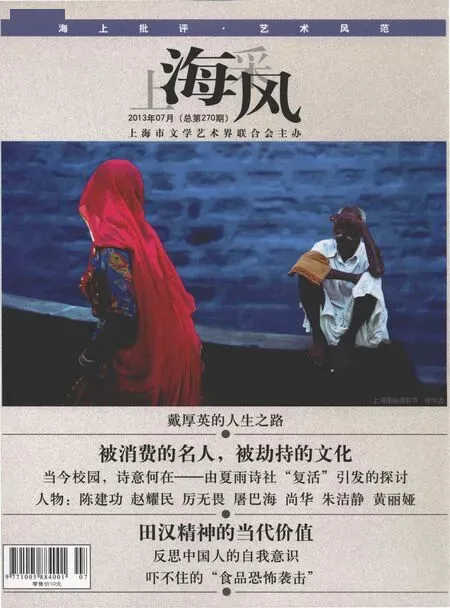影壇元老“雙百導演”楊小仲
文/陳清泉

說楊小仲是中國電影的元老,是因為他在美商亞細亞影戲公司拍出上海出產的第一部影片之后的第二年(1920年)就寫出了我國第一部長故事片劇本《閆瑞生》,由伍彭年導演并于次年上映。據查,這是我國開始拍攝電影以來的第33部影片。當時擔任過編導的僅為11人,楊小仲名列其中,所以他是當之無愧的元老級人物。
稱楊小仲為“雙百導演”,是因為他一生拍了近100部電影(如包括紀錄片當超過此數),所以人們叫他“百部導演”;后來他導演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于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評選中,獲得最佳戲曲片獎,于是人們給他又加了一個“百”字,成了——“雙百導演”了!
楊小仲與我家長輩相識、相交乃至成為“不是親戚,勝似親戚”的關系,是從19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的。那時他已進入商務印書館好幾年并于1918年成為正式職員。不久,我的大表叔陳趾青也進入商務做英文編輯,先是見習隨后轉正,與楊小仲成為同事,并先后進入活動影戲部。楊小仲于1920年為中國影戲研究社將當時上海灘上十分轟動的“文明戲”《閆瑞生》改編成電影劇本,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成立的活動影戲部拍成了電影。這是商務從1919年開始拍攝影片以來的第一部長故事片,也是楊小仲進入電影領域的處女作,從此他便踏入影壇,并終身與電影為伴。
陳趾青見楊小仲步入影壇,自己也躍躍欲試并于1926年寫出了他的第一個電影劇本《母之心》,從此,活動影戲部出現了最佳搭檔——陳趾青與楊小仲,他倆在六年間,由陳趾青編劇、楊小仲導演的影片竟達七部之多,其中十分成功的作品有《不如歸》《秘密寶窟》《兒子英雄》等。而陳趾青在楊小仲幫助下,不僅自編自導了影片,還導演了楊小仲編劇的電影,可見他們友誼之深。
1934年,陳趾青病逝于揚州,楊小仲與當時上海電影界人士近百人奔赴揚州為陳趾青執(zhí)紼。這是楊小仲第一次見到我,而我與他真正有交往卻已是1948年的事了。
陳趾青與楊小仲比鄰而居,一個住福履里路(今建國西路)建業(yè)里中弄72號,一個住74號。1948年春他過四十大壽,電影界很多人要來吃壽宴,于是便借了楊家客堂與天井辦了四桌酒,這是我真正結識這位我稱為“楊伯伯”的大導演的開始。
由此為開端,我們有了二十年的交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從揚州出差來滬,住在陳翼青處。一天上午,我在弄堂里與他相遇,已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了,還是那么精神,頭戴一頂巴拿馬硬盔帽,手拎一只皮包,有點氣宇軒昂的味道。在我叫了他以后,他便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的近況來。還用自我譴責的口吻說:“我們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身上的污垢太多了,真的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呀!”話語十分懇切。
我安慰他說:“楊伯伯,您能認識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您一定能夠在新社會發(fā)揮作用的。”
他點點頭,并且用欽慕的眼光看著我,說:“你們肯定是有前途的……”大概他已知道我參加了革命(那時,參加了工作并拿供給制的就是“參加革命”了),所以作了這樣的判斷,其潛臺詞十分豐富。
不料,又過了六七年,我這個“很有前途”的青年,卻因“與反黨分子沆瀣一氣”犯了“執(zhí)行資產階級新聞路線”的“嚴重右傾錯誤”,不僅在實際上被撤銷了行政職務而且被清除出共產黨。此時,我以解決夫妻長期分居的名義要求調來上海,以擺脫在揚州的困窘處境。蒙天馬電影制片廠領導不因我的上述“劣跡”而歧視看待,反而“格外開恩”地接納了我,但我將與楊小仲同為天馬廠的工作人員,這位楊伯伯又怎樣看待我呢?
真的是“無巧不成書”,我到廠后的第三天,廠部就通知我到《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攝制組,接替已升任助理導演的張秀芳擔任場記。而該片的導演就是我不太想見到的“楊伯伯”,真的是要多么尷尬就多么尷尬!
我到制片主任陶侃那里報到時,他顯得很熱情,告訴我說:“這部戲已經開拍了一段時間,但大量場景尤其是重場戲還沒有拍。張秀芳是一位老場記,你可以先跟著她看看,然后就獨立工作——把場記的任務擔起來。”
我連連點頭稱是,雖然我從妻子陳嬋那里知道一些場記的工作范圍,但要實地去干恐怕還是要經過認真學習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好的。
陶侃領著我進入攝影棚,照明師們正忙著“佈光”,我遠遠地就看到這位楊伯伯坐在攝影機一側的帆布椅上,正在和一位年輕的男士交換意見,我想這位風度翩翩、頭發(fā)梳得十分齊整、著裝極其整潔、不到四十歲的同志就是導演俞仲英吧。而站在一旁聽兩位導演說話的女同志,一定就是我的前任場記張秀芳了。
陶侃領我到他們面前一一作了介紹,楊小仲說:“來了,好,好!”露出一臉的笑——這是一種長輩見了晚輩的真情流露的笑,使我忐忑的心情馬上松了下來。
接著,俞導演也表了態(tài):“先跟著秀芳看看,讓她講講工作情況……”
秀芳立即對我點頭表示歡迎,我向她表示:“我是來跟你學習的。”聽了這話,她的臉竟有些發(fā)紅了,接著開玩笑地說道:“我哪兒比得上你們家陳嬋呀,你們家里就有一個現成的師傅……”
張秀芳詳詳細細地介紹了場記單如何填、怎樣打拍板以及場記需要做哪些工作,然后對我說:“下一個鏡頭就由你來打板、記場記單。”一下子就把我推向場記工作的第一線,讓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鍛煉的機會,這分明是對我的充分信任。
這天的中午,大家在吃完飯后都找地方休息去了。楊小仲看到四周無人,招手讓我到他面前,悄悄地對我說:“你要吸取教訓呀!”很明顯,他已經知道我的“劣跡”了!我注意到,他的語言十分平緩,充滿了關懷之情而不是責備,這使我很感動。而且,他是按照革命者的要求,對一個犯有“錯誤”的青年人進行教育。
五十年代初與我的談話和這一次與我的談心,生動地表明一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正努力使自己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從他解放以后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看,他的確是在努力地“為人民服務”的,與他從前的一些作品對比,真可謂“涇渭分明”。在經過了他對我說的“脫胎換骨”之后,他迎來了“又一個藝術創(chuàng)作的春天”。
一個是,他連續(xù)拍了五部戲曲藝術片。上海從1953年開始,以桑弧導演拍攝的越劇戲曲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為開端,謝晉、黃祖謨、張?zhí)熨n、應云衛(wèi)等人相繼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而楊小仲則成了在戲曲藝術片導演方面卓有成效的一位藝術家。他先后導演了京劇戲曲片《紅樓二尤》、錫劇戲曲片《庵堂認母》、閩南戲《陳三五娘》、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與俞仲英合導)、京劇《周信芳的舞臺藝術》等戲曲藝術片,讓周信芳、言慧珠、姚澄、蔡自強及六齡童、七齡童等一批著名演員在銀幕上展示風采,讓全國城鄉(xiāng)觀眾獲得欣賞這些優(yōu)秀劇目的機會。
另一個是,他“童心未泯”,努力進行兒童片的開拓,先后拍攝了《蘭蘭和東東》(1957年)、《好孩子》(1959年)和《寶葫蘆的秘密》(1963年)。人們在欣賞這些充滿童趣的影片時,很難想象這是他從58歲—64歲時完成的作品。
從拍完《寶葫蘆的秘密》以后,他再也接不到任務了。那個時期,在經過“反右傾”、“拔白旗”、“新三反”、“面上社教”和“四清”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后,他被“掛”了起來,直至逝世再也不能涉足他為之努力了一生的電影了。
1969年的一個充滿慘霧愁云的日子,他奉“造反派”之命每天來廠接受批斗已有多日了!這一天,好不容易挨到下班,但卻走上了不歸路。第二天,一個噩耗傳到“牛棚”中,他于昨天突發(fā)疾病(好像是心腦血管病)不幸逝世了。我感到“牛棚”內的氣氛特別凝重,與我同登一個“牛棚”的老藝術家們用沉默來悼念這位故人,大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我們兩家雖為至好,卻也不可能去火葬場為他送行了,可嘆,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