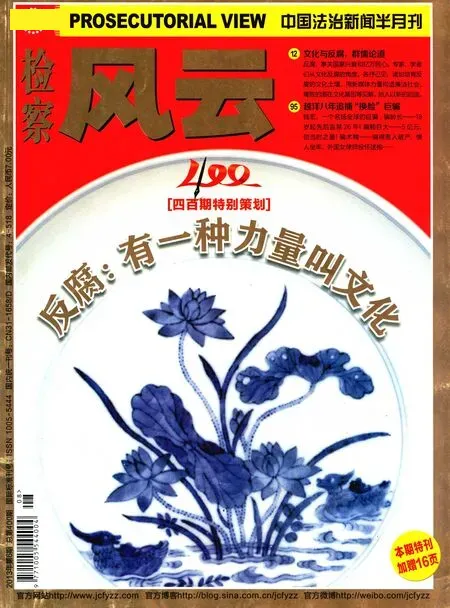涉罪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應違法披露
文/姚建龍
涉罪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應違法披露
文/姚建龍

姚建龍,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教授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擴展了犯罪人隱私權保護的范圍。這是《兒童權利公約》所確立的“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所規定的未成年人特別、優先保護原則的體現,也是一種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慮。
保護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立法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是未成年人保護與少年司法的一項重要國際準則。聯合國第96次全體會議于1985年11月通過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北京規則》)第八條規定:“應在各個階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隱私的權利,以避免由于不適當的宣傳或加以點名而對其造成傷害”,“原則上不應公布可能會導致使人認出某一未成年犯的資料。”盡管《北京規則》沒有明確將傳媒列為限制公開未成年犯資料的主體,但由于媒體是信息傳播的最主要載體,這一限制性規定實際上將媒體作為主要的規制對象。
199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將《北京規則》關于不應公布可能會導致使人認出某一未成年犯資料的要求轉化為了我國國內法的規定,并且明確將媒體作為主要的規制對象。該法第42條第二款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決前,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其中引起爭議最激烈的是對立法將禁止披露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的時間節點設置在“判決前”。 這種披露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時間節點的設置違反了《北京規則》關于應在各個階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隱私權的規定,也使得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大打折扣。因為即便在判決后才披露未成年人犯罪人的身份信息,仍然可能會給該未成年人貼上“犯罪人”的社會標簽,仍會對其矯正和復歸社會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針對上述不足,許多省市地方未成年人保護立法均放松或者取消了時間節點的限制。1999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吸收實踐經驗和地方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完善了限制媒體披露未成年人罪案信息的規定。該法第45條第三款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這一規定取消了披露時間節點的限制。
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規定相銜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在隨后頒布的關于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規定中,明確不得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例如,1995年《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第五條規定:“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當保護未成年人的名譽,不得公開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最高人民檢察院2002年頒布2006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也均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信息。由于公檢法機關是媒體獲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的重要來源,這些對于司法機關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禁止性規定,對于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要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12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新《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我國限制媒體披露未成年犯罪人信息的制度作了進一步地完善。該法以一個獨立法條(第58條)的形式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肯定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取消僅在判決前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規定,并且將限制披露的主體進一步擴大到了網絡這一新興媒體。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制度的基本內涵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訴訟法》等的規定,可以將我國現行禁止媒體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制度概括為如下基本內容:
對于未成年人觸法案件的信息披露限制是指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但按照“舉重以明輕”的規則,對于有違法及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也不應隨意披露。
受約束的對象主要包括“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增加了“網絡”這一新興媒體后,還使用了“等”的表達方式,即還可將其他未列舉的媒體包括在內。如果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其他媒體形式,也要受到未成年人罪案信息披露限制制度的約束。由于司法機關也是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主要掌握者和媒體獲取未成年犯罪人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司法機關也被禁止向外界,特別是媒體披露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在自媒體時代,普通公民在具有公共傳播功能的微博、博客等網絡空間,也應受到不得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法律規定的約束。
禁止披露的內容不僅僅包括犯罪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還包括其他任何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息披露限制制度僅僅是禁止披露未成年人罪案中犯罪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而不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本身。只要媒體對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予以了保密,對于罪案本身報道、評述、分析、研究均是允許的,也是合法的。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沒有時間節點的限制,即便涉罪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或者刑罰執行過程中、刑罰執行完畢后已經成年,也不應在“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中披露其身份信息。
近日,某歌唱家、少將之子李某在因尋釁滋事解除收容教養后不到半年又涉嫌輪奸案引起軒然大波,也引起輿論的強烈關注。但令人遺憾的是,全國媒體在對此案的報道中幾乎集體淪陷,一方面正義凜然的聲討、反思,另一方面又公然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身份信息的規定,棄新聞職業倫理于不顧。
對李某輪奸案的幾點反思
近日,某歌唱家、少將之子李某在因尋釁滋事解除收容教養后不到半年又涉嫌輪奸案引起軒然大波,也引起輿論的強烈關注。但令人遺憾的是,全國媒體在對此案的報道中幾乎集體淪陷,一方面正義凜然的聲討、反思,另一方面又公然踐踏《未成年人保護法》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身份信息的規定,棄新聞職業倫理于不顧,不但熱衷于挖掘輪奸案細節,也將李某的照片、家庭情況、成長經歷等所有個人身份信息全部曝光。李某首先是“未成年人”應遵守“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的法律規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8條)。當然,只要不披露身份信息,對于罪案本身的報道、評述、研究是允許的。
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制度健全的國家,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屬于嚴厲禁止披露的范疇,并且這樣的禁止性法律規定能夠得到較好的執行。例如,1997年日本神戶發生兩名兒童被害并分尸的惡性案件,疑犯為一名僅有14歲的少年,此案震驚全國。由于日本法律禁止披露少年犯身份信息,疑犯真實姓名未被傳媒公開,在法律文件上他被稱作“少年A”。“少年A”經家庭法院裁定送入少年院,2004年出院并更換身份后在另一城市正常生活。迄今為止,其真實身份信息仍被保密。在對該案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嚴格的身份信息保密制度對于“少年A”可以改惡從善、正常回歸社會、融入社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除了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被違法披露外,本案還有諸多值得反思之處:
李某是不良教育、家庭環境、社會環境的畸形產物,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收容教養制度的犧牲品。
少年司法制度奉行保護主義理念,但其基本立場是寬容而不縱容:一方面強調以教代罰,在懲罰與放任之間建立中間性保護處分措施;另一方面則建立剔除機制,將極少數極度惡性的未成年犯罪人通過棄權等機制當做成年犯罪人來對待。我國少年司法改革,還任重道遠。
《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不適宜未成年人活動的場所不得允許未成年人進入(36、37條),涉事酒吧違法接納李某等未成年人飲酒難辭其咎,主管部門應首先責令改正并給予行政處罰(67條)。涉酒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動向,酒吧管理應予重視。
未成年人輪奸案的常見特點是利用被害人的醉酒狀態。此案中被害人與嫌疑人聚飲而醉,并同往賓館,給嫌疑人以可趁之機。避免進入高危險情境是被害預防的一條黃金法則。在犯罪學看來,每個男性都是潛在的犯罪人,女性與男性飲酒應適可而止避免醉酒,酒后更應避免前往賓館等高危險場所。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