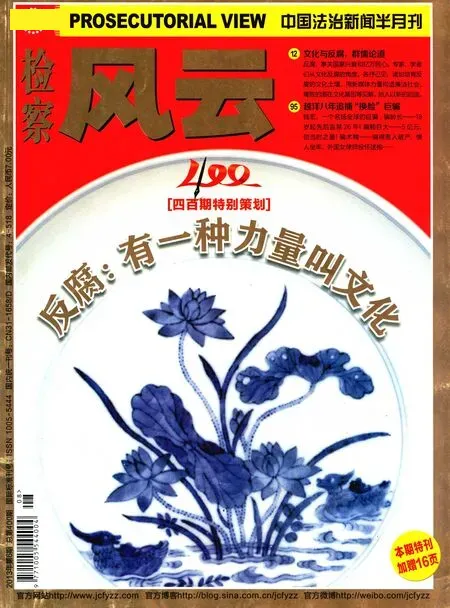兒女婚變與算“賬”的父母
文/章偉聰
兒女婚變與算“賬”的父母
文/章偉聰
父母總是為兒女的婚姻大事牽腸掛肚。正如那句話: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長寧區法院近期判決的幾個由兒女離婚引發的父母討債案件提醒人們,少一些財產與情感的糾纏,就會多一些身心的平靜和輕松。
辦婚宴的錢,到底借了沒有
2005年,譚健與小他三歲的許雋步入了婚姻殿堂。可惜好景不長,2006年9月一場大吵之后兩人開始分居,最終于2009年7月經法院判決離婚。
2010年12月,張阿姨與丈夫譚先生共同將兒子譚健及前兒媳許雋告上法庭。張阿姨在訴狀中稱,2006年3月,兒子辦婚禮時向她借款5萬元用于支付婚宴開支。現在兒子離婚了,這筆借款理應由兒子譚健及前兒媳許雋共同償還。
雖然與譚健一同坐在被告席上,但許雋心里明白,本案的真正被告只有她一人。許雋告訴法官,婚宴的費用是譚健支付的,且花費不到5萬元。她從來沒有向原告借過錢,譚健是否借過她不清楚。許雋認為,當時譚健的年收入約有20萬元,根本沒有必要向原告借錢。
為證明自己的說法,張阿姨向法庭提供了兒子譚健寫的一張借條。該借條記載:“今借父母(姓名)人民幣伍萬元整,用于婚禮喜酒費用。借款人:譚健 2006年3月11日”。許雋認可借條是譚健寫的,但認為是譚健在第一次起訴離婚后的2007年12月寫的,許雋要求對借條的形成時間進行司法鑒定。
2011年8月,司法鑒定部門出具鑒定結論:由于借條上手寫字跡系非正常保存,字跡墨跡歷時變化與正常條件保存下的變化規律不相符合,難以對借條的實際形成時間提供鑒定結論。同年9月,張阿姨以譚先生因病住院為由,申請撤回起訴。
但去年10月,張阿姨又以同樣的訴訟請求再次向長寧法院起訴。法庭上,張阿姨堅決要求許雋歸還5萬元中的一半,許雋則直指借條是假的,原告根本就是訴訟詐騙。雙方各執己見,沒有調解余地。然而庭審結束后,張阿姨卻提出了撤訴申請,理由是:丈夫譚先生已經過世,自己沒有精力再打官司了。

為了讓兒女結婚生子,父母往往出錢出力,甘愿傾盡所有。而當兒女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走向解體時,做父母的甚至比兒女本人更加傷心傷神。這也是財產與情感太過糾纏的結果。
房屋首付款,是贈與還是借款
黃斌與郝靜自小相識,2001年8月,兩人登記結婚。2007年4月,為改善居住條件,兩人買了一套價值55萬元的商品房。其中首付款32萬元由黃斌的父親黃先生資助,20萬元公積金貸款由黃斌主貸,其余3萬元兩人共同支付。房屋產權登記在黃斌、郝靜的名下,為兩人共同所有。搬入新居后不久,黃斌與郝靜逐漸產生矛盾。2009年夏天,郝靜搬回娘家居住,開始與黃斌分居。
2011年11月,黃斌起訴要求與郝靜離婚。郝靜應訴后同意離婚,也認可現價110萬元的房產為雙方的唯一財產,但在具體分割時,圍繞32萬元首付款是不是向黃斌父親借的,兩人爭執不下。黃斌拿出父親的銀行存折、相應的取款憑證以及他與郝靜的一段電話錄音,以此證明買房時用父親的存款支付首付款,郝靜對此明知并曾表示愿意與他一人一半償還。但郝靜均不予認可。后來經過法院調解,兩人在去年3月達成協議:雙方自愿離婚;房產歸黃斌,黃斌支付郝靜房屋折價款56.5萬元。
得知兒子與郝靜調解離婚,黃先生感覺自己吃虧了。去年8月,黃先生一紙訴狀將黃斌和郝靜告上法庭,要求兩人分別歸還借款16萬元。長寧法院審理后駁回了黃先生的訴訟請求。
主審法官表示,原告出資行為的性質應當以出資當時原、被告雙方的意思表示為準。黃先生主張32萬元是借款,但沒有提供能夠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的證據。黃斌雖然認可黃先生的說法,但從他與黃先生是父子關系以及已經與郝靜離婚的事實考慮,黃斌的表態并不能得出借貸關系存在的結論。
關于電話錄音,法官表示,黃斌在電話錄音中一連六次問郝靜:“32萬元是不是我爸付的首付?”事實上,如果雙方都清楚地知道這32萬元是借款,就無需用這種方式提問。因此,僅憑電話錄音,還不足以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綜合分析案件事實及在案證據,法庭確認,原告在兩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他們購買房屋出資32萬元,并將房屋產權登記在他們名下的行為,是贈與行為。
墊付的藥費,小夫妻該不該還
去年6月,年過花甲的吳阿姨向長寧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女兒歐陽慧及女婿張毅明共同償還欠款15.3萬元。吳阿姨在訴狀中稱,2006年3月,女兒歐陽慧被查出患有白血病,為了幫女兒買進口特效藥,自己分兩次借給他們15.3萬元。2011年8月,女婿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但對這筆債務卻只字未提,所以起訴要求女兒女婿歸還這筆欠款。為證明自己的主張,吳阿姨向法庭提供了女兒寫的借條、銀行轉賬憑證以及藥品出售人員的書面證明。
對吳阿姨的主張和相關證據,女婿張毅明卻有另一種說法。張毅明表示,歐陽慧患病前投有保險金額為10萬元的重大疾病保險,患病后歐陽慧單位為她捐款10萬元,自己父母也資助過7萬元,這些錢款已足以支付歐陽慧治病所需的花費,沒有必要再向原告借款。張毅明認為,就算原告出資為女兒買藥,也應視為贈與。張毅明還認為,兩張借條是歐陽慧事后補寫的,申請對借條的形成時間進行鑒定,但后來又撤回了申請。法庭審理后于11月5日作出判決,支持吳阿姨的訴訟請求。
法庭認為,本案有兩個爭議焦點:一是原告是否出資為女兒買藥;二是該出資是否屬于借款。關于原告是否出資買藥,該案審判長表示,經法庭審理,原告提供的藥品發票、銀行轉賬憑證以及證人證言等證據,與其訴稱的購藥時間、地點、藥物名稱及金額等完全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能夠證明原告出資買藥的事實。
關于出資性質,葉法官認為應從幾個方面綜合分析。首先,張毅明認為借條是事后補寫的,但沒有提供反證證明,并撤回了鑒定申請;其次,張毅明認為根據當時的情況沒有必要借款,但借款理由是否成立與借款事實是否存在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再則,生病、住院是夫妻任何一方都可能遭遇的,除非有特別約定,相關費用應作為共同生活的必要支出以夫妻共同財產支付;最后,夫妻之間有相互扶養的義務,母女則是彼此獨立的民事主體,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原告有任何贈與或免除債務的意思表示,否則當然應作為夫妻共同債務予以歸還。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
法博士點評
別讓財產與情感太過糾纏
從法律上講,借貸關系成立與否,取決于雙方當事人有無相應的意思表示并且該意思表示是否真實。三個案例中,第一個由于原告撤訴暫且不論。第二個案例中,原告出資32萬元的性質可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從舉證責任來看,原告負有舉證責任卻未能提供相應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從法律規定來看,婚姻法相關解釋明確規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除非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否則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因此,黃先生為兒子買房支付首付款,房屋產權人登記為兒子、兒媳的事實,在沒有反證的情況下,這筆出資應當認定為是黃先生對兒子、兒媳的贈與。而第三個案例,雖然雙方對借條這一關鍵證據說法不一,但是,在母親墊付行為得到確認的前提下,夫妻之間又互負法定的扶養義務,因此,法庭認定母親墊付的藥費為借款,不僅符合法律規定,也符合社會公序良俗的要求。
事實上,三個案例更多反映的是兒女婚姻失敗帶給父母的心理影響。現如今,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家庭財產的“含金量”早已今非昔比。因此,在父母對兒女的婚事有較大“投入”,兒女最終又選擇離婚的情況下,父母難免有“人財兩空”的失落感。由此,兒女離婚后,父母不惜以對簿公堂的方式進行“秋后算賬”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實,無論是父母還是小兩口,只要轉變一下觀念,就不會讓財產與情感太過糾纏,從而保持內心的一份平靜。當然,這需要雙方達成共識。如上所言,父母對子女疼愛有加,談婚論嫁又少不了以一定的物質和感情為基礎,而為了促成兒女的婚事,許多父母不惜傾盡自己畢生積蓄。因此,一旦兒女婚姻失敗,財產與情感的糾纏幾成必然,當事者想要淡定也難。既然如此,雙方若能達成財產歸財產、感情歸感情的“君子協定”,豈不省心?
讓財產歸財產,是對勞動的一份尊重;讓感情歸感情,是對愛情的一份信念。這話聽起來有點虛夸,但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高談闊論,而是法律早就考慮到了的。我國婚姻法第十九條有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婚姻法解釋(二)、解釋(三)對父母為兒女購買婚房的出資的性質認定也做了具體規定。這都彰顯了民事行為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原則的立法精神。我們要做的僅僅是轉變觀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