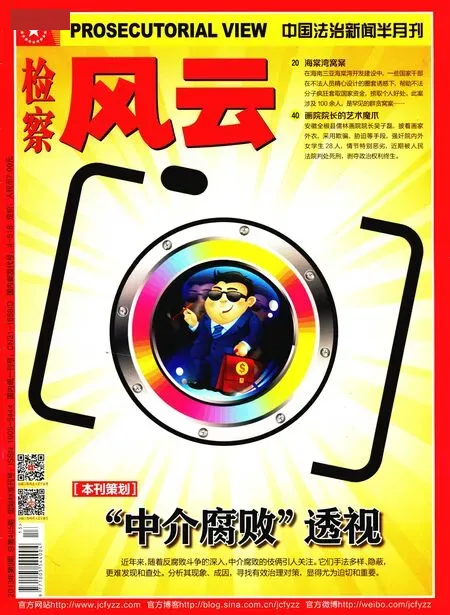俄羅斯轉軌的“腐痛”與憂思
文/張克
俄羅斯轉軌的“腐痛”與憂思
文/張克
Deliberation on corruption problem in transition of Russia
2013年3月,俄羅斯反腐法案細則出臺,為俄羅斯龐大的反腐敗法律體系又增添了一項規范性文件。俄羅斯的腐敗問題自蘇東巨變以來一直是世界關注的焦點,諸多其他轉軌國家冀望于俄羅斯提供反腐敗的良治經驗。遺憾的是,俄羅斯反腐敗的曲折性和艱巨性超出了世人預期,二十多年來,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關系始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2年10月的《全球財富報告》統計顯示,俄羅斯是世界財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1%的富人,掌握著全國71%的財富,財富分布的基尼系數為0.84。寡頭與貧民之間嚴重的貧富差距被認為是俄羅斯腐敗對社會的最惡劣影響,制度性腐敗使得收入分配不公無法從根本上解決。
記得十年前,普京把石油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投入監獄,接著又消滅了多位葉利欽時代崛起的寡頭。他那時曾怒斥眾寡頭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商人,可以在短短幾年內,暴斂數十億美元的財富。然而此后十年,俄羅斯國家的金融、石油、軍工、交通、傳媒等重要行業,又紛紛落入新寡頭之手,整肅貪腐變成周期性的政治游戲。
俄羅斯,這個轉型國家遭受的腐敗頑疾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為更多的后發現代化國家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教訓。
2013年2月23日,俄羅斯圣彼得堡,以“保衛俄羅斯軍隊抵御腐敗侵害”為名的集會在戰神廣場舉行。(圖/東方IC)
反腐敗遭遇法律失靈
在俄羅斯長期的反腐敗斗爭中,反腐敗立法一直被置于突出位置,普京曾指出,“為保證反腐敗取得成效,就必須解決公民對國家權力機關信任程度不高的問題;而要提高公民對國家機關的信任度,則必須建立公平的法律并在實際生活中付諸實施。”
2008年5月,梅德韋杰夫政府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敗措施,相繼出臺了《俄羅斯聯邦反腐敗計劃》和《俄羅斯聯邦反腐敗法》(以下簡稱《反腐敗法》)。《反腐敗法》中“官員和公職人員不得收受超過3000盧布(約合609元人民幣)的禮物”的嚴苛規定,一度被公眾視作“驚人之舉”。次年,該法全面實行,規定公職人員不論等級高低,須一律公示家庭收入和財產。此外,梅德韋杰夫也在俄羅斯國家機關內部增設部門,專門負責審查國家公務人員及有意擔任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情況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2012年8月,普京也批準了一項法案,其中涉及禁止俄羅斯官員及其配偶和18歲以上子女在海外擁有財產等反腐措施。俄杜馬旨在通過這項法案大力打擊腐敗,使民眾更多地了解和監督官員的收入與財產,并且防止官員將財產非法轉移至國外。
盡管俄羅斯反腐敗法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對法案的修訂以及相應的配套建設從未間斷,但俄羅斯反腐作用卻仍然不盡如人意。2011年,俄內務部共查處3.1萬起腐敗案件;而2012年,這一數字上升到4.5萬起。2012年12月5日,“透明國際”也公布了“2012年國際貪腐印象指數報告”,俄羅斯排名依舊靠后,此次是第133位。
此前,來自俄羅斯國內的數據《俄羅斯年度反腐狀況報告》也指出,俄羅斯每年“腐敗經濟”規模高達6500億美元,相當于俄羅斯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較4年前增長了17.6%。俄羅斯的腐敗情況并沒有明顯改善。
俄羅斯反腐敗之所以遭遇法律失靈,制度約束未起應有作用,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反腐敗法律的目標具有多重性,立法往往不是出于真正解決腐敗問題,而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
轉型以來,俄羅斯政壇風波迭起、斗爭不斷,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政治勢力之間的沖突始終沒有停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個政治體制和各項政治事務的正常發展,自然也影響到腐敗的治理。可以說,俄羅斯的腐敗治理幾乎與政治斗爭形影不離,從葉利欽到普京再到梅德韋杰夫,腐敗治理都不可避免地夾雜著政治色彩。這不僅影響了反腐敗的徹底性,也使人們對政府的反腐動機產生了懷疑,動搖了人們對政府的信心。
盡管之前頒布的《反腐敗法》從預防角度來加強對腐敗的防范,并作出預防腐敗措施優先適用的規定,但針對具體的預防制度,缺少詳細而周密的實施細則,缺乏切實可行的方案計劃。此外,各級政府機構和部門的預防制度也嚴重缺失,缺乏針對不同崗位公務人員基本行為準則的具體規定,僅僅靠《反腐敗法》中對公務員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規定來約束他們的行為,容易導致在具體工作落實過程中,個人責任感弱化、權利與義務認識不足、權限邊界模糊不清等現象發生,不僅難以達到預防腐敗的效果,甚至可能會成為腐敗滋生的誘因。
細看近期出臺的針對公務員收受禮物禁忌的反腐法案細則,對官員收禮等事宜作了較為細致的分類規定,有人說細則的公布是新一輪反腐工程走向精細化的開端,從反腐法律的執行能力來看,越是細致的法律規范執行起來越簡單,針對性越強。然而,也有反對人士認為這些細則 “十分可笑”。僅僅對送禮收禮這樣的小事大做文章,可能忽略了更為根本的反腐制度設計,而且這樣的細則對中低層級公務員可能十分有效,但對更高層級的公務員來說顯得太過小兒科。
腐敗治理是個世界性的難題,并非“立法”這一劑妙藥能看到成效。反腐敗應當從更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層面發力,讓“文本中的法律”與“實踐中的法律”相互促進才是更為有效的解決之道。
轉軌方式不同,俄羅斯腐敗破壞性更甚
同為轉軌國家,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法律變革常常被人進行比較。兩國近30年來的發展績效,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俄羅斯的腐敗問題比中國更具破壞性也更加難以根治。究其原因,俄羅斯選擇的激進轉軌方式決定了其更為劇烈和慘痛的腐敗癥候。
俄羅斯在巨變時選擇的休克療法使得國家與社會關系產生了劇烈動蕩。在20世紀90年代里,俄羅斯國內既沒有社會共識,也沒有政治共識,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之間的不斷沖突,官僚資本各派系、各集團利益的碰撞使國家處于震蕩之中。
聯邦中央和各地方之間的矛盾也使人不得安寧,甚至威脅到新的俄羅斯國家體制的建構進程。在這種環境下,首任葉利欽總統盡管被培養成“鐵腕沙皇”形象,但對解決國家政權和政治精英內部的矛盾卻無能為力。國家機構在事實上全面失調,也使立法機構國家杜馬的工作紊亂不堪。立法機構經過最初的混亂,很快便加入到催生官僚資本主義的進程中,首先是為“新俄羅斯人”利益服務,當然同時也不忘記謀私利。
俄羅斯較為徹底的體制轉軌在造就一個新富裕階層的同時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公職人員階層的收入增長緩慢,由此產生了強烈的自我補償沖動。而轉軌進程中市場經濟建立過程為公務員以權謀私提供了較多的尋租機會,特別是俄羅斯推行的全面私有化經濟改革政策,促成了掌握國有資產控制權的政府主管官員與暴富階層合伙瓜分國有資產。
反觀中國的改革歷程,政府始終堅持小步快走的漸進雙軌改革方式,保持著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以“摸著石頭過河”與“試點——推廣——完善”為特征的漸進放權改革模式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對外開放程度也大大加強。相反,推行了“休克療法”的蘇東國家,出現了惡性的通貨膨脹,俄國、烏克蘭等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甚至達到1000%甚至10000%,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也出現了崩潰式下滑,這些國家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一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有所增長。

從各國各時期的經驗來看,經濟增長率與腐敗程度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越是經濟委靡不振腐敗的機會往往越多,另一方面大量的腐敗消耗過多的社會資源反過來加劇了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與腐敗的互動陷入死循環。轉軌政府是否強有力地推進改革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一盤散沙的組織結構和過于分散的權力配置不但無法發展經濟更會導致極端腐敗。
此外,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廉政文化的深刻體現。有學者指出,“在社會轉型階段,由于原有的社會價值體系解體,又未形成新的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人們以自我為中心,社會進入道德淪喪的沉淪狀態,腐敗在這個階段表現得尤為嚴重。”
在前蘇聯時期,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規范處于主導地位,對于各級黨員干部形成了強大的潛在約束力,為防止他們的腐敗墮落設置了有利的屏障。蘇聯解體后,經濟結構的改變,帶動了社會利益關系與分配方式的調整,進而帶動整個社會價值觀的重構,占主導地位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徹底打破。在傳統政治道德體系解體、相應的道德和文化建設未能跟上、權力約束缺失之時,極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乘虛而入。
中國的改革也經歷了思想多元化的過程,但意識形態的主流觀念仍然通過各種方式覆蓋大部分人群。即使在反腐制度建設上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中國反腐敗意識形態仍然是較為穩定和積極的,這是中俄兩國在文化層面上的最大不同。俄羅斯式顛覆性的革命往往造成巨大的制度漏洞和意識形態真空,滋生腐敗的機會和治理成本極大;而中國式漸進改革有助于保持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穩定,降低制度變革失敗的風險,對腐敗的控制相對處于更為穩妥的狀態。
轉軌國家必經的陣痛根治
在一個國家轉軌的過程中,腐敗的蔓延在本質上是政治、經濟轉軌和與之相伴的制度變革不相適應的產物。俄羅斯反腐敗歷程顯示:轉軌是一個打破原有的經濟制度體系的過程,若與新的政治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制度建設不足,會導致制度漏洞頻出,并提供了大量的腐敗機會。即使有眾多反腐敗立法,但由于制度執行力不足會導致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很低或者處罰成本不高,由此帶來了制度約束失效。政治、經濟轉軌破壞了原有的意識形態,造成了道德敗壞,進而導致腐敗動機的大幅提高。
鏈接

俄羅斯最新出臺的反腐法案細則規定,公務人員在典禮活動或公務出差中以官員身份收到的禮物,將被視作非法;而在活動中發給每位與會者的辦公用品,則屬于可接受禮物范疇。如果公務人員在參加會議時收到作為辦公用品的平板電腦則無需上繳(貴金屬和寶石材質除外)。鮮花和易腐壞的食物也屬于可接受的禮物,即官員可以接受任何數量的鮮花、冰淇淋和火腿。
公務人員收到明文規定之外的物品需在3日內報告上級,并提供相應發票,證明禮物的價值低于3000盧布。若無法出具發票,而禮物的價值又明顯高于 3000盧布,則當上繳至上級官員。若禮物十分稱其心意,公務人員可以出錢將禮物贖回。細則同時規定,國家公務人員,例如總統、總理、部長、議員、檢察長、調查委員會主席、央行行長等,不能收受任何禮物,上繳后也不能贖回。
(來源:俄《獨立報》)
俄羅斯反腐敗斗爭的經驗啟示我們,在立法規制之外還應將目光投向更為深邃的地方:必須鏟除腐敗生成的文化土壤,寬容腐敗的心態亟須救贖;必須鏟除腐敗生成的制度土壤,權力應當得到制衡而不是共謀。
由于腐敗已經滲透到俄羅斯社會的文化心態層面,所以反腐敗已不僅僅只是一場政治斗爭,更是一場文化斗爭。隨著腐敗的制度化、公開化,俄羅斯社會出現了一種很危險的文化潮流,越來越多的人對腐敗的發展熟視無睹,對腐敗的危害性視而不見,導致“腐敗有利論”大行其道。
作為對策,普京曾提出“以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和社會團結為核心的新俄羅斯思想,作為聯系俄羅斯人民的精神紐帶、支持俄羅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團結俄羅斯人民的精神動力”。新俄羅斯人的核心價值觀念有待進一步建立,其中就蘊含著對腐敗的基本看法,只有讓民眾充分意識到腐敗對國家與社會的深刻負面影響,寬容腐敗的心態才能被救贖,腐敗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才能得以鏟除。
俄羅斯的政治轉軌,實現了從一黨專制向多黨制下的競爭性執政制度的轉變。民主選舉、政黨競爭執政,在理論上一直被視為是實現權力監督、遏制權力腐敗的靈丹妙藥,然而在俄羅斯的實踐中卻未見成效。究其原因不難發現,癥結不在民主制度本身失靈,而在于俄羅斯民主化不足。治理俄羅斯腐敗除了加強文化建設和制度建設外,更應重視民主政治的發展,以民主和公開的方式來制約和監督權力,這是防止公權濫用和腐敗滋生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
一個擁有成熟公民社會的國家制約腐敗的成本往往是比較低的。公共輿論是反腐的有力武器,應確保公共輿論遠離腐敗現象的影響,保證輿論媒介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加強輿論對政府機構以及公務人員的監督,及時采納社會輿論正確、合理建議和意見。
2010年,俄羅斯開始實施電子化政務,整合各地數據庫對官員的財產狀況進行監督和審查,隨著技術的日益發展,政府應及時對數據庫進行完善和補充更新,動員更多的民眾參與反腐敗這一國家工程。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