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成:檢察官要成為“法律的守護人”
汪建成:檢察官要成為“法律的守護人”
新刑訴法對刑事證據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增補或修訂,主要涉及證據種類、證明標準、舉證責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及證人制度等方面的內容。這些修訂充分吸收證據理論研究成果,對于繼續完善刑事證據制度,提升檢察工作水平,實現司法公正具有積極意義。同時,證據制度的改變也使檢察工作面臨更多挑戰。為此,本刊專訪了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汪建成教授,暢談刑事證據制度變革對檢察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
《檢察風云》: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證據種類進行了增補或修訂,將“物證”、“書證”作為兩種獨立的證據種類予以分立,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在“勘驗、檢查筆錄”后增加規定了“辨認和偵查實驗筆錄”,并將“電子數據”與“視聽資料”規定為同一種證據類型。上述對刑事證據類型的規范化努力有何重要意義?
汪建成:證據種類的規范化首先要求檢察機關應當按照嚴格的形式要求,以法定的證據種類形式參加法庭舉證活動。證據種類規范化既是實現訴訟活動規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人員進行取證、質證、認證等一系列訴訟活動的行為依據。
在將案件交付審判前,檢察人員必然會接收紛至沓來的與案件有關的各種信息,用什么樣的標準對這些繁復的信息材料進行篩選、分析和判斷,并把它作為指控材料提交給法庭審查,不僅直接關系到訴訟效率的高低,而且直接決定著能否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只有以法定的證據種類形式為標準對各種證據材料進行收集、固定和運用,才能確保最終的指控證據具備證據能力,有資格進入法庭審判范圍并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證,最終被法庭接受作為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根據。
因此,對于刑事證據的準入資格,各國都規定有嚴格的形式條件,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必須以法定的證據種類呈現在法庭上。可以說,對刑事證據種類進行規范化處理是我國實現刑事法治的必由之路,也意味著作為刑事審判過程中主要的證據提供者的檢察機關,應當進一步強化法治意識,在證據收集、固定、運用上嚴格按照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確保所有提交給法庭的證據都符合法定的證據類型。
其次,在“物證”被規定為一種獨立的證據種類后,檢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和運用物證上必須加倍謹慎。考慮到物證和書證在對案件的證明方式以及搜集、審查和認定方法上的諸多不同以及各國的立法通例,本次刑訴法修改沒有固守過去將兩者規定在同一款中的一貫做法,而是將兩者作為兩種獨立的證據種類分別規定在不同款,并采納了學者的意見,將物證規定在書證之前。對于檢察機關而言,除了要按照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兩個證據規定”的要求使用物證外,還必須在提取物證后及時進行審查,確保物證的收集程序、方式等合乎法律規定,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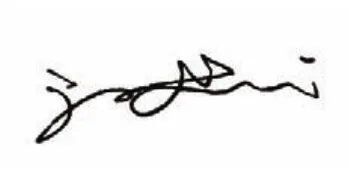
本期客座總編輯:
汪建成,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證程序存在瑕疵的應當及時補正,盡量避免物證因為在提取程序、方式等方面存在瑕疵而無法作為定罪根據從而削弱控方證據指控力度的情形出現。
另外,對于幾種新增加的證據種類,如電子數據、辨認筆錄、偵查實驗筆錄等應當注意采取相應的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這些證據的方法。其中電子數據的固定和運用應當嚴格按照“兩個證據規定”來進行;對于辨認筆錄和偵查實驗筆錄必須注意到這兩種證據在訴訟證明中的補強作用,因此這兩類證據必須同相應的主證據結合起來使用。最后,對于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能否使用,仍然存在裁量的空間。檢察機關在“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的使用上不能放棄審查的職責,應當嚴格按照這些證據種類的法定要求,逐一審查核實,才能最終確定是否作為證據使用。
《檢察風云》:偵查程序的核心在于查獲犯罪嫌疑人和搜集證據,在一定意義上,查獲犯罪嫌疑人的過程也就是搜集證據的過程。修訂后的刑訴法為何加強了對偵查程序的監督力度?
汪建成:偵查取證行為必然伴隨公權力的運用,往往通過暫時限制或剝奪民眾的人身自由、財產權或隱私權等憲法權利的方式進行。因此,對偵查取證行為施加控制,將其納入法治軌道是各國立法的共同選擇。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也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比如確立了訊問錄音錄像制度,要求偵查人員在訊問重大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憲法體制下,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有限的司法審查功能,因此,如何加大對偵查取證工作的監督范圍和力度,暢通監督的渠道,必將成為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后,人民檢察院應當認真研究和加以解決的問題。本人認為,除了傳統的發出糾正違法意見通知書以外,召集偵查人員和辯護人參加的聽證應該逐漸成為偵查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此外,檢察機關對偵查人員出庭接受對有關取證行為的詢問應該給予高度重視,只有多讓偵查人員出庭接受法庭的質證,才能真正促使偵查機關不斷規范自身的取證行為。
《檢察風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正式入法,是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大亮點。立法者將檢察機關確立為非法證據排除的主體,這是否意味著對檢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汪建成:從法理上說,公訴人有排除非法證據、保障人權和維護司法公正的責任。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應當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偵查機關所提供的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有針對性地核實偵查取證行為的合法性。對于存在以非法方法搜集證據嫌疑的,應當要求偵查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說明;如果確認非法證據存在的,應當直接決定予以排除。
同時,檢察機關在審判過程中需要承擔證明控方取證合法的證明責任。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一規定從根本上否定了實踐中讓偵查部門就取證過程出具書面情況說明的做法,客觀上也符合被告人及其他相關人員舉證不能的現實,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實施至關重要。客觀地說,在無罪推定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成為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時代背景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只能由控方承擔。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檢察院可以提請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這不僅有助于緩解檢察機關在承擔非法證據舉證責任上面臨的壓力,更有助于通過庭審交叉詢問,使偵查人員直面取證不合法的苦果,推動某些偵查陋習的革除。所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給檢察工作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有助于檢察機關工作質量的提升。
《檢察風云》: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重大突破是對“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具體化,規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必要條件。那么,應當如何準確理解證明標準的內涵?
汪建成:從具體內容上來說,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第一個條件確定了證據的量的規定性,即證據充分的參照坐標是證明對象,只有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全部證明對象都有證據證明才達到了證據充分的標準;第二個條件確定了證據的質的規定性,即對“證據確實”提出了具體要求,既強調用以定案的證據是查證屬實的結果,又強調了對各種證據查證屬實的過程,即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強調后者的目的在于保證各種證據均具有法定的證據能力;第三個條件確定了證據的綜合運用法則,即在確保案件證據同時具備量的規定性和質的規定性的同時,對綜合全案證據認定事實提出更為明確的要求。
《檢察風云》: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強化了被告人保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賦予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聘請辯護律師的權利,并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強調辯護律師意見的作用。檢察官應如何面對辯方提出的證據?
汪建成: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就不能再一味固守單一的懲罰犯罪的觀念,在承擔懲罰犯罪職能的同時,還必須承擔客觀義務。其實質是要求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通過客觀評價案件事實,追求法律的公正實施,歸根結底就是要求檢察官成為“法律的守護人”,實現檢察官只對法律公正負責的目標。對于辯方提供的證據,檢察官經過審查后認為證據真實性存在問題的,應當提出疑問并在法庭上進行質證;而對于那些在取證程序上存在問題的,考慮到當事人取證并不涉及公權力的運用,一般難以采取強制性的取證方式,也不太可能對其他民眾的權利形成損害,檢察機關要保持適當的寬容度,不應作與控方一樣的嚴格要求。
采寫:張克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

